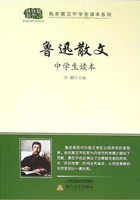郭营长到遂平县以后被安排在车站乡任党委副书记。他上任前首先考虑的是把三个孩子的上学安排好。从陕西到青海,胜利上了五年学,实际在校时间不到三年,这时按他的年龄必须上初中。十多岁的毛妮只上了一年多学,两位数加法不会算,现在要上四年级。七岁的巧,由于秀曾到部队加工厂上班,整天被拴在床上没人照管,该入学了还不会自己解裤带大小便。郭营长夫妇担心、痛心,却又无奈。
好在学校不远,而且在地方工作也没有部队那样的“令行禁止”“十万火急”,他和爱人千方百计帮助、引导孩子们学习,寻找各种办法,利用各种渠道为三个孩子加餐、补课。可是三个孩子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思想不稳定,意识不专一,脑子不好用,记忆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差,最终三个孩子连中等专业学校也没有考上。
据专家介绍,平原地方的婴幼儿到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地区生活,长期的缺氧、常年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缺乏维生素,就会导致儿童大脑发育的异化,造成正常人记忆力的减退。
遍访我的各位首长、战友,凡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子女,随军以后搬来搬去,今天上学明天停课,尤其是在高原上出生、在高原上生长的那一代人、那一批人,全团算起来有一百多个家庭,三四百个子女,没有一个正式考上本科的,通过做工作考上中专的也没有几个,绝大多数是凑凑乎乎上个初中、高中毕业。在襄渝线随军又上青藏线和在青藏线上随军的子女,事业有成的微乎其微。
所谓铁道兵战士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在郭国法营长身上可以窥见一斑。
郭营长看到子女求学无望时,又下决心让他们传承他的军旅夙愿。让儿子去当兵,让女儿做军嫂,支持国防建设。儿子胜利当兵后没有他那样屡逢部队扩编的机遇,三年就退伍了。大女儿向阳找了个军官随军啦,他很高兴。小女儿再找当兵的时被老申坚决拒绝了。为国防事业咱留点遗憾吧!留下个姑娘到你走不动时好照顾你!
郭营长出生入死、积劳成疾,最后落下了脑溢血后遗症,行动困难,大脑迟钝,在爱人申秀曾及儿女们精心照料下,承受着病痛,延续着生命。我和战友们去看望他时,他默不作声,以泪洗面,不断地用泪水诉说着他的无愧和有愧……
4.神秘的“山鹰机械厂”
参加关角隧道施工的指战员经历了挑战生命极限的卓绝,饱尝了风沙严寒、昼拼夜战的艰辛,但也享受到了其他高原部队所没有的殊荣与优待。高原食物供应不足,关角隧道优先安排;评功评奖、升学提干,关角隧道重点考虑。各级首长到高原视察,首先要看望关角隧道施工的干部战士,包括一些文艺团体到高原部队慰问演出,也一定要到1营2营演一场。政治上的关怀,生活上的关心,使指战员们虽苦犹甜,虽苦亦乐。
1978年仍是青藏铁路西格段的铺轨高潮期。由于党的文艺路线的正确回归,社会的、军队的文化生活趋于活跃,铁道兵部、兰州军区、青海省人民政府及各级文艺团体纷纷到青藏铁路沿线进行慰问演出,不少剧团、文工团,甚至包括铁道兵篮球队也深入到1营、2营慰问一线指战员。由于慰问演出活动较多,接待成了一个大问题。营党委决定凡到1营慰问的文艺团体由各连轮流接待。当年7月铁道兵文工团要到1营演出,按轮序由3连安排当天的午餐和晚饭。
接到通知后,历来对接待工作极为重视的钟指导员召集陈副连长我们几个商量接待方案。指导员听了连队的家底介绍后立即提出要求:
铁道兵文工团到营队演出,代表的是兵部首长、兵部机关的关怀,他们十分辛苦,非常不易,生活招待要按照营首长的指示精神必须搞好。所需的食品要及早准备,没有的东西早点出去买……
当时连队的青菜供应正值淡季,品种很少,正常吃菜已很困难。指导员还希望演出结束时为演职人员以酒驱寒。当年连里干部变动大,上级来人次数多,我的小库房里的存酒早几天已经告罄,决定立即去一趟西宁,采购些蔬菜、罐头等副食品,再买一些连队应酬方面的必需品。时间紧迫,事不宜迟。当天晚上请老司务长帮助联系了一辆马槽解放平板车(部队为区别翻斗解放车,把木制平板车称为马槽车),次日早上出发,晚上直接跑到乐都县以东的民和县,找到曾经买过菜的一个地方。由于我们施工部队对蔬菜需求量大,买菜时基本不讲价钱,不挑不拣,什么菜都要,当地群众对我们这些“部队上”买菜的很欢迎。只是季节不到,蔬菜品种很有限,较多的是茄瓜(青海人称菜瓜),还有些包菜(青海人称甘蓝,部队称莲花白)、菠菜,最不好办的是有一种青海特产的水萝卜,红颜色、圆圆的,算盘珠、杏子一样大,既不能炒着吃,又不能生着吃,实在不能要。(三十年后,在郑州“金悦利湾”所吃的鲍鱼、鱼翅的配菜中又吃到这种高级的小水红萝卜,只可惜当时没有鲍鱼、鱼翅做压轴菜)。当地群众看我买菜心切,就逼着非要配卖这种萝卜不可,无奈也只好装了二三百斤。谚语说是“萝卜快了带泥卖”,我们这次是“要买好菜带萝卜”。
青海的首善之区西宁市,当时不到百十万人,作为青海省唯一的一个市,它不仅是个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商业中心,也是青海省内数十万驻军的物资采购给养补充的大本营。兵站部、运输兵、通信兵、二炮部队、铁道兵在当时都是相对集结比较多的,分散全省各地,分别执行着特殊任务,都有着一个共同的难题:生活食物供应紧缺。而西宁则是唯一能够满足适当需求的地方。因此,在西宁市进行大宗购买活动的基本上都是部队的。
当天下午,我从西宁市最大的十字大街“大十字”到东关大街,从古城台到小桥,车不熄火,人不停步,好不容易买了几箱猪肉罐头、鱼罐头和水果罐头,关键是买到了一箱互助大曲、一箱老白干酒和两箱红酒,解决了连队接待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次西宁采购,出发前唯一不大放心的是汽车司机不是我希望的熟人或老乡,而是一位甘肃同年兵。两天来的活动中,这位司机配合得超出预料的好,我非常感激。下午,在买罐头时还专门为他买了两包香烟。
第二天往回返的线路采纳了司机的建议——走青海湖南线。一大早起床吃了早饭就上路,争取早点赶回连队。
青海境内,出西宁市向西有两条重要线路:古代丝绸之路的羌中道,自湟源向西北方向过刚察、青海湖正西过天峻、德令哈到茫崖为羌中北道。另一条是自湟源向西南,翻日月山过青海湖,经香山德、格尔木到茫崖与羌中北道重合后进入新疆。当时中原地区与西藏尚无大道相通,而文成公主进藏所走的“唐番古道”则是过日月山自倒淌河向南走果洛、玉树经四川的昌都到西藏,是谓当今的“青康公路”。而新中国形成自东向西的到西藏两条主要干道是以青海北面的羌中北道为骨干的青新公路。我们团所处的天峻县正处在青新公路上,平时到天峻县的车辆就走北线,这条路自西宁市到刚察县因有核基地的政治优势早已铺上了柏油,刚察以西则全部是令司机们伤脑筋的石子“搓板”路。另一条则是走青海湖以南,自格尔木过唐古拉山的青藏公路,即二一四国道。司机所谓的南线,除翻越日月山弯多坡陡外,全程柏油铺面,而且我们连又在天乌公路上,走南线距离上与北线相比要稍近一些。
司机走在他乐意走的公路上,虽然一路仰行爬坡,却车速均匀,铿锵前行。
当兵四年第二次行走南线。第一次是到江浙出差时与全师其他几个外出采购的同志统一乘车从乌兰去西宁,中巴车走下山路,没有什么印象就翻过了日月山。这一次则是与司机一起从西宁向青海高原进发,一路爬坡步步升高。早就听说翻日月山很危险,从湟源岔路向南开始走我心里就祈望着能顺利通过日月山。
日月山是青海农业区与牧业区的分水岭,平均海拔四千米左右,历来是内地赴西藏大道的咽喉,唐朝时为唐朝与吐蕃的分界线。当然也是汉藏文明的分水岭,故有“西海屏风”“草原门户”之称。日月山因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曾驻驿于此而闻名。
日月山的公路自山下的日月山乡(海拔三千米左右)一路陡坡向上,红岩垒垒,兀峰连连,汽车像一头驯服的老牛,喘着粗气,一步一颤,十步一旋地一直攀爬到四千多米的高度。在日月山隘口,司机长出了一口气,我一直前倾的身子似在用力为“老牛”助力加油,这时自然地挺了起来。司机看我头上浸出汗珠,问我:“怕什么?”我说:“害怕爬坡时汽车累出毛病。”司机听出我对汽车是外行,笑了。
过日月山隘口,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眼前也顿时开阔、明亮起来。西边是广阔的草原,线条柔和的青海南山静静地卧伏在地平线上,成群的牛羊和蘑菇状的帐篷勾勒出草原的诗情画意。汽车如脱缰的战马一路狂奔,很快蹿到了109国道(青康线)和214国道(青藏线)的岔路口。倒淌河到了。下山时司机说要给汽车加点水,我提醒他,快到倒淌河了,那里肯定有水。到倒淌河才发现我说的“肯定”是瞎说。车到倒淌河岔路口停下问路边的居民,倒淌河在哪里?答曰:这里就是。司机提着水桶下车找了一会儿没见到河。原来这里的河是地名,是历史文化的一个藐小遗存,不下苦功夫在这里根本找不到那条河。
据说文成公主翻过日月山后,弃轿乘马入草原。她眼望茫茫戈壁,无边的草原,千里吐蕃,何日可达?不由感到一阵酸楚,顿时失声恸哭。泪水带着公主的思乡之情汇成河水向西流去,造成“天下河水皆向东,唯有此水向西流”的奇观。传说的历史给我们一种美好畅想,而往日的河水则随着岁月的远去渐流渐少。没走过倒淌河的人,可能会以为倒淌河是条波涛滚滚、水流清澈的奔流大河,到跟前经过打听才知道闻名遐迩的历史名河就在脚下,少雨季节仅是条干沟,冰雪消融之时才有小小溪流。不知司机用什么办法从何处提了半桶水,灌满水箱后看看虽已近晌午,而此地黑乎乎的土坯房没有适合我们俩吃饭的地方,蛮有把握地说:再有个把小时到茶卡再吃饭。
我有同感,也有同心。马达发动,离合开启,我的心伴着汽车启动开始了轻松愉快的跳动。汽车像轻盈的春燕欢歌前行,爽意飞翔,飞向草原,飞回关角。
天有不测风云。高原上运转的机械设备更有难料的故障。欢快的解放车飞奔了约二十来分钟,突然慢了下来,接着哼哼两声停下了。司机脚踩马达嚓嚓嚓了十几下,汽车仍像死猪一样没有丝毫反应。我的心情一下子由沸腾降到零下,愣住了!
司机推开车门,从坐垫下面的工具箱里拿出一把“改刀”,下车掀开引擎盖,不知照什么地方捣了几下,仰脸对我说:“哈啦(甘肃话:坏了)!电路不通了。”
我像一个放了气的皮球,软塌塌地挪下车。“能不能修?”我问。
“估计不咋着。”司机说着话没有停止手里的活儿,捏捏油管,按按线圈,捣捣分电器,我的脖子伸得像“蘸蒜汁”一样瞪眼看着。其实只是干着急,对汽车这家伙我什么也不懂。
司机“捏捏”“捣捣”,又到驾驶室踩马达发动,一次、两次、三次……没有任何反应,最后一次从驾驶室下来悻悻地说:“点火线圈烧了!”
“好不好修?”
“修不成。”
“有没有备用的?”
“以前有一个能用的,前两天让别人用了,现在车上有一个也是坏的。”与没有一样!
我脑子里出现了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也不知道该怎么问。过了几分钟才回过神来。
“那咋办?荒天野地连个人影也没有。”
司机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吸着烟在想心事。这时我看了一下我们所处的环境:路的南面是逶逶迤迤的青海南山,路的北面近处是草原,远处是浩瀚无际的青海湖,湖水蓝色如黛,发着磷光。车向前方是214国道,像一条黑色巨龙一直伸向天边。视野以内没有车辆,没有行人,甚至看不见一只飞鸟,白云在蓝天飞翔,白云下往日的羊群也无影无踪,空旷给人以冷酷、发怵的感觉。在车的后面是刚刚告别的日月山,弯弯的国道从倒淌河出来以后打了一个大弧形弯归到了青海湖边。视野里看到路两边有羊群和几头牦牛在率意地吻着大地,啃着青草。约有两百米处有一个公路界碑,我走近看见水泥制作的界碑上显示着“二一四”和“一四八”字样。出西宁已经走了一百四十八公里,不知道到关角还有多远。
“离关角还有多远?”我问。
“估计有一百多公里,基本一半路程。”
我手足无措,没有了主张。一路上觉得这位司机老兄挺实在,经常出车也应该有经验。“你看咱下一步怎么办?”我问。
“往家里打电话,让连里来个修理工,带个点火线圈。”司机说得很认真,也很沉重。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儿打电话?如果是到乌兰、德令哈这些地方,顺路还可以捎个信儿,而我们连、我们团不在这条线上。正在无计可施,从后边有一台车开过来了。我们俩像看到了救星。至少还有一公里的距离,我们俩就分站两边做好了拦车准备。不知司机怎么想的,当时我心里根本不知道拦住车后要人家帮助解决什么问题。
汽车停下了,是一台青海湖牌马槽车。车门上一行白字“山鹰机械厂”,车后面被帆布篷盖着,几道麻绳捆得紧绷绷的。中年司机摇下车窗伸出小平头,面无表情地问:
“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