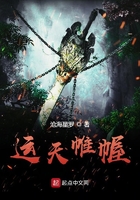前面已经对中国佛学精神的印度文化之源与中土文化之根以及它的形成发展做了初步的探讨,从本讲开始,将对中国佛学的最主要代表隋唐佛教宗派的主要佛学思想分别予以介绍,以便更好地把握中国佛学的精神。
本讲主要介绍第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的思想。由智实际开创的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形成的第一个宗派,“性具实相”被认为是该宗最具特色的理论,天台宗后昆四明知礼曾说:“只一具字,弥显今宗”,这俨然已成为天台有别于他宗的理论标尺。在展开“性具实相说”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鸟瞰一下天台学的大纲,它大致可以被归结为教与观两个方面,即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与止观并重的实践法门。
第一节五时八教与止观并重
判教是一个宗派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所谓判教,乃是对佛陀所说的各种教法予以分别评判,重新估量其不同的意义与地位。判教思潮发端于印度佛教部派分裂之时,而随着大量佛典的汉译,为调和其中的大小、空有之争并作出于己有利的安排,南北朝时期各学派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判教体系。
刘宋时道场寺慧观,就依据《大般涅盘经》牛乳五味说并受当时顿、渐之争的启发,首先建立起“二教五时”的判教体系。到了智时代,据《法华玄义》所述,当时有影响的判教,已有“南三北七”十家之多。按智的说法,这十家判教虽互有出入,但从总体上看,也有共通之处:南北地通用三种教相:一顿、二渐、三不定。《华严》为化菩萨,如日照高山,名为顿教。三藏为化小乘,先教半字,故名有相教;十二年后为大乘人说五时《般若》乃至常住,名无相教,此等俱为渐教也。别有一经非顿渐摄,而明佛性常住,《胜鬘》、《金光明》等是也,此名偏方不定教。此之三意,通途共用也。
三种教相实际上更符合南方三家的情形,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对渐教的判释有异,即于中或开为三时,或开为四时,或开为五时,而北方七家则远为复杂,并没有像“南三”那样有一个大致统一的构架。智的判教体系,就是建立在对上述各家判教思想的批判整合基础上的。
先来看“五时”。“五时”之说,一般以《涅盘经》的牛乳五味喻为依据。《涅盘经·圣行品》以牛乳制作过程中依次形成的五种味道乳、酪、生酥、熟酥、醍醐为比喻,来说明从佛出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从《方等》出《般若》、从《般若》出《涅盘》的相生次第。南方以成实师为代表的五时判教,就依此与各种佛经相配,认为从牛出乳,譬如佛陀在成道后十二年内所说的三藏有相教;从乳出酪,譬如其后所说的《般若》无相教;从酪出生酥,譬如《维摩》、《思益》等褒扬大乘、贬抑小乘的褒贬抑扬教;从生酥出熟酥,譬如会三归一的《法华》同归教;从熟酥出醍醐,譬如明法身常住的《涅盘》常住教。
可见,南方的“五时”,但约佛陀一代时教的次第高下来作判释,并且仅于渐教中作五时分判。
智对这种以五味譬五时的观点提出了责难,认为这种配对是不确切的,并不符合经文的原意。首先,以十二部经对有相教,智认为,有相教事实上只有九部,而且智是以顿渐共约五时,因此佛陀最初说的是《华严》顿教,亦非有相教;其次,以修多罗对《般若》无相教,智认为,修多罗通指一切有相、无相,亦不能仅以无相《般若》相配;再次,以《方等》对《维摩》等褒贬教,在智看来,《维摩》不应在《大品般若》之后;最为牵强的是,经文明明说的是《般若》,却又以《法华》来相配,实为乖文失旨。
智指出,《涅盘经》的“五味”首先乃是从根性上来说明的。众生因有信解行证的差别,故而佛陀开示种种方便说教,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修行者转凡成圣。比如,以《华严》为乳,以三藏为酪,是因为说《华严》时,于凡夫无益,其见思惑未转,而说三藏时,却反而能断其见思,不能因为于小机有益,就认为三藏高于《华严》,这里没有次第高下之别,只是约逗机而言。而从根本上说,五味都能获得醍醐、见得佛性,如《涅盘经》所言,置毒乳中,乃至醍醐,遍五味中,悉能杀人,这显然是与《法华》会三归一的思想相一致的。
不过,智在约根性说明“五味”义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五时”教说,其主要根据是晋译《华严经·性起品》的“日出”喻。该经卷三十四云:“譬如日出,先照一切诸大山王,次照一切大山,次照金刚宝山,然后普照一切大地。”此喻表明,释尊一代时教,可依说法的先后次第,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华严时,谓释迦成道之初,首先为慧根菩萨说《华严》圆顿之教,令速悟入,如日出先照高山。第二鹿苑时,谓佛为根机较浅不堪领受《华严》大法的初学者,于鹿野苑等地,讲说小乘四《阿含》,宣说苦集灭道“四谛”之理。第三方等时,谓对已有小乘基础者,佛陀进而为说大乘《方等》类经典,令其耻小慕大。第四般若时,谓佛陀为明诸法皆空、显中道实相之理而广说《般若》类经典,此有通别之分,通即共般若,为三乘共学,别即不共般若,为菩萨独进。以上三时,从说法形式看,俱为渐教。第五法华、涅盘时,此为佛陀最后的说法,直明一佛乘真实之教,从说法形式看,这属于非顿非渐教。其中《法华》开权显实,会三归一,方便引导十界众生归于究竟佛乘,大智之人如舍利弗等禀此即可受记见性。这样历五时五味至《法华》而得道,智称之为“前番”;更有于《法华》未得入者,则重于《般若》淘汰,令于《涅盘》中悟入,智称之为“后番”。
前番与后番,证悟虽有先后,但二经俱为醍醐,能同样得道受益,就像谷物虽有早熟、晚熟之别,但最后都能成熟一样。不过,在具体论述上,智对两经的看法事实上是有区别的。在他看来,《法华》原始终要,唯论如来设教之大纲,是最圆满、最究竟的法门,《涅盘》则对未能于《法华》得悟者而说,相当于对《法华》的补充,在照顾到当时受教界普遍重视的《涅盘经》之地位的同时,智事实上更为强调《法华经》的权威,《法华》畅如来出世之本怀,开示真实一乘,故能遍摄一切众生,而其他佛典都是化导不同众生的方便权说,具有不同的教相。在全面安排与系统调整各类佛经的基础上来突出《法华经》的崇高地位,乃是智判教的根本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和南方成实师的“五时”说不同,智的“五时”是建立在“五味”义的基础上的。在《维摩经玄疏》卷六中,他对此有一个总结性的说法:但以禀教之徒根缘不一,时方有别,是以大圣设教名字不同,言方亦别也,故有顿渐赴机。至如《华严》广明菩萨行位,三藏偏说小乘,《方等》破小显大,《大品》历法遣荡会宗,《法华》结撮始终、开权显实,《涅盘》解释众经、同归佛性常住。五时的先后次第乃是为了适应众生的不同“根缘”,究竟说来,佛以一音演说法,三乘同归一乘,若历然要作次第高下的分别,则必然会得其权而忘其实,在智看来,这正是南方五时说的根本缺陷之一。
灌顶大师再来看“八教”。首先需要指出,“八教”之说,乃出自智弟子灌顶的总结,而智原来的说法是三种教相与四教义。在《法华玄义》卷十上中,智明确指出其判教的大纲为顿、渐、不定三种教相,并认为此三教各可约教门与观门而分别作二解,可见,他以三种教相为判教大纲是以他的教观一致论为基础的。具体说来,就教门而言,第一是顿教,值得注意的是,智并不仅仅把《华严》归属该门,在他看来,如《维摩》、《大品》、《涅盘》等大乘经中显示该教相的内容也都归属该门,换言之,他是纯粹以教相来作分判的,而不是仅机械地作教部的归类,即简单地把某经置于某一部类,如南方诸家所作的那样。第二是渐教,指上述《涅盘经》所说的“五味”次第。第三是不定教,即不为顿、渐二门所摄的教门,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约根性的不同,于五味之中,能处处得见佛性,并不一定要按照五味的先后次第,这譬之如《涅盘经》所言,置毒乳中,乃至醍醐,遍五味中,悉有杀义。智有时也把不定分为显露不定与秘密不定,但他主要是以显教来作判释的,秘密不定可直言为密教,基本不在他考察的范围之内。而智之所以要特别强调三种教相,是因为它正好可与他所传的三种止观相配合而构成他的教观一致论,与之相配的三种止观分别是圆顿止观、渐次止观与不定止观,这也就是上述三种教相约观门的解释。
智弟子灌顶开始有“化仪四教”的说法,并与“化法四教”相结合而构成所谓的“八教”。化仪四教是对三种教相的发展,即将显露不定与秘密不定开而为二,合顿、渐两教而为四教。显露不定又称“不定教”,秘密不定又称“秘密教”,两者的区别在于,佛以一音说法,“同听异闻,互不相知,名秘密教;同听异闻,彼彼相知,名不定教”,这里顿、渐两教也不再是纯从教相上分判的,而是主要就“五时”立言,即以《华严》为顿,《阿含》、《方等》、《般若》为渐,《法华》、《涅盘》为非顿非渐。之所以称为“化仪”,据灌顶解释说,是因为它系“化之仪式,譬如药方”,即就佛陀化导众生的方式而作的分判。应该承认,和下述“化法四教”相结合,“五时八教”的判教体系单就“教”而言显得更为系统,但它事实上忽略了智以三观配三教的教观统一论的基本思想,明末智旭撰《教观纲宗》,对历代相承的“五时八教”说提出质疑,就是企图恢复智判教原则的一种努力。
如果说“化仪四教”是治病的药方,那么藏、通、别、圆的“化法四教”就是实际的药味,“所化之法,譬如药味”,它是就佛陀化导众生的内容而为言的,事实上,这也是对智“四教义”的进一步系统化,其具体内容是:“藏教”,即以《阿含》为主的小乘经、律、论三藏,此教以小乘为对象,傍化菩萨,它以生灭四谛为教理,认为有苦可舍、有集可断、有道可修、有灭可证,在观法上则是通过析空观断见、思二惑,证得偏空之理而入于无余涅盘。“通教”,通前藏教,通后别圆,为三乘共禀,其经典以《般若》为主,亦包括大乘《方等》类经典,此教以菩萨为对象,傍通二乘,它以缘起性空的无生四谛为教理,认为诸法如幻如化,当体即空,故四谛生即无生,在观法上则是通过体空观由假入空,是大乘的初门。
“别教”,不共二乘、专为菩萨所说的法门,它以因缘假名的无量四谛为教理,在观法上则由空入假,进一步认识四谛的无量行相,上根之人,还能因此由假入中,不过,由于三谛隔别而观,即它是“次第三观”而非圆顿的“一心三观”,因此所见证的乃是与空、假不融的“但中之理”。“圆教”,此教以不可思议的无作四谛为教理,所谓“阴入皆如,无苦可舍;无明尘劳即是菩提,无集可断;边邪皆中正,无道可修;生死即涅盘,无灭可证”,它以圆顿的“一心三观”为观法,所见证的乃是即空即假即中的性具实相。
天台宗“五时八教”的判教思想在判定佛所说的各类经典的意义与地位时,按照本宗的理论体系,从说法时间、思想内容以及教法方式等方面,对佛教各派思想作了系统的整理与安排,一方面抬高本宗的地位,把本宗的学说确定为佛的最完满的说教,另一方面把佛教内部各种异说融通起来了。无论从其判教体系的整体性,对佛教异说的融通,还是以自宗为主,突出“一佛乘”的宗旨等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同时,智从教观一致论出发,将教判的三种教相与止观联系起来,也体现了其佛学理论体系的一体性、圆融性。
如上所述,在智的着述中,教观相资是他所有理论的基石。他对东流一代教法的判释,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以此来指导止观观心的宗教实践。而当我们转向观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学说的另一特色,那就是止观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