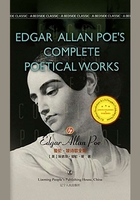纪事
上半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参加英语培训,9月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又开始大量阅读西文典籍。
什么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海”?
一年多来,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它所带来的吸引力和压力,使一向比较平静的学界也不时听到这样一个具有直接实践意义的问题:“我要不要下海?”然而,现在我想提出的问题虽然也和市场经济有关,却纯粹是学理性的,是纯粹出于好奇,即我想问:什么时候我们竟然有了一个“海”?或者说,这“海”是怎么来的?它的成因和道德有何关系?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应当如何看待其动因等等。
中国曾经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但现在我们所说的“此海”肯定非“彼海”
也,现在的“海”是市场经济、商品生产的“大海”,“下海”也就是办公司、做生意之类(gotobusiness)。黄仁宇在考虑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时,曾引Maurice Dobb语说明主要有三种研究这一现象的方式:一是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二是注重其精神与动机;三是注意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为了限制我们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试着仅从第二种方式,即精神与动机的方面来考察这“海”的成因,这也直接和道德有关。
我在读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管子·侈靡篇》等文献中,曾经不止一次在心里感叹:中国不是早就有了某种市场经济的萌芽吗?太史公笔下的几个商人,不是典型的资产者的形象吗?你看他们不仅具有韦伯所强调的勤劳、节俭的性格特征,而且也同样专一、大胆、有远见、有谋略、有决断,如白圭“能薄饮食,恶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那么,在这种勤劳、节俭、多谋、善断之后隐藏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韦伯认为在西方那些积极从事工商业的新教徒心底深处,埋藏的是一种神圣的召唤(calling),是一种对自身天职的感觉。而在古代中国人那里,显然并没有这样一种宗教的联系,于是,按司马迁的解释,那刺激着、推动着古代商人的,看来就直接是一种相当广泛的人性动机了:“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也就是说,在这些性格行为后面隐藏的,首先,它是一种求利益、求实惠的动机;其次它还是一种求自利、求己惠的动机;最后,在合适的条件下,它还将是一种谋求获得最大限度的自我利益的动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谋求个人利益的“极大化”(maxi mi zation)。
我们后面将谈到:我们没有必要隐讳或回避这一点,坦然承认这一点也许还是最好的引导它的第一步。但我们现在暂不论及此,而是依然回到前面一个问题:既然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有了某种市场经济的人格或人才的准备,甚至有了某种思想理论的萌芽,例如我们在《货殖列传》中读到“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的某种“放任主义”的思想;“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思想,以及《管子·侈靡篇》中以充分消费来刺激生产的思想,甚至我们看到,在秦汉之初商人已实际取得了某种“礼抗万乘,名显天下”的“素封”地位,这种地位虽不可能与现代社会相提并论,但至少比中国商人在后来中古时期所居的地位为高,那么,既然源头之水并不太缺少,为什么这些源头之水却一直没有汇聚成一个汹涌澎湃的“大海”呢?
从中国人的民族性中去寻求解释,认为中国人生性淡泊,追求和谐,从而阻止了这一发展,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可能是错把少数人的文化性格当成了大多数人的文化性格。相反,中国人在没有超越的宗教,以及其文化的实用倾向的影响下,反而是更有可能趋向实利的。1919年12月14日,陈寅恪与吴宓在哈佛大学曾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陈寅恪在指出中国思想学问的实用特点之后说:“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群,则中国人经营商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
虽然仍几经曲折,但今天,中国人之为“世界之富商”的日子看来确实已经不远了,磕磕碰碰地走了那么多路之后,中国现在看来确实已经走到经济迅猛发展的门槛了,我们已经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那经济起飞的晨曦。
中国人经商的巨大才能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在东南亚,以及东亚数小龙起飞的过程中得到了雄辩的证明,而从80年代起至今,也在中国大陆得到了证明。这里当然有制度与政策之功,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大陆近十多年的发展中,虽然市场的体制远非健全和完善,甚至“市场经济”的正名也只是晚近的事情,中国的经济却还是在此期间取得了令世界侧目的高速度。这一原因,我想应当首先到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中去寻找,这种动机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而正是这种动机,也将使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具有一种最重要的动力保证。
因此,我们不难承认,中国人就其多数来说,不仅确实是非常聪明、精细和能干的,也是有着相当强烈的致富欲望的。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指出过“上下交征利”的现象,感慨人们“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而在几乎经过了两千年的儒学熏陶之后,王夫之仍然说,“庶民之终日营营,有不如此者乎?”今天,对大多数人的日常活动亦可大致作如是观,虽然我们将站在一个稍稍不同的立场上,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此事。
那么,为什么这一种相当强烈和普泛的求利动机并没有使中国在历史上发展出一种高度繁荣和发达的市场经济来呢?这里当然有许多原因,包括许多技术理性方面的原因。用欲望乃至贪欲并不能够解释市场资本主义的产生,而我们知道,上述古代中国商人的活动和思想也和现代市场的经济活动和理论相距甚远,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欧洲的出现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此指出在中国制约了这一发展的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社会的等级制度,一是一种占据了支配地位的追求和谐理想和基本生活水平的价值体系。
我们在此不想详述这两个基本因素。显然,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虽然是向下开放的,但却是始终存在的;而作为社会主导精神的价值体系虽然主要是儒学,但实际上也得到了道家和佛教思想的支持。
我们在此只想特别指出这两种基本因素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起了主要的遏制作用。后一种价值体系虽然可能只是为少数人所衷心地赞同,而并非多数人的想法,也就是说,它是精英性质的,然而,由于它是处在社会上层的少数人所信奉的价值体系,借助于社会的等级制,它就可能对整个社会起一种主导和统制作用,就能通过至少对人们的活动和操作范围的限制(如重本抑末的政策),而把社会上人们的求利欲望也限制在某个范围之内。
而在近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不断遭到了猛烈的冲击,这当然与西方的刺激有关,但我们可以指出,这一平等化的潮流实际在中国正面接触西方之前就已经悄悄开始了。近四十年以来,中国人可以说终于获得了有史以来最普遍、最广泛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