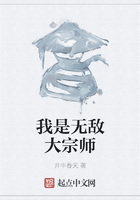1935年上半年结束时,由于追击红军,薛岳、胡宗南带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驻了四川,控制了四川的局面。加之龙云投靠了蒋介石,使蒋介石多年来梦想统一西南的愿望,总算得以实现。他把这很大程度归结为庐山办训练团的功劳。所以一进川,就派陈诚创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他自兼团长,陈诚和四川军阀刘湘任副团长,轮训武官营长以上和文官县长、中学校长以上人员。蒋介石第一次来到成都,登上峨眉山勘察地形,选择校址。
蒋介石一行从峨眉山脚下报国寺出发,经过伏虎寺,驻节半山,再登临顶峰。在圩池之间,卫士们租了一所外国人避暑的竹木小屋,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居住。侍从人员也租了一所洋人的简易房子,分居左右。他们用大竹管接来山溪水,供蒋介石饮用。溪水经过沙石过滤,清冽味甘。蒋介石品了品,不住点头:“比蒸馏水味浓,好喝,跟青岛崂山矿泉水差不多。我以后就喝这种溪水,但一定要注意过滤清爽。此地人多吸食鸦片,防止这种恶习污染。”蒋介石对峨眉胜景极感兴趣,两次乘坐滑竿登金顶游览。蒋介石用望远镜观赏四周风景,舍身岩下,万丈深渊。听说有人追求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曾纵身跳岩。蒋介石用望远镜看了一阵,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就把望远镜递给宋美龄。宋美龄看了半天,放下望远镜,感叹了一声:“愚人何必去舍身呢?”第二天,蒋介石早早到达金顶,果真看到了日出、云海、佛光、圣灯的“四大奇观”。一轮红日在万云簇拥之中突然跳出,顿时漫山遍野红透,云海翻腾,蒋介石大喜,以为吉兆。峨眉山的猴子是出名的顽皮,文明点的被人称作“猴居士”,野蛮点的被人叫“土匪”。最要紧的是不能去招惹打它们。它们一旦被伤害,就会群起而攻之,以至伤人发生意外。所以蒋介石和宋美龄外出游山,侍从事先就要在路口注意猴子的动静,或者把猴子引开。可是宋美龄又特别喜欢引逗猴子。卫士又把猴子引到路旁,让它老实蹲下,让宋美龄开心逗弄。蒋介石在一旁也笑得格格有声。
在山上转了一圈,蒋介石还是觉得山脚下的报国寺最理想。这里三面环山,很负盛名的玉液泉自石罅中流出,绿叶娑娑,溪流淙淙,景色端的非凡。训练团开办之初,只有报国寺周围的几间竹架泥墙的简易棚。蒋介石亲自上课,大讲三民主义。还请了一些著名教授、学者,来讲国内外大事和军事知识。训练团先抽调了四川各路军人邓锡侯、刘湘、刘文辉、王陵基、杨森等部队校尉下级军官训练,后再调训将校高级军官,名曰高级将校班。在训练团内,当师长的可任连长带队。当时四川军人大都有抽鸦片的嗜好,高级军官的家里,竟然公开设置烟具,而士兵几乎个个是“瘾君子”。蒋介石办班,就想改掉这种恶习。谁知这一大批“瘾君子”来到训练团,憋得难受,就每天偷偷摸摸进入大伙房隐蔽处过瘾。蒋介石怕一时抓得太紧反而闹出事来,示意陈诚稍为宽和一些。陈诚心领神会,在夜间巡查时,预先告知带队的川军领袖,让他们及早吹风下去,将烟灯熄灭。但是,在第二、第三期训练中,政治部的干部查岗时,只通知下边的人“熄灯”,然后去查没有得到通知、常在那里大过其瘾的两个大头目杨森和王陵基,当众出丑……
正在蒋介石尽兴游峨眉之时,周恩来他们正在生死线上挣扎。
连续征战,饥饿与疲惫,病魔再一次将周恩来扑倒了。
周恩来从8月初就开始腹泻,大便中有脓、血和黏液,体温从38度上升到40度,全身逐渐发黄,神智不清以至高烧昏迷。红军中的李治医生化验了大便,发现有阿米巴原虫。中央马上把在王稼祥身边的王斌医生找来,他给周恩来做了身体检查,发现肝脏肿大,下缘竟达到右肠骨窝,右侧下胸及上腹肿胀,胸围右侧比左侧大四横指。王斌认为是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无疑了。幸好药箱里还有依米丁注射液,就给他每天打一两支,没有别的办法。医生还在担心,万一脓肿破裂到胸腔或腹腔,肯定有生命危险。医生急得只好让人到60里外的山找些冰块,放在周恩来的肝区上缘冷敷,每天从早上10点敷到下午6点。人们还是担心,又把邓颖超从干部休养连接来,一起护理周恩来。其实邓颖超自身也难保,从长征开始前就患肺结核,经常发低烧,痰中带着血丝。她一看周恩来昏迷不醒,急得不行,就在周恩来木板床旁边的地上铺了点稻草,躺下。一看周恩来那件灰色毛背心,爬满了虱子。她用指甲掐着,竟有一百七十多只,血把指甲都染红了。被风吹刮着的营火哔剥地爆响着,有人在剥那些战马的皮。地面上的几万红军,都在担忧。周恩来轻轻动了一下,在他不安的脸上,往外突出的颧骨显得黑黝黝的。他开始呻吟,说肚子痛。邓颖超和医生把他扶起来大便,竟排出半盆棕绿色的脓,高烧也逐渐减退。他清醒过来,一看邓颖超在身边,好生奇怪。马上嘱咐人:“快,给一、三军团发电报,问他们作战计划执行得怎样?”
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杨尚昆正在屋里转圈。马上要过草地了,原先抬担架的同志一个个病倒了。彭德怀已经命令扔掉两门迫击炮,腾出40名战士,专门负责抬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重病号。当时红军总共不过八门这样的炮。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负责组织担架队,他们为找个担架队长犯了愁:这个人必须有高度政治责任感,能吃苦;同时要有点医学护理知识。这在多半文盲的红军里实在难觅。
突然一个自称“大知识分子”的人冒了出来:“我来当担架队长!”
彭德怀扭脸一看,又泄了气:是陈赓,红军干部团的团长。彭德怀意外地大笑起来:“你是个瘸子,还是先保住你自己吧!”
杨尚昆也直摇头。陈赓的腿部多次负重伤,现在走路还一拐一拐的,再说干部团里管着百十号人,说是“团”,其实好多“团员”都是师团干部。
“你们放心!”陈赓能说会道,“我陈赓没多大本事,可对革命是心地赤诚,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就一定能把周副主席安全抬到目的地。”
也只好“瘸子”里拔将军了。8月21日,由陈赓担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去抬担架,抬着周恩来向那荒无人烟、充满沼泽和泥潭的大草地进发。周恩来不愿看到同志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地抬着担架,几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下来自己走。然而他已衰弱不堪,身不由己了。(19年后杨立三去世,担任着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说什么也要亲自为杨立三抬棺送葬……)
走出草地,周恩来感激的目光望着陈赓,说:“东征时,你曾经救过蒋介石;长征路上你又救了我!”
陈赓笑了,两手做了个遗憾的动作:“假如那时我知道我们的蒋校长竟如此反动,我说什么也不会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了,弄得我们和他斗到现在!”
周恩来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按现代医学的说法简直不可能。王斌医生后来分析:如果当时肝脓肿不是和横结肠黏连,脓肿破裂后不是穿入肠内而是穿入腹腔,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周恩来是不可能被救治的。可奇迹偏偏在命如游丝上发生了。当时陈赓闭眼双手合十念了一道“经”:“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周恩来在1976年临终前,对一直在医疗组工作的王斌说:“你40年前对我的救治,使我多活了40年……”
1935年9月中旬,正有峨眉山给军官训练团讲课的蒋介石,突然接到薛岳、胡宗南的来电,说红军已跨过草地,突破封锁线到达了阿坝和巴西地区。蒋介石在震惊之下大发雷霆,当即将失职的师长撤职查办,并急调江西的三十七军,同时命令东北军在甘肃的静宁、会宁、天水和陕西的平凉一带堵截红军。又利用陇南土匪出身的新十四师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及天险腊子口。
不到十天,蒋介石心情忧郁地下了峨眉山,还没坐稳,戴笠来报告红军已突破天险,红一方面军与红三军团业已会师,并统一由毛泽东率领。戴笠说得又快又急促,不时被蒋介石所打断。蒋介石时刻绷紧的身架一下瘫软下来,大声感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戴笠站着不动似有更重要的事要报告:“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出兵北上抗日!”
蒋介石并没吃惊:“这我知道。他们不是共产党,好对付。”
“可他们的军队已进入湖南衡阳,委员长派去的军队顶了一阵,现在成了僵局,只怕时间长了,军心有变。”
蒋介石喝着水:“我们就是要坐观以变。但变的不是我们的军队,而是他们。广东空军首领黄光锐,拿了两千三百多万,比韩复榘、石友三当年还给的多,他不会变卦!还有余汉谋……”
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策动的“两广事变”酝酿已久。就在这年夏天,广西的李品仙作为两广集团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黄旭初的总代表,来到湖南与省主席何键相晤。一天中午,何键请李品仙到长沙容园吃饭。席上只有四个人,另两个人是李品仙的秘书和何键的部下刘廷芳。李品仙边吃边高谈阔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抗日。而现在中央就好比一辆坏了的汽车,动不得了,它不动我们就在后面推它。”接着,李品仙婉言说出两广军队欲假道湖南北上抗日的意思。
何键埋头吃菜,见无人答话,便用眼迅速看了刘廷芳一下。刘会意,马上向李品仙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李先生是否可以先去南京,与大家朋友了解一下全国经济、国防诸方面的情形之后再作决定?我敢断言凡是中国人,全国无论男女老少都是要抗日的,我自然也是不例外。第二,你既然要抗日,为什么军队不往边防走,而要往里派?”
李品仙猝不及防,眉毛一竖,直瞪着刘廷芳。何键一看气氛有点僵,忙堆上笑脸:“李先生一路辛苦,早点送李先生回招待所休息吧。”
从招待所出来,何键和刘廷芳来到何公馆,何键挺神秘地说:“现在情势很紧张,根据各方面密报,两广要出兵北上,直赴武汉,成立临时国民政府,与中央分庭抗礼。”何键吐出牙里剔出的肉丝,继续说:“据我所知,两广军队数万人已渡过湘桂边境黄沙河,来势很猛,拟往岳阳、羊楼洞等地径赴武汉,李先生此行就是来商谈假道过境问题的。”
刘廷芳闷头一想,两广军队有十多万,而岳阳地区的中央军只有陈诚和胡宗南的部队,在人数上不占优势。如两广军头游说成功,获何先生首肯,使两广得以假道湖南进军武汉,则势必造成分裂之势……他力劝何键不要采纳。
“那就派你前往南京见蒋先生如何?请蒋先生设法制止两广军队发动兵变。”何键望着刘廷芳,征求他的意见。
刘廷芳还在考虑。
何键又说:“前几天我已派省政府秘书长易书竹去了南京,已经七天了,没有一字报告,可能蒋先生不见他。我思来想去,别人都不行,只有你去最合适。因为,第一,你与蒋先生相识,他对你印象很深;第二,蒋先生了解你的为人,并以为你很有作为,你的意见蒋先生容易接受。可以说,你是能面见蒋先生而又能达到预期目的的唯一人选。廷芳兄,南京之行,非你莫属啊!蒋先生给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的信不就称赞过你吗?”
刘廷芳不再犹豫:“可以。”
当下,何键派了专车,立刻把刘廷芳送到汉口,包了一架水上直升飞机飞南京。在飞机上,他就给蒋介石打了电报。一到南京,翁文灏奉蒋介石之命到码头迎接。他与钱昌照交往已久,认为他有远见,所以先去见他。然后由翁文灏陪同,来到蒋介石官邸。蒋介石正在隔壁房间与熊式辉、张群、陈布雷等人商谈事情。听说刘廷芳到了,蒋介石来到书房,会见他。刘廷芳先报告了湖南当时的紧张局势,以及何键派他来南京的目的。他还告诉蒋介石:“何先生说他是您蒋先生的弟子,您叫他朝东走,他不会朝西走的,你绝对服从您的领导。”
“那很好,那很好。”本来蒋介石正在担心何键关键时刻倒向两广军一头,听刘一说,顿时露出笑意。
刘廷芳继续强调:“现在的国家只有您蒋先生一人能领导,也许20年、30年后出一位领袖比您蒋先生能干,但现在不可预料。为国家计,为人民计,绝对地不要打内战,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如有不实不尽之处,我蹲在金陵不走,敢用头颅担保!”
一番话说得蒋介石心旌乱摇,连连说道:“不会,不会,不会。”
他立即挥毫写了一封信:“你马上送到汉口,面交武汉委员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及高级顾问何成浚两位先生。”又吩咐侍从黎秘书派“美龄号”专机送刘廷芳出发。
当刘廷芳将信交给杨永泰,从汉口返回长沙时,发现两广军队已在撤兵了。
原来被蒋介石买通的余汉谋、黄光锐一倒戈,两广事变就中途偃旗息鼓了。
蒋介石刚松了一口气,又接到特务密报,说西北情况复杂,恐怕要起变化。蒋介石问有什么证据,戴笠说:
“东北军跟红军打了几年仗,没有结下什么冤仇,慢慢地受了红军的影响,赞成抗日了。也难怪,他们老家都在东北,家乡给是日本人一占,家破人亡,不免思想报仇雪恨……”
蒋介石默然,又问:“当兵的,可以理解。当官的呢,高级将领的态度怎么样?”
“美国记者访问过张学良,他们在纽约《太阳报》登出来过文章,提到张学良表示过,他愿意团结抗日,如果政府失去民心,就无存在的基础。张学良甚至说,如果共产党能够诚意合作,抵抗外国侵略,就应该和平解决。”
蒋介石摇头:“汉卿少爷脾气,随便说说罢了。不过也不可等闲视之,我会注意这个情况。”
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蒋介石即召张学良、顾祝同、陈诚、薛岳、刘湘到四川开会,再次作消灭红军的作战部署。10月1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自兼总司令,调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当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这时的蒋介石已不能像当初那样,亲自指挥对红军作战,原因是日本对签订《何梅协定》的做法已不能满足,又在策动汉奸搞“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蒋介石怕日本人在北方另搞一个政府和自己对立,所以,10月7日由重庆飞抵开封,安抚驻天津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宋哲元及其部下。可日本人此时也正在拉拢宋哲元,宋举棋不定,不想见蒋,只派了一个秘书去开封见蒋。蒋介石又火速赶往山西访问阎锡山,劝说他不要参与“五省自治”,希望他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六中全会。
11月1日,六中全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一百多人。令蒋介石欢欣鼓舞的是,除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反蒋派的冯玉祥、陈济棠、阎锡山等都来了。
早上7点钟,大会代表依照惯例去紫金山谒中山陵,9点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由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中央委员们步出大礼堂,到会议厅门前等候照相。但蒋介石迟迟不到,大家都嚷着先拍。拍完了,委员们三三两两转身上台阶,往会议室走。突然一声大喊:“打倒卖国贼!”随着喊声,只见一个青年从记者堆里闪出身来,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六响左轮手枪,对着站在第一排正中、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枪枪命中,汪精卫顿时滑瘫在地。现场大乱。坐在轮椅上的张静江也被人推翻在地;孔祥熙在往汽车底下钻时,慌乱得扯破了新马褂……第一个起来和杀手搏斗的是站在汪精卫身旁的文官张继,他从背后把杀手拦腰抱住,抢上来的武将是张学良,他猛踢一脚,托起杀手的臂膀,下了手枪。这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杀手胸肺中两弹倒地。
蒋介石听到枪响,急忙下楼,走到斜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旁,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连连唤着:“兆铭,兆铭!”
汪精卫脸色苍白,大呼小喘:“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你要单独完全负责了。”
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瞪着蒋介石大吵大闹:“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蒋介石脸上青一块,白一块,他确实不知道这件事是谁干的,但又辩解不清,只好说:“你们放心,这件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他回到在中央军校的官邸,把汪派人物陈公博等人叫来,告诉他们:“这件事的确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你们要给汪夫人解释清楚,我蒋某人也不会干的!”他又把戴笠找来训斥:“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就让出现这类祸事吗?限你三天之内把指使者缉获,否则要你的脑袋!”
蒋介石更不知道此次行刺的目标就是他。
杀手叫孙凤鸣。是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的四个热血青年筹划的,为首的叫华克之。孙凤鸣在行刺前已服鸦片烟泡,在一定时间内毒性发作,不见蒋介石出来,临时决定刺汪的。他在承受肉体撕裂的痛苦时也没供出合谋者,只留下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还有中国的地方没有?再不打,要亡,要做亡国奴……”第二天,孙凤鸣平静地死去了。
戴笠后来探出是晨光社的华克之主使的,下令悬赏十万重金捉拿。沈醉亲自出马也没捉到。不料40年之后,在北京,沈醉被一位熟人介绍到一个人的面前。那人拉住沈醉的手问:“你还认识我吗?我的老朋友!”沈醉也算是记忆超群,可怎么也想不起此人是谁。那人哈哈大笑:“我就是你追缉多年的华克之呀!”沈醉大惊。原来华克之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力行三民主义。刺汪后,他于1937年进入延安,翌年经廖承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一直战斗在无形的战线上。与沈醉相见时已年逾八旬,两人相聚谈得十分投机。
“剿匪”不成,反蒋派又蠢蠢欲动,日寇又步步进逼,汪代蒋受刺,更招致责难的呼声,到了1936年,蒋介石的日子更是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