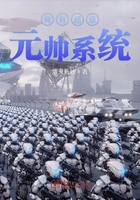不論世道的好壞,一切總需有個落腳的地方,慣常的人們習慣把它稱作“家”。
家本是個可以養豬、養牛,生兒育女的自由所在。自然的人啊、畜生的雜居期間,也就各自各的繁衍生息開來。
但需求的無止境,卻為此也添了許多的麻煩與功用。到頭來幾間茅草棚子便成了廣廈萬丈的源頭。
人總是溫飽思****的。
怎奈得開口閉口的就這樣姑且將息了?所有的安排似乎總是顛三倒四的混雜著。
好比吃喝天生就是“低級趣味”的東西,然而所有重要的東西,都不承認的自己出生的低級卑微。
所有稍有成就的“人物”,到頭來都需歸宗認祖,饗列宗廟。
這種把祖宗當祖宗的事——都可歸結到“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古論上去。
既然祖宗都是親的,兒女親不親又如何呢——依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便同理可證了,人的微妙就在於這點點差異的區別。
DNA親子鑒定的備注,是“妻吾妻以及人之妻”的限定因素。細細觀察才知道“兒女是債主”,不是債主為何如此殫精竭慮的細心供奉;“小東西”之於“老東西”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從此不難看出契約精神的影響深遠——一種基於“債權”與“信託”的厲害關系。是需要嚴格釐清關系順序的,為此兒女的親屬出處是甚需明確的,到底他的一般繼承順序是排在“老東西”之前的。
雖說孔夫子是個先賢,但到頭來終是個自欺欺人的先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天曉得什麼叫“思無邪”?
老先生的智慧,終有些掛一漏萬的地方;到也為那些仗著他老人家“搭夥吃飯”的尊家們,造就了無數宴集論道的機會。
不過這樣看來夫子于至聖先師之外,未嘗不是好的企業家。
文化創意產業肇始,亦可附會其身——幾句話創造的GDP是無可估量的慈悲善舉。
學術文章的繁榮,教授學者的成就。
謾罵詆毀的“書劍恩仇”,未嘗不曾為紙張的消耗,油墨的鋪張大行其道。一些依此附生的行業,更是造就了一條深遠的商業鏈條。
道德的分化,也許就是由自己的喜惡愛憎出發的。
心裡那些“分別心”一類的“小九九”,造就了人類的條條框框。
利益天生是如此,骨頭縫裡浸透了的根深蒂固;如同娘胎裡帶來的一副心肝腸胃,是容不得你輕易淘換說算的。
那種“祗許州官點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絕妙荒誕,是不可全然用“諱莫如深”就概況了的。
民主、民粹、民生的偉大,未曾不是建立在那種人心不古的利益討好中。
人是個愛好折騰、深於折騰、以折騰為導向的玩意兒;吃飯、穿衣、說話,怎麼都是在折騰中邁步闊進的。要不所謂高深文化、燦爛歷史,又何從談起。
藝術科學更是盡其所能的,折騰玩笑著全民的大腦與財質;政治的偉大,就在於他將戲劇的藝術,與諂媚神靈的魅惑神技,發揮的淋漓盡致。
這種歡悅的盛世浮華,與跌宕起伏的興衰成敗;一直以來就是以中飽私囊的人物變易為始終的。“天下為公”的事業,從來就是為“公”天下的治亂之制。
這種基於政治的博弈,未嘗不是一種表像的趨勢。刨根掘土,入地三尺;一種基於“性”的現象,為一切的一切,都做了蓋棺定論的題解——脫掉傳宗接代、開枝散葉的道統袞服。一個被光鮮性感的小兜兜所包裹著的美人,卻因這層遮羞布的襯映,顯現出紅白淡紫,美艷動人的嬌容媚俗。
裸體的禁忌似乎與服飾的發展,有著某種不可分割的聯繫。
出於對服裝史的興趣,我考證過服裝出現的作用——最初不過是為了適應氣候的變化,而後產生了審美的需要,最終引入了身份的識別。
為此它也自然的成為了一種表現與禁忌。由此服裝有了權利的意識,有了族群的分割。
對於原來純粹的裸露,一切相反的,成了另一種禁忌。其實裸體本身是自然的,不具有所謂的審美。
審美是一種傳染的,特定人群的意識喜好。
文藝復興為人本的回歸,開創了有利的機會;出於對這一思想的支持,也是對人的本身的探索與認識,人體的揭露與展示成了一種風尚。
現在所為“豔照門”的事件,本身就是個人的私隱。
人對於性的認識與追求,是一種自然的本能,是自然選擇的表現。
所謂公眾的人物,只需要在其公眾的範圍內,完成他的社會角色便可以了。至於他的個人生活無必要依從於別人的看法。
“食色性也”,想想我們的出處;沒有這些我們打什麼地方來到這個世間?
不要把所有自然的東西都社會化。那是一種對自身,乃至於自己所處的同一群體的反向裸露。
即使我們的隱性中都存在著所謂曝露性,但現實中未必就便充斥了曝露狂。
當我們去指責曝露時,是因為我們佔據了所謂的群體優勢,是一種以眾凌寡的表現。
當你出現在一個裸露的原始部落時,你本身也是另一種禁忌的體現。
所以如鄉隨俗。
這等事之所以如此的大為傳播,試想未必是出於當事人的本來意願。
它的氾濫,就在於媒體的強暴與無情。
是媒體強姦了所有普羅大眾的意願,
我們什麼也沒說。因為我們的發言,已經被更多的發言所掩蓋;忘卻相對記憶,顯得如此的喜新厭舊。
在進化的過程中,“天體運動”的出現未曾不是一種異端。
可是所有現在被承認的,大多哪個未曾不是異端呢?
想想高跟鞋、迷你裙,
當抗爭成了勢力,一切自然就是對了的。
奇怪的道德,就是所謂強勢的世道;
我們難以抗爭的莫名。
人對於自己身體的興趣,怎麼就見不得人呢?
壓抑的性觀念,卻不能壓抑本身對性的渴望。
對於異性本來的好奇在於他(她)的不瞭解與疏隔。
一種對於性的負罪感,只會增加對於性的錯綜複雜的認識,它的遺傳本身就是一種可怕的毀滅之路。
人對於道德的需求,是為了自發的維護秩序的常態。
而犧牲了性的常態能安定嗎?
我不是******的推動者,我只是贊成自然選擇與本性的正常延展。
我們都是些心口不一的傢夥,為著皇帝的新裝將自己埋葬。
想要的是自己的,但我們的無知往往葬送了自己。
因為禁忌與叛逆,可能將自己送上了一個不認識的人的床。
如果深切瞭解和尊重對方的需要,那可能真的是一種幸福。
但只是因為聽信了一些小圈子的私房話,失去所謂的初次,那到是次要的;只是對於心靈的期許將會大大受傷。
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對於性的趨向與意見。
只是這是純粹的自我。
找我要的,從而去尋覓合適的;不是因為人,而犧牲性的自私,那本身就是一種真真的罪過。
我們害怕指責,是因為善良?
如同我們被所謂的愛情,壓迫成了性的奴隸。
愛情是愛情本身。
愛情佔有而激發的自私,使所有都成了標籤的貨物,成了交易。
想想彼此的相愛是為什麼?
除去所有,
他(她)到底要了什麼?
我又做了什麼?
男人為了自身的純粹,期待女人的所謂純潔;而女人為了所謂的安全感,出賣了自己的心。
人從本身出發是一直的事,只是我們不去承認我們自己的虛偽。
什麼是“媚俗”?從來的“俗”,《說文》謂之“習也。從人穀聲。似足切”。看這個是隔靴搔癢,無關痛楚的。既是說俗就當俗解,一人一穀,吃喝拉撒、喝水屙尿、吃豆放屁,天經地義;約定成俗積久成習自然天成。
誰說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要知道內褲比外褲貴的大有人在,所謂財不外露。揣著明白裝糊塗,未必不是明智的表現。
一種變化中的不變信念,將國人一股腦的帶入了一個新時代,一個我正好趕上了投胎做人的年代。這或許是一種註定了的因緣,祗是一切都是如此平淡的沖和著。
作為一個與這時代共同成長的人,我沒有過多的發言權——因為從歷史的角度去審視,我也不過祗是其中的塵埃罷了——沒有指手畫腳的所謂“權威”;但這種不能超脫的悲哀,使我要盡力的去突圍。
但某種境況下,一個沒有圓滿的世界往往到真是圓滿的境界所在。我祗是隱約可以在意識裡捕捉到些許的記憶碎片,所有的拼湊可能到最後都難以說明我所處在小小前半生的世間。按佛家的講法一種因緣的生成,是彼此的關係的開始,是一種有因果的聯繫。
出於這種影響,我更多的開始用一顆稚嫩的心去完成一部新鮮的歷史。在這裡我不得不提及一種觀念——“新鮮的歷史”,自然的這是一種歷史,有若一種過去時的表達。可是它自身的講述方式卻是現在時的,如同意識流的溯洄,是一種潛意識的自然表述;它固然不在於歷史的縝密考據,或許一切祗是為了說明一種虛幻的真實感觸。
當時者為了盡力的還原歷史而編纂的真實人生,可大概在他人看來,最多既是所謂的“影射”而非真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