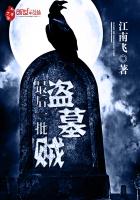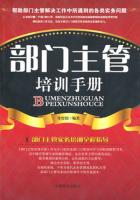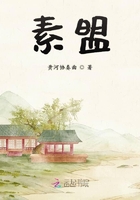我久久地注视着这尊铜像,心灵受到极大的触动。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安徒生的作品,因为它与安翁的追求相差甚远。然而我却从盖费昂女神的身上找到了人类的影子。人类啊,谁都在嘴上高喊着爱,高唱着施舍与和谐,可在骨子里面,有谁不是在恃强凌弱、唯利是图呢?我并不信教,可我却下意识地、异常虔诚地在胸前划着十字,祈祷着人类改恶从善。我想人类只有放弃争斗,和谐共处,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安宁。只有人人都尊重爱,享有爱,创造爱,世界才会充满爱。因为对于人类来说,物质的需要总是相对容易满足的,而精神的需求却是永恒的追求。文治武功,你争我夺,所获得的只是人本身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利益,而失去的却是难以获取的精神需求。须知精神需求,获取固然不易,一旦失去了,要重新获取又是何其艰难呢?
我深知,人类进入理想的境界,还有太远的路程,人类追求理想的境界,却是随时可为的,因为我们拥有童话。在童话里,这个境界已为安徒生等大师们描绘得活灵活现,只等人们去争取它、实现它。
离开市政厅时,友人要我在留言簿上写句话,我本想自己乃无名之辈,附庸风雅题什么词?正自嘲时,突然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是那么强烈地鸣响,使我顿时产生了写下它的欲望,于是便欣然提笔,在那个厚厚的、可能永远也无人注意的本子上写下了这句话:
人类应该回归童话!
2007年10月1日作于丹麦哥本哈根
瑞典—经典
历数北欧古国,瑞典可能算得上典型的一个。它建国于12世纪,距今已逾千年。瑞典的皇宫为欧洲最大的皇宫之一。这个曾显赫几百年的巨大宫殿,如今已成为瑞典王室历史展览馆,各种宝藏应有尽有,特别是12顶星冠及其权杖,总是那么默默地闪耀着无价的光芒。
走进瑞典,给我的感觉是一切都是经典的。我们从西北边的挪威进入,长驱530公里,直抵首都斯德哥尔摩,沿途的旖旎风光,叫人惊叹不已。时值深秋,漫山遍野的枫树正在由绿转红,与长青的针叶林一起,构成了绿、黄、橙、红间杂的斑斓画卷。尤其是当我站立在瑞典最大的内湖—维纳思湖边的时候,山水一体,恰似一位婀娜多姿的北欧少女,在尽情地展示着她的清秀和妩媚。微风拂起,带着一阵雅香,直熏得人陶醉。
斯德哥尔摩堪称北欧的威尼斯。它由14个大小不等的岛屿组成,54座风格各异的桥梁把岛屿连成一体,使整个城市犹如一串靓丽的珍珠,镶嵌在波罗的海边上。徜徉在老城的大街小巷,我真的不断地在为这里的古老建筑叫绝。所有的楼房,几乎都是宝贵的艺术珍品,造型是欧洲的典型风格,配以哥特式或巴洛克式的屋顶辉映其间,构成了水陆相绕、树林与建筑相间的幅幅画图。看皇宫,它精巧别致,典雅端庄,至今还保持着每月一次的宫廷卫兵交接仪式,那是个气派非凡又相当繁琐的仪式,皇宫军乐队在广场上足足要行进表演一个多小时,引得观众成千上万。出皇宫,约行三五公里,便是皇后岛,这里的宫殿庄严雅致,红墙黄瓦,金铂镶边,宫前是一片硕大的草坪、森林,宫后是一行人物雕塑,细致精美,惟妙惟肖。皇后宫的东边是梅兰湖,足有数十平方公里,把整个皇后宫衬托得如同一个温和安详的公主。而不远处的尤根王子花园,则又是另一番景致,岛上的建筑小巧玲珑,别有风味,有些现今用作艺术展厅的小屋,简洁中隐含着高雅,精华处体现出大方,与岛上错落有致的树木草地一起,浑然成了内涵丰富的艺术殿堂。其城市建筑的精细做工也令人由衷地赞叹,所有的建筑物你都几乎难以挑剔出毛病。我从心底里感叹,这要在中国,每个建筑物都可评上鲁班奖!
当然,说瑞典的经典,自然远不止它的自然风光与建筑技艺,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内涵。一个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罢,文化的积淀始终是它赖以立足的支撑。瑞典的文化是古远的,也是深厚的,它有古老的斯堪森露天博物馆,展示着本民族的民俗风情;有斯德哥尔摩老城,这一中世纪城镇,至今犹如人们心中的圣地,被爱称为“宝岛”;还有宗教的殿堂—斯德哥尔摩大教堂,年复一年地传颂着皇室加冕大典的盛况。更为举世闻名的,是著名的诺贝尔奖颁奖地这一经典之地。诺贝尔当年确定五大奖项,除一项文学奖放在挪威的奥斯陆颁发外,其余四项均放在斯德哥尔摩。颁奖的地方是音乐厅—一座蓝色的方形建筑。我们前往参观的那天,正在上演一场音乐会。我发现,在检票进场的人海中,不乏手持鲜花的男女。捧着鲜花听音乐,应是一种高雅的情调吧。诺贝尔奖颁奖晚宴是最受重视的活动,安排的地址也非同一般,放在市政厅里。市政厅的中央大厅又叫“蓝厅”,据说以前这里没有建屋顶,人们在里面抬头便能见到蔚蓝色的天空,故此得名,可后来还是加盖了屋顶,虽然看不见蓝天,但蓝厅的叫法一直未改。晚宴是浩大的,每次都有三千余人。一个仅千把平方米的大厅里,要坐下这许多人实在不容易,于是只好分为三等:一等贵宾安排在正中长条桌上,每人可拥有80厘米的座位;二等宾客坐在四周,每人仅60厘米;三等的就只能安排在两边的厢房里了。想来这餐饭,对很多人来说真是受罪,但与这一殊荣相比起来,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我刚惊叹于诺贝尔颁奖晚宴的盛况,顺楼梯上到二楼,却又被另一番景象折服了。二楼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场所:斯德哥尔摩议会厅。每年几次的市议会在此举行。观看其会场的布局,倒没有多少特别的地方,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差不多。无非是议长在最高位端坐,中间一圈是重要人物—部长。四周为三百多名仪员席位。两边阁楼上,一边为媒体席,一边为旁听席。据介绍,斯市的大事由议会作决策,而议员都是兼职的,都有其一份谋生之计。因此,这里的议会每次都安排在下午4点召开,且在旁边特意安排了一个婴儿室—好让携儿带女的议员寄放小孩。斯市还有一“奇”,就是没有市长,只有几名打理市政的部长。实在需要,比如有外交活动,需对等接待时,就临时指定一位部长代行市长之职。我对这些饶有兴致。这些在另一些地方简直不可思议的事,在这里却是如此正常,如此有序。一个不设市长的城市,一个连议员都是兼职,无工资可发的议会,城市建设却异常先进。论环境,这里治安良好,工作有条不紊;论实力,这里人均年GDP高达4万美元,是全欧洲福利最好的地方之一。我想,民主政治的建设,究竟有些什么内容?大社会小政府究竟要怎样付诸实行?我们是不是从这里能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呢?
傍晚,我们乘坐“维京(Viking)”号客轮离开了斯德哥尔摩。站在船舷边,望着渐渐远去的城市,我突然想起,“维京”的意思即海盗。瑞典不正是一个由海盗占领而演变过来的国家吗?只要治国有方,海盗一样可以造福于民啊!恰如这艘豪华客轮,号叫“维京”,可它的豪华和一流的服务谁不赞赏呢?
2007年10月6日作于赴芬兰赫尔辛基途中的“维京”号客轮上
古堡遐想
屈指一算,很有意思,跑了一整天,竟然是看了四个古堡:丹麦的夫雷登堡、克隆堡,瑞典的赫兴堡、哥德堡。
“堡”在欧洲是多见的,很多也是著名的,譬如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德国的汉堡、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等等。我想堡的原意应与战争是分不开的。建筑坚实的城堡以御敌入侵,这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管用的一着。因此,每个城堡几乎都建设得异常稳固,易守难攻。周边往往还挖有护堡河,吊桥挂起,令敌人插翅难飞。这便是历史残酷演绎的实证。试想众多“堡”的矗立,能给我们后人以什么启示呢?我想到的是在堡的内外,不知埋下了多少白骨,洒遍了多少鲜血。彼此的争斗,无论谁胜谁负,在几百年、几千年后的今天,不都成了参观者的一声叹息么?顶多再提供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不过对于夫雷登堡来说,却有些与众不同。据说它是丹麦女王为制止战争而别出心裁建造的。历史上,丹麦王国与近邻的瑞典王国曾进行了多达22次战争,两国胜负各半,势均力敌,然而最终却以丹麦的割地赔款了事。我们跨过波罗的海海峡后,沿欧洲6号公路前行了二百多公里,直到哥德堡,这些都是在战争中瑞典从丹麦手里夺走的。如今丹麦国土面积仅剩四百多平方公里,而瑞典却有四千多平方公里,是丹麦的10倍!这不免令我这个局外之人欷歔不已。多年的战争,使两国人民深受灾难,也使丹麦宫廷精疲力尽。正是出于对战争的厌恶,女王才在与瑞典朝廷握手言和后,倡议建造了这个城堡,目的在于告诫后人:我们不要战争,从今往后要爱护和平,一心搞建设,一心求发展。而这个城堡便也成了女王的后宫,人们又把它称为“和平宫”。
和平宫的规模不算很大,大体与“美泉宫”相似,也是前面一座宫殿,后面一个大的花园。区别在于美泉宫是开放的,而和平宫是封闭的,前后左右均有宫廷卫兵守护,游人不得入内。在导游的引导下,我们一行人沿宫外的小道走了一圈,花去了半个小时。放眼望去,宫堡内外,都是一片绿色,大树参天,绿草铺地,鲜花盛开,层林醉染。在林间散步,别有一番风味。据说直到今天,这里都是丹麦王宫的重要活动场所,美国总统布什还到这里过过生日哩!
离哥本哈根约四五十公里的地方,便是北西兰岛的顶端—赫兴市。这是一个仅12万人口的小市,隔海与瑞典遥遥相望。岛的东北角上,便是著名的克隆堡,因为莎士比亚曾以哈姆雷特为原型,在这里创作了名剧《王子复仇记》,所以这里又叫哈姆雷特堡。久而久之,哈姆雷特堡的名声反而盖过了克隆堡,叫开了,叫响了。
哈姆雷特堡的牢固程度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周遭竟有三道水沟作为堑壕,底部一圈是厚厚的石墙,砌有射击方孔。三层高的城堡,坚固得无懈可击。几个高低不等的尖顶刺破青天,使整个城堡傲然屹立,无人可敌。我注意到了城堡上,至今还整齐地排列着九门火炮,齐齐地面对着波罗的海。这里是大西洋通往北冰洋的咽喉要道,古时有这九门大炮扼守,足可抗击来往战船了。
沿古堡走来,我对哈姆雷特及其王室的争斗一幕倒兴趣不大,而对这个城堡的建造却想了很多。是呀,古时的丹麦,在欧洲可是首屈一指的大王国,可在与邻邦的争斗中,锋芒失尽,锐气大伤,堂堂大国仅剩下了几个小岛,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令人心痛的。后来者的唯一办法,恐怕也只能是拼全力扼守要害,以防一失再失了。这是不是建造哈姆雷特堡的真正含意呢?我终是不得而知。不过历史发展到现在,古堡的作用早已废掉了,堡内到处是存放《哈姆雷特》剧中道具服装之所在,还有就是商业行为的充斥—旅游商品琳琅满目。堡的东北角塔尖上,倒是装上了一个红色的灯塔,用来指引过往海峡的船只—为和平发展发挥作用。那九门大炮据说还有用处:曾为丹麦王室喜得子孙而鸣放过21响。
古堡现如今呈现的是一片安详,在它的注视下,赫兴城温静地迎接着游客。海滩上,几位垂钓者静静地等着鲟鱼上钩。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与海浪嬉戏欢歌。堡外的小饭馆门前,几位老者领着小孙子辈,排开长条桌,悠闲地享受着刀叉之乐。10月的太阳洒下一片温暖,催得城堡周围斑斓鲜艳,树林显出了五光十色的景象。小屋的墙上,爬山虎正由绿转红。远处田野里,收割牧草、打捆草包飘过来阵阵花香草味,令人迷醉,教人忘返。多么美好的日子啊,目睹这一切,回忆曾经的风霜雨雪,古堡啊,你在作何感想呢?
渡过波罗的海的厄勒海峡,上岸就是赫兴堡,赫兴堡已成为这个市的市名。不过赫兴堡至今还在,只是它与对面的哈姆雷特堡相比起来,小得多也简单得多了。登堡眺望,小市镇尽收眼底,海峡一片繁忙,两艘庞大的渡轮不停地往返于两国之间,迎送着为名利而忙碌的人们。两岸对比,已无所差别,仅从国旗的不同花色上可以辨认出:红白相间的是丹麦,蓝黄相间的为瑞典。
下午经长途奔驰,我们到了瑞典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据说从前这里并没有城镇,瑞典与丹麦战争期间,瑞典一路挺进,占领了厄勒海峡以东的大片土地,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立马此地,发现这里有着良好的港口条件,便勒马横剑,右手一指地下,大声宣布:我要在这里建一座城堡!于是便有了哥德堡。哥德堡以海的城市自居,尊奉海神波塞顿,在市中心的文化广场上,至今海神一手抓鱼一手托蚌的雕像还屹立在广场中央。哥德堡不仅是瑞典的老二,而且还是北欧第一大港口、第一大工业城市。它有人口四十多万,据说实际已达七十多万,拥有二十多公里长的货运码头,年吞吐量有三千万吨。这里还是著名汽车VOLVO、世界电信之王爱立信的生产地,其钢材产量、质量均闻名全球。另外,这里的发明创造也令世人敬佩,比如活动扳手、汽车的保险带、气囊等,都从这里走向世界,成为人们生活之必需。所有这些,都使我对哥德堡刮目相看,此“堡”已非彼“堡”,但愿它在和平发展中,不断创新,不断进步。
参观四个堡,使我浮想联翩。堡的兴衰总是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呈现的。堡兴则意味着战争、灾难,堡衰则预示着和平、发展。当然,到了当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已使军事手段飞速发展,“堡”已演化成了足以摧毁人类文明的巨大灾难性恶魔。这些新的“堡”们正在危害着人类,成为世界抹不去的阴影。善良的人们总是在呼吁,不要“堡”,要和平,要稳定,要发展。我们期盼着,希望一切的“堡”们,都尽快失去它们的本义,丢弃它们的功能,成为供人参观的摆设,成为警醒世人的警钟。到了那时,世界没有威胁,人们没有恐惧,一派歌舞升平,万众齐享和谐,该有多好!
2007年10月2日作于瑞典哥德堡
静听涛声
到美国不去圣迭哥是不是件憾事?反正到了之后,你一准觉得不虚此行。
圣迭哥真的很美。她有着良好的海滨天然环境。辽阔的太平洋把万顷碧波送到这里,却被马鞍形的克罗拉多岛温柔地挡住,尔后又把波涛调成万种风情,在温暖的港湾里来回嬉戏,醉倒了无数的游人。从克罗拉多岛回望圣迭哥,便有如远眺一位多情的妙龄少女,你会对那些错落有致、高雅飘逸的建筑发出感叹,你还会对港湾里点点白帆迎风起舞嗟叹不已,倘若瞟一眼不远处沉默着的蓝灰色航空母舰的雄姿,你更会为这位女郎的安详幸福而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