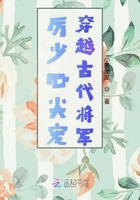从那以后,每天打水的就是妹妹了。估计爸爸要到家了,妹妹就打好水蹲在厨房里,只等爸爸那一声“兔崽子呢”,她就挺着肚子冲出来。等妹妹到了面前,爸爸接过水问她:“想爸爸吗?想!爱爸爸吗?爱!有多爱?”这时,妹妹就会挺起胸脯,把两只小胳膊伸开老远,做出拥抱全世界的样子,说:“这么爱!”爸爸最喜欢妹妹这个姿势,每天回来都要进行这段对话,为的就是在最后能欣赏到她这个姿势。
妹妹3岁那年,被爸爸妈妈“赶”了出来。爸爸在我的小床上加了块板子,这样妹妹就有地方睡了。我们家房子很小,除了用土砖搭的厨房、杂屋,就只有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瓦房了。妈妈常跟爸爸说想加一两间房子,不过每次爸爸都没答应。
有天晚上,我听到妈妈说:“趁现在天气好,还是把房子盖了吧。你总不能老让他们挤在一起吧?”
爸爸叹了口气,说:“还是等下半年吧。兔崽子马上要初中毕业了。别看他不说话,一心想考市里的一中哩!这个钱不能少……”
我听爸爸说这些,眼泪忍不住流出来了。考一中这件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爸爸竟然这么清楚。原来,我也是兔崽子!爸爸仍然只是逗妹妹玩,很少跟我说话,但我的心情从此明亮多了。
我没有让爸爸失望,夏天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当天晚上,爸爸准时回来了,进门还是叫“兔崽子呢”,于是妹妹端着水冲出来,不过这次没等爸爸开口妹妹就先报喜了:“爸爸,哥哥考上市里的一中了!”
爸爸听了好像没什么反应,对站在一旁的我视而不见,还是继续跟妹妹说话。妹妹又摆出了她拥抱全世界的造型。在欢声笑语中,爸爸看了我一眼,这唯一温柔的一瞥令我毕生难忘。
第二天,爸爸回来得晚些,手里多了个大塑料袋。妹妹在厨房里腿都蹲麻了,才听到一声“兔崽子呢”,冲出去的时候差点摔一跤。爸爸接过水,并不急于洗脸,他故意在袋子里掏来掏去,逗妹妹踮着脚在那里翘首以盼。
晃了半天,爸爸掏出一件连衣裙,是给妹妹的。裙子颜色鲜亮,有漂亮的小碎花,好看极了,我真难以想象大老粗的爸爸还有这么好的审美眼光。
妈妈接过裙子,很利索地给妹妹套上。因为裙子太长了,拖在地上,看上去很滑稽,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这时,爸爸把那个大塑料袋递给我,打开一看,是个新书包!这是爸爸第一次给我买礼物,我想说句感谢的话,却始终没有说出口。
第二天快收工的时候,爸爸头顶的煤层突然塌方,他被埋起来了。
傍晚,几个人到我家报信。他们还没说完,妈妈就晕过去了。大家慌忙展开急救。看着眼前乱糟糟的景象,我却显得异常冷静,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我突然想起了妹妹,她一定还在厨房。
我走进厨房,妹妹还死死端着一盆水,蹲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的眼泪如决堤之水,顿时涌了出来。
“起来吧,爸爸不会回来了。”我蹲下身子。
“会回来的!他还没叫我兔崽子呢!”妹妹倔犟地不肯动,但眼泪已流了出来,一滴一滴,都掉在她的小盆子里……
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后来老板赔了三万八。靠这些钱,一家人的日子还算过得去,我也在市一中读到了高三。
在高三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回了趟家。妹妹在村口等我,我很远就认出她,因为她穿着那件鲜艳的小碎花裙。现在,那裙子正合身。
在一个小土包上,妹妹突然停了下来,望着对面山腰上的洞口出神。那是爸爸曾经工作过的矿井,现在已经废弃了。我们默默地站了很久,回想着以前的事。
“哥,你想爸爸吗?”妹妹轻声问我。
“想。”
“有多想?”
“很想,很想……”
我单膝跪地,看着妹妹伤感的样子,忍不住鼻子一酸,紧紧抱住了她。
天生我才必有用
父亲在我尚没有真正踏上人生旅途的时候就离我而去,现在已经20年了。
父亲走后的多年里,我在生活的海里沉浮飘荡,他不怎么入我的梦,昨日夜里,我忽然见到了他。父亲身穿青袄,坐在地头的榆树下,口中叼着烟袋,我似乎知道他已是隔世之人,问他:“你还好吗?”
“我在那边还种地。”说罢,转头向田里走去,留给我的是若有若无、缥缥缈缈的影子。
我撵他,可腿迈不开步子;叫他,却喊不出声。在惊悸中醒来,秋夜正浓,半轮月儿在天,四周一片寂静,我不能再入睡了。
我踮着脚离开寝室,走进书房,默然地坐在书桌前,父亲生前的影像便浮现在眼前。
那年,父亲近60岁了,又患了肝病,他骨瘦如柴,虚弱无力。那时,我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已成家了,只有刚结婚的小哥同我和父母一起过。小哥的媳妇看到父母年老又有病,不能做活,我又读书,觉得同我们一起过是吃亏的,因此,对供我上学是颇不情愿的。父亲为了证明我们三人不全是吃闲饭的,就硬撑着下地。
那年秋天收土豆,嫂子说忙不过来,执意要我回家秋收,我不敢违拗,只好请假回去。我怕落的功课太多,做活的间隙,看了几眼书。哥嫂不乐意了,怨我的心思不在做活上,有气的哥哥抡起鞭子使劲地打那头拉犁的年迈老牛,眼看鞭子就要落到我的身上。父亲脸色青黄,大口喘着气,他从哥哥的手中拿过鞭子,扶着犁杖向着地的那头走去。犁杖太重了,病得一阵风就能刮倒的父亲,被犁杖带着踉踉跄跄地往前跑。瘦削的父亲架不起衣服,宽大的黑褂子在风中一飘一飘的。父亲像一个影子人,飘荡在苍茫空旷的天地间,跑了两条垄,就一头栽倒在地上了,此后许久起不了床。
深秋的时候,学校放了几天假,让我们回去拿换季的衣服和准备冬天烧炉子的柴火。
镇上中学离我们深山里的小村子有50里山路,我走了大半天,午后的时候才赶到家。父亲不在,患眼病的母亲在摸索着剁猪食,母亲说父亲到北蔓甸摘草穗去了。我匆匆吃了口饭就去找父亲。我登上山顶时,已到夕阳落山的时刻。塞外的秋天,风霜来得早,8月的草洼,已呈现凋零之势,青的草已变成一片苍茫的白色。这草是碱草,细高的秸秆上都挑着个穗子。当年,镇上的货站收购这种草穗,说是到沙漠去播种,也有人说是喂种马。乡里人都满山遍野地采这种草穗,这山顶也早已被人采过了,多数的草茎上都已没了穗头,只有晚长起来的或人们采摘时从指间遗落的,稀疏地藏在草棵中。
我站在草洼边,四处张望着寻找父亲,许久,我发现远处苍茫的草丛中有个小小的黑点在蠕动。我奔着那儿跑去,走近了,看到了父亲。他背对着我,身穿一件青夹袄,腰扎一根用黄色的羊胡草挽成的草绳,怀前是一个系在草绳上的小木筐。他弓着腰,头低在草丛中,白草在他的头顶上飘摇,他的两只手扒拉着草棵,寻找着草穗,直到我走到身边,他才发现了我。
“回去吧,天快黑下来了。”我说。
父亲停下手,他怀前的木筐里有大半筐草穗。父亲的脸色青中透着层暗黄,发白的嘴唇裂着血口子。父亲把筐里的草穗装入袋子里,用手掂了掂,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这些卖了,够你交学费了。”
父亲无力地瘫坐在地上,说得吃一口东西才能下山,要不就走不动了。他打开手巾包,里面是母亲烙的两张饼,他咬了一口饼,饼干硬得咽不下去。父亲站起来,用石片划破一块桦树皮,很快那小小的洞口就渗出细密的水珠,父亲舔了几口,才又接着吃干粮。我的眼里涌动着泪水,我说:“我不想读书了,你也别再受这累了。”
“不算啥,只要我能动,就能供你。”他又说,“人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你那么喜爱书,学得又好,咋也得把书念下去!”
这次上学走的时候,我难以启齿地告诉父亲,学校要交冬天烧炉子的柴火,交钱也行。父亲说,不犯愁,过几天送柴去。
初冬一天的下午,父亲来了,他赶着牛车,拉了一车柴火,都是一小捆一小捆的。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是父亲一捆捆从山上扛回来的,他没力气,每次只能背两小捆。老师看父亲吃力的样子,招呼一些男同学,帮助我把车卸了。父亲蹲在墙角,灰黄的脸上挂着感激的笑。
卸完车,父亲让我跟他到镇上去一趟。他送柴火,也把那些草穗拉来了。
我们到镇上的货站,卖了草穗。我看父亲脸色已冻得发白了,就说去吃碗馄饨,暖暖身子吧。父亲说不用,一会儿就到家了。他把卖草穗的18元钱全给了我,又从青棉袄里襟的小兜子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21元钱,他叮嘱我一定要拿好,并告诉我这钱是悄悄地给我攒下的,不要跟别人说。
我的心苍凉而沉重,有说不出的酸楚,我把父亲送出小镇,过了白水桥,就是通往家乡的山路了。
父亲站住了,说:“你照管好自己,以后遇事要往前想,就总有奔头!”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我。说罢,他转过身,手牵着牛的缰绳往前走。父亲与黑牛并肩走在空旷的山路上。寒冬的风呼呼地刮动着,父亲只穿一件黑棉袄,外边没有皮袄大衣之类的遮寒,他弓着身子,一只手牵着牛,一只手遮在额前挡风,吃力地往前走。我望着他一步步走远,后来我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眺望,视线里那凄寒的背影,渐渐变成一个黑点儿,一会儿就融进苍茫的暮色里了。
不想,这背影竟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的记忆。父亲回去不到十天就去世了。
父亲死后不久,我的书就没有办法念下去了,从此我被命运沉入生活的海中,上下漂浮,左右奔突挣扎,受尽了风霜浪打,可在漫长的求索旅途上,眼前总有个影子,耳边总有个声音对我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是这影子、这声音使我在任何艰难的境遇下,永不言弃、百折不挠,坚定地向着心中的目标远行。
生活不辜负我,我终于实现了用文字铸造事业的梦想。
今天,父亲入梦,勾起了我点点滴滴的忆念。可父亲留给我的记忆仍旧是模糊的:他的笑容是模糊的,他的喜怒是模糊的,就连他的面庞似乎都是模糊的;而留在记忆中最深切的仍是那身着黑衣的、踉跄而凄寒的背影!
爸爸给我扎小辫
元旦前夕,红苹果幼儿园学前班在小礼堂举办联谊会,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都来了。看着小宝宝的精彩表演,家长们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
表演快要结束时,主持人李老师微笑着说:“各位家长,下面是一个互动娱乐节目,节目的名字叫——爸爸给我扎小辫!请女同学的爸爸做好准备……”
李老师的话引起台下一片哗然,再看那十几个女孩的爸爸们,表情各异,但大多数是满脸的不自在,有的干脆低下头,悄悄请教身旁的“高手”去了。
“请爸爸们不要紧张!”李老师仍带着微笑,“我们的规则是:看谁能在5分钟之内把宝宝的小辫子拆开,然后原样扎起来。哪一位爸爸扎得最快最好,将会获得我们特制的‘爱心爸爸证书’。”接着,李老师转过身对孩子们说,“小朋友们,我们一起为爸爸加油,好吗?”
“好!”孩子们高兴地回答,用稚嫩的声音齐声高喊,“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尤其是那些小女孩,更是兴奋得又蹦又跳。她们排起队,等待自己的爸爸上台。
第一个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她爸爸似乎很在行。只见他让女儿坐在板凳上,然后有板有眼地半蹲着,三下五除二去掉皮筋,不一会儿就把辫子解开了。看来这位临时抱佛脚,请教了妻子两招。不过,紧接着可就露马脚了!嘿嘿,解开容易编起来难哟!等好不容易批出一条歪歪扭扭的缝儿,下一步却无从下手了。只见他左也不对,右也不对,窘得满头是汗。时间到了,本来乖巧的羊角辫让他弄得乱糟糟。小女孩撅着嘴,气鼓鼓地说了声“笨爸爸!”,便不理他了。
第二位爸爸更离谱,拆开辫子后连皮筋都扎不上,还一不小心揪了头发,女孩当场就哭起了鼻子。第三位、第四位……等爸爸们挨个上了台,再回头看看这些可爱的小女孩:个个头发一团糟,小嘴儿撅得都能挂上酒瓶喽,真把宝宝们折腾得够呛呀!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女孩的爸爸还没上场,也只有她的头发还算规整,但保不准一会儿也就“披头散发”了。
“刘婷婷!”
“到!”女孩欢快地跑了上来。
李老师知道,整个学前班就数刘婷婷的头发最难梳,不仅又长又软,而且还是天生的自来鬈儿。别说她爸爸了,就连李老师自己都扎不好。所以,等婷婷的爸爸上了台,李老师委婉地劝他“弃权”。可是婷婷的爸爸笑了笑,没有作答,而是轻轻地拉着女儿坐下。“婷婷,爸爸今天不讲故事,只梳头,好吗?”婷婷听话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情景让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只见婷婷的爸爸娴熟地解皮筋,松辫子,梳理头发,然后一丝不苟地扎起了辫子。他粗糙的双手显得那么灵巧,真不可思议!细心的李老师还发现,爸爸给婷婷扎的还是四股辫呢。一会儿工夫,辫子扎好了,比原来的还要漂亮。随着李老师一声“时间到”,台下不知谁带头鼓起了掌,顿时,掌声响遍了整个礼堂。
李老师走上前,递过一本证书,说:“婷婷爸爸,给您,这个‘爱心爸爸证书’您拿之无愧!”婷婷的爸爸接过,正准备下去,却被李老师叫住了,“请等一下!”李老师调皮地眨了眨眼睛,“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从小到大,婷婷的辫子都是您扎的吗?您怎么能剥夺爱人的‘权利’呢?”一句话,引来一片笑声,大家疑惑地盯着坐在后排的婷婷妈妈。“不不不——我爱人——我——”一着急,婷婷的爸爸连话都说不利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