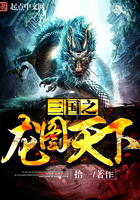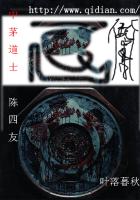从心理学的角度,结合诸葛亮的幼年经历,我们可以认为,诸葛亮在青少年时代,就对生与死进行过深层次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生死观。也许,在心灵深处,诸葛亮对生命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宣泄的,可能就是这种悲天悯人的生死观。这种情怀可能是日后诸葛亮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屡次北伐,不惜鱼死网破的情感基础。
诸葛亮年少时,每每自比管仲、乐毅,从小就要做生命的强者。基于年少时的生活经历,结合“二桃杀三士”故事中强者的覆灭情景,少年诸葛亮的生死观是独特的。
观念包含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生死观是一个人对生与死的认识和态度,这种认识和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目标取舍和道路走向。人生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死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生死观,其他什么“观”都无从谈起。只不过,生死观尤其是死亡观,往往存在于人的潜意识层面,平时也鲜有论及而已。
没有死亡观的人生观,是残缺不全的。生的艰难,死的无奈;生的乐趣,死的恐惧;生的喧闹,死的沉寂,都是每一个人必须直面的。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只是一个过程,只是种族延续的一个环节。生是这个环节的开始,死是这个环节的结束,也是为早已诞生的或即将诞生的下一个环节让路。开始和结束一样重要,死亡也就和生存一样重要。既然死亡和生存一样重要,那么,死亡观和生存观也就一样重要,死亡教育就和生存教育一样重要。
当然,诸葛亮跟普通人不一样,他是聪慧的、深邃的,用不着老师授课,就能体悟到生与死的真谛。
诸葛亮深知生的艰难,所以,他选择一种怪怪的方式生存——带着自己的生产建设兵团,远离首都和君主,偶尔打一仗(八年五仗),小胜或小败间隙,则演兵讲武,开荒种地;也算是忙里偷闲,战时休闲。
诸葛亮深知死的无奈,所以,他(下意识地)选择一种非常的方式死亡——一个政权的最高掌权者,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死在前线军营中。一方面,用如椽大笔,饱蘸自己的心血,为生命画上一个苍凉的句号;另一方面,拼上老命残躯,殉了自己的理想(至少在形式上),无论对蜀中父老,还是对子孙后代,都有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
本书第一集论述魏延之死时说到,性格即命运。本集还要抛出一个“谬论”:选择亦命运。性格影响人生道路的选择,但左右人生选择更重要的,是人生观,尤其是人生观中的价值观、权力观、死亡观。
用行为阐释“选择亦命运”这一原理,最耐人寻味,又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秦朝宰相李斯。
李斯是战国时楚国上蔡(今河南省漯河市)人,年轻时是楚国的基层公务员,干过仓库管理员之类的低级职务。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又脏又臭,瘦不啦叽,见人则仓皇逃窜。仓库里的老鼠,吃得油光发亮,肠肥脑满,见了人神态安详,不逃不窜。
不愧是荀子老先生的高足,年轻的管理员观察日常所见,醍醐灌顶,顿开茅塞,得出一个影响他终身的结论:人与老鼠一样,贤能不贤能是其次的,身份地位和生活待遇主要是大环境决定的。哪怕做个老鼠,也应该做仓库里的老鼠,而不能做厕所里的老鼠。于是,年轻的公务员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我们暂且称之为“厕鼠仓鼠论”。
于是,这个姓李的小公务员便打点行囊,西入咸阳,到当时最强大、最开放、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秦国,谋求发展。就像如今的青年男女,远涉重洋,追寻美国梦一样,当年的小公务员,也去追寻自己的“秦国梦”。
李斯到了秦国,凭自己的才能和政治导师吕不韦的提携,终于混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秦始皇死后,为了保住自己在“仓库”里头号大“硕鼠”的地位,李斯协同赵高篡改秦始皇遗诏,废扶苏,立胡亥。后被赵高陷害,夷灭三族。临刑前,李“仓鼠”抱着儿子,老泪纵横:“儿啊,我们父子,现在就连想回上蔡老家,到野外打打野兔,也不可能了。”
李斯年轻时摒弃当“厕鼠”,选择当“仓鼠”,仕途果然红灯高照,一路高官厚禄。成了“仓鼠”之后,进食多,运动少,自然身体臃肿,行动不便。仓库是有门有窗的,当然不能随便、轻易逃窜。怡然自得、看着满屋子粮食担心无法享用完毕时,突然来了位心狠手辣的仓库管理员(赵高),妻儿老小被一锅端,还祸及三族。
一个偶然的发现,一次灵感的顿悟,一个早晨的离家,造就了人生的辉煌过程,也注定了人生的悲惨结局。
考察诸葛亮的人生道路,他诠释“选择亦命运”这一原理的行为,刚好与老前辈李斯相反。这种相反的选择,又会是如何的一种结局呢?
致命选择
诸葛亮当时的人生道路选择,演绎出一个妇孺皆知的典故:三顾茅庐。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正式出场,在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其实,第三十四回“蔡夫人隔屏听密语,刘皇叔跃马过檀溪”就为诸葛亮的出场铺垫、渲染。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个章回的内容,都是为诸葛亮的亮相做准备的。刘备飞马过檀溪,大难不死,隐隐有大难不死必有贵人相助的气息散发出来。逃难途中,夜宿南漳村,巧遇司马徽(水镜先生),单福(徐庶化名)擦肩而过。接下来,单福新野投明主,略施小计,不世名将曹仁、李典一败涂地。不幸单福老母被曹操掳至许昌,单福救母心切,辞别新主,临行前表明身份,走马荐诸葛。
那还了得!卧龙先生的粉丝单福,竟有如此能耐,可见卧龙是怎样的一条龙!卧龙要闪亮登场了。掌声、口哨、挥舞手中的烛光……且慢!
徐庶走后,司马徽放下大隐士的架子,再次登门向刘备恳切推荐卧龙。刘备便屈尊前去拜访诸葛亮。第一次,恰巧碰到卧龙的好友崔州平,刘备被崔州平没好气地教训一番。第二次,冒雪前往,碰到卧龙的另二位好友石广元、孟公威在乡村酒店喝酒,只顾猜拳行令,仰天长啸,对刘皇叔爱理不睬;又碰上卧龙的老丈人黄承彦,话不投机,拂袖而去。
那就更不得了了。不仅诸葛亮的粉丝徐庶厉害,诸葛亮的狐朋狗友也一个个有模有样,高谈阔论,目空一切,可见卧龙不是条真龙,而是神龙。
刘备当时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那就只好三顾茅庐了。第三次,碰上诸葛亮正睡午觉,刘备束手敛容、毕恭毕敬在厅堂等候。诸葛亮好不容易醒来,还要吟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坦然又超然,肃然又傲然,大隐士、大名士的派头跃然纸上。诸葛亮起床后,精心地梳洗打扮半天,才慢腾腾出来会客。
功夫不负有心人。宾主摆上香茗,促膝交谈,就当前国内国际形势进行深入的探讨,就刘备今后的出路达成共识。刘备果然是拨云见日,胜读十年诗书。客气一番之后,诸葛亮安排好家务事,半推半就地受了聘礼,便于次日随刘备出山去了。
《三国演义》的“演义”之功,不能不令人佩服。
《三国志·诸葛亮传》是如此记述的:年轻的诸葛亮隐居在襄阳附近的隆山脚下,躬耕陇亩,自食其力。当时刘备驻扎在新野,诸葛亮的好友徐庶向刘备推荐,刘备叫徐庶唤诸葛亮一同来见。徐庶说,诸葛亮这个人是不能呼之即来的,应该将军您屈尊前往拜会。
于是刘备就前去拜访诸葛亮,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见面后刘备虚心请教,诸葛亮则根据天下大势和刘备目前的状况,为刘备的出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番,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
《三国志·诸葛亮传》只说刘备去了三次,才见着诸葛亮,诸葛亮陈述完后来被称为《隆中对》的战略规划后,刘备说,太好了!紧接着一句“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三国志·诸葛亮传》并没有说诸葛亮出山的具体时间,只是说,刘备去了三次,才见着诸葛亮,见面后“香”味相投,诸葛亮献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毕业论文,打起背包随刘备干革命去了。
《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的出山,可谓神来之笔,诸葛亮的推销自我,足以让当代任何一位营销大师叹为观止。刘备的求贤若渴,足以让后世任何一位统治者羞愧汗颜。
事情真的是这样富有浪漫色彩甚至这么富有离奇(不仅仅是传奇)色彩吗?
关于诸葛亮的出山,《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如下:“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对“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句话,通行的理解是:“于是,先主就去拜访诸葛亮,一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
古人叙事说理,常用比喻、隐喻,行文简洁,单音词多,又不时使用通假字,古文的语境与现代汉语明显不同。现代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比较接近,而古代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相距甚远。所以,今人读古书,往往容易产生或大或小的歧义;一句古文,译成现代汉语,有时可有几种译法,语义之间可能有微细甚至明显的差别。
其实,“由是先主遂诣(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句话,除了上述通行的理解外,还有两种理解。
第一,句中的“三往”不是特指三次,而是泛指多次。如此,则可理解为:“于是,先主就去拜访诸葛亮,去了多次才见到。”
第二,句中的“见”字读xiàn,通“现”。古代汉语中,“见”是“现”的本字,如神龙见(xiàn)首不见(xiàn)尾;或者说,“现”是“见”的通假字。如此,“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可表述为:“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诸葛亮)乃现。”
这样的话,这句话则可以理解为:“于是,先主就去拜访诸葛亮,去了多次,诸葛亮才与先主见面。”古汉语中,“见”做现代汉语的“见”字时,是及物动词;做现代汉语的“现”字时,是不及物动词。如果“乃见”是说刘备看到诸葛亮,是不能省略“亮”这个宾语的。如果说“乃见”通“乃现”,指诸葛亮现身与刘备相见,则可以省略“亮”这个主语。由此可见,我的这种理解正确的。
上述第三种解释,倒是可以将《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述与《三国演义》的情节,做一个合乎情理的贯通。大致的情形是,刘备得到徐庶的推荐后,对诸葛亮不是很重视。在徐庶的劝说下,才亲自去拜访诸葛亮。但诸葛亮拿不准刘备是怎样的一个人,开始时并不亲自与刘备会面,先让自己的师友与刘备打交道,以便对刘备作些试探性的了解,最后才亲自与刘备见面交谈。
所以,对于诸葛亮的出山,我们不能根据史书或文学作品的记述、描述,作生搬硬套的理解。因为,诸葛亮本人,对于自己的身家性命,断不会如此草率。
刘备自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至诸葛亮出山,在荆州住了六七年。这六七年应该是刘备一生中最幸福同时也是最郁闷的时光,休闲得很,以致引出一个成语:髀肉复生。同时,诸葛亮的品牌在荆州士人的炒作下,已是如日中天。“诗才将略,一时才气超然”,据说曹操和孙权都想将其罗致麾下。
闲来无事的刘备就是平时上街买菜、遛鸟、下馆子,肯定也能听到诸葛亮的大名,不可能连卧龙是谁都不知道。思贤若渴的刘备绝不可能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少年老成的诸葛亮也绝不可能不与刘备深入接触,与刘备面谈一次就投怀送抱,以身相许。
诸葛亮的出山,不是今天的白领到民营企业打工,随时可以被老板炒,也可以随时炒老板。那是“卖身投靠”,弄不好要丢掉身家性命的。诸葛亮出山前能做出《隆中对》这样的战略规划,说明他的世界观已相当成熟,不可能像今天的热血青年,上头一糊涂,下头一发热,便带着女朋友到宾馆开房。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刘备驻扎新野期间,经过多次与诸葛亮的接触、交流,探讨今后的出路,共同制定了载于《隆中对》中的战略决策。至于两人是怎么认识的,则有很多可能:人才招聘会、朋友聚会、偶然相遇、诸葛亮毛遂自荐、刘备虚心请教,等等。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共同作出战略决策,说明他们有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诸葛亮才决定出山辅佐刘备。至于有没有谈什么待遇问题,不得而知,大概聘礼还是收了的,这是当时的惯例。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好的是,你很在意。”这首歌,是诸葛亮献给刘老大的呢,还是刘老大唱给小诸葛听的?
抱歉,我也搞不清楚。
诸葛亮决定追随刘备,基于他们达成了共同的愿景和理想,但光有共同的愿景和理想不够,刘备还必须有别的什么东西,能满足诸葛亮理想之外的其他一些欲望。正如一对男女,要组成幸福的家庭,光有性爱是不够的,那只是生育合作社;光男人养家,女人持家,也是不够的,那只是经济共同体。一个幸福的家,除了生计、性爱以外,还需要别的一些东西,诸如情趣、情爱、爱好,等等。
出山之前,诸葛亮在荆州生活、学习了十余年。当时的诸葛亮像个如今哈佛、牛津留学回国的待业青年,囊中羞涩,自己开公司不可能,但找工作还是很容易的,不少五百强企业都等待海归高材生的加盟,而且薪酬优厚,前途看好。
经过多年的观察,诸葛亮对刘表的懦弱无能,对蔡、蒯两个当地豪族的离心离德有了清楚的认识,刘表集团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凤凰当然不会栖于将覆之巢。所以,诸葛亮不仅不参加刘表的幕府,还要胳膊往外拐,吃里扒外(诸葛亮的丈母娘是刘表后妻的亲姐妹,诸葛亮还得跟着黄婉贞叫刘表一声姨父),唆使刘备造刘表的反,端刘表的老巢。
诸葛亮不投靠近在咫尺的刘表,情有可原。曹操已统一了北方,孙权已稳据江东,诸葛亮为什么不投奔曹操、孙权,而选择寄人篱下、四处流浪的可怜虫刘备呢?这个类似于海归精英的高级知识分子不睬两家大公司的招揽,而投奔一个一名不文的个体户。除了所谓的理想以外,肯定还有别的追求。
什么追求?要么是高薪,要么是高位。换句话说,要么是利,要么是名。至于什么崇高理想,除了诸葛亮本人,谁也说不清楚。
高薪刘备是付不起的,至少没有曹操、孙权出的价码高。
那只能是追求高位了。
这就涉及诸葛亮的价值观和权力观。
打个比方来说,当时的曹操集团是国营垄断企业,尽管总经理(曹操)大权独揽,有篡党夺权的嫌疑。孙权集团是初具规模、欣欣向荣的民营公司。刘表集团是个得过且过的公私合营企业。而刘备(此时还称不上集团)不过是街头卖茶叶蛋的个体户。
诸葛亮的主观定位和客观定位,只能是总经理(谋臣、谋士),而不是董事长(人主)。此时的曹操身边,可谓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这些猛将谋臣,要么身世显赫,要么身怀绝技。诸葛亮到曹操身边工作,可能要从办公室秘书干起,先干十年八年倒茶扫地的活计。东吴方面,要津肥缺统统被孙策旧部和本土豪强占据,最多弄个处长、科长的干干。何况,孙权开的是民营公司,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尚未登记,政治上也毫无背景,入不了诸葛亮的法眼。
刘备这边,武能称得上战将的,只有关羽、张飞、赵云,基本上是几个大老粗;文能称得上谋士的,只有一个徐庶,不过是个中智之士,还是诸葛亮的好友兼粉丝。更重要的是,刘备虽然是个穷个体户,但拥有皇室远支的身份,相当于持有开国营垄断公司的许可证。只要勤奋努力,只要抓住机会,另开一家国营公司完全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