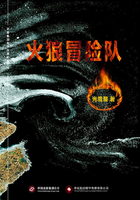星期天清早,司仪还在罗舜的怀里熟睡,就被电话铃声吵醒,罗舜说,吵死鬼!昨夜忘了摘下它。
司仪拿起话筒,一听是何良才的声音,就递给了罗舜。
何良才说:你们两口子倒舒服!你就不管管我啦?
你要什么有什么,哪还轮得上我来管?罗舜说,你大清早的吵什么吵?你不要我休息了?你玩得快活时我怎么不去吵你?罗舜昨夜与司仪“娱乐”得尽兴,觉没睡足,一肚子不高兴,便句句没好话。
哎哟!还说我快活呢!我不如死掉算了,这后院起火把我烧得焦头烂额,快成木乃伊了。何良才在电话那头叫苦连天。
你他妈是自找的!被钱“烧”的!罗舜恶狠狠地。
罗舜,你也该文明一点。司仪在边上插话。
何良才在电话那头听到司仪的声音,就说:是呀是呀!还是司仪温柔。现在温柔的女人太少了!他大声感叹。
罗舜不耐烦了,催问:你到底要干啥?我不能老这样光着身子陪你聊天。
你夫妻俩个上午能不能来一趟?何良才认真地问。
干啥?
离婚!
谁离婚?罗舜如坠烟云中。
当然不是你两口子!
那——罗舜正要问司仪,那边何良才又催问一遍。
罗舜说:好吧!你还真时髦呢!让我羡慕啊!
罗舜电话还没挂好,腿上就被司仪拧了一把,司仪恨恨地说:我叫你羡慕!羡慕不羡慕?
哎哟哎哟!老婆,你真狠心!长包了长包了,快放下!罗舜痛得大声讨饶。
谈判地点就选在红叶商场楼上的娱乐室。司仪夫妇到这里时,何良才已坐在木沙发上吞云吐雾。司仪问:
洪叶呢?
何良才答曰:还在卧室呢!她现在总是昼夜颠倒。
司仪便对卧室喊“洪叶!洪叶!你还在做梦啊!”
洪叶头发零乱穿着睡衣趿着拖鞋伸出头来,淡淡地说:你来了?有事吗?
嘿!你怎么问起我来了?你们两个没统一意见?
何良才说:司仪你先坐一会儿,喝点水。我去叫她。
何良才走进卧室,不知说了些什么。司仪便听见洪叶歇斯底里的哭骂声:你走开你走开!你找你的野老婆去!
何良才冷笑一声:你没脸骂我!你比我更龌龊!我俩半斤兑八两,谁也不欠谁。
我不同意!你休想!洪叶恨恨地说。
有这个必要吗?还是好聚好散吧。何良才一派大将风度。
洪叶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一伸手,手机便砸向何良才。
何良才头一偏,手机落在门上,哐的一声掉下地。何良才仍笑着:你最好是快点,罗舜、司仪都来了。
你死远!——洪叶大哭起来。
何良才悻悻地退出,司仪走了进去,关上门,坐在床沿,望着洪叶,悲悯地说:洪叶,我做梦也没想到你成了这个样子。从读高中时起,你一直是那么乐观、活跃、有主见。后来,你又是那么能干、勤劳、大胆。我一直很佩服你,也羡慕你的爱情你的婚姻。我一直以为你很成功,无论在事业还是爱情上。可是,而今看来,我仍是想不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嘛?
洪叶止住哭声,哀怨地看了司仪一眼:反正你也不是外人。闹到这个地步,我也不怕什么。这个狗日的!我那么累死累活挣钱,而他倒好,背着我乱搞。我一忍再忍,看在我俩十几年二十年的情份上,以为他能珍惜,以为他能回心转意。可是,他太不要脸了!即使这样,我仍不想分开。我都这么大了,离了还有谁要?孩子还小,不也可怜吗?——我怎么这么命苦啊!洪叶又哭起来。
司仪的心里很不好受。两个人都是从中学时代就交往的朋友,一块玩耍惯了,忽然要成为他们离异的证人,这本身就是十分不对劲的事。她一时不知如何劝说,只尴尬地坐着。
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帮帮我,司仪!洪叶哀求似的看着司仪,等待回答。
我尽力而为吧。司仪乏力地回答,便出门去了娱乐室。
何良才看着司仪。罗舜问:她来吗?
司仪说:她只是哭,她能不能受得了?这对她太残酷了。何良才,你是不是重新考虑一下?
何良才执意地说:不行!说完头偏向窗外:你不问问她背着我干了什么。这种变态的女人,我能忍受吗?
何良才自然指的是洪叶同何谭的事。罗舜司仪曾隐约听说过,一直不相信,但这样的事,谁也不好直问。今听何良才如此说,以为是真的了。心知这桩婚姻是彻底完蛋了,谁也无回天之力。
都沉默起来。
罗舜说:何良才,你们无法达成一致。我看今天就算了吧?他想:能拖一天算一天,劝合不劝分嘛。
何良才,你真是狼心狗肺!洪叶咬牙切齿。
那你又是什么?何良才冷笑道:你有资格骂我吗?
洪叶一时语噎,心中一个声音哀叹: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男女之间的事越解释越糟,她无法也没有勇气对任何人作出解释,她与何谭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与一个比自己小十五岁的男孩子苟且偷欢_这是这个社会任何人都无法容忍的啊!洪叶绝望了!差点要从楼上跳下去。
洪叶怔怔地坐着发呆。
罗舜过来拉走了何良才。何良才一边走一边喋喋不休说:她是个什么东西!还说我狼心狗肺。整天钻到钱眼里去了出不来,男人的事不管孩子的事不管,她还算个女人吗?我出去喝酒有什么关系?我打牌犯法啦?就是跟女人一块玩玩又算什么?哪个男人不是这样?她还有脸说人吗?她干了什么,她敢说出来吗?
罗舜默默地听着,只觉得心口难受,他无法说出什么。即使对方不是自己的同学,他在心里告诫自己决不再多开口了。——男人,到了这种地步,你是无法让他明白什么妥协什么的。
一阵风吹过,室外的各种扭结在一起的电线,还有窗外的太阳篷呼拉拉乱响,发出一种让人感到阴森作冷的声音。
罗舜打个寒颤。何良才一句“哪个男人不是这样”让他愤慨又让他悲哀,说不清什么原因。他只觉得早点了断这桩纠缠,让每一个人包括自己尽快清静。长痛不如短痛,烂了不得治好的腿还是趁早砍掉为妙。
司仪的心也越发沉重,她根本没想到洪叶与何良才的关系已到了这个地步,来的时候还以为属于两口子之间的“民事纠纷”呢,哪知是势不两立的局势。与其绑在一艘船上共同沉没,还不如放下救生艇各自逃命,也许还会有生的希望。
这样想着的时候,罗舜把她拉到走廊的另一头,悄悄说:我看算了吧,何良才已是铁了心。差劲!你去劝劝洪叶,女人未必离不开男人!
司仪听了后一句话,却抓住罗舜的胳膊不放,附在耳边轻轻说:我就离不开你呀!
罗舜心中一动,紧紧握了一下妻子的手,仿佛传送着一种坚定的答案。又抽出手来拍拍司仪的背,示意她去劝洪叶。
司仪走进卧室,见洪叶呆坐着,脸色木然,平时那个活泼生动的洪叶不知哪去了。她轻唤一声:洪叶!洪叶没应,仿佛远古神话中怨妇的石像,看不出还存活着一个生命的细胞。那神情让司仪心中涌出沉沉的担忧:洪叶是否有勇气活下去。
曾经将感情的全部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以为象中学课本所言那么纯洁那么永恒那么长相厮守,这美好的愿望在生命的溪流中也许还能平稳地漂流,可一旦遇上峡谷险滩、暴风骤雨,地势变了,天气变了,甚或碰上了人为的拦水坝,它就束手无策,就昏头转向直至四分五裂。
那么,每一个漂流者能否躲过毁灭的灾难,驶向生命的终极地——大海?司仪的思维又一下子跳到了前几年的那一群漂流长江的勇者!她想:光有愿望和勇气,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具备生存的智慧和自救的能力。
那一幅《人生三部曲》的油画又不合时宜地浮现在司仪眼前。生命是如此的短暂,是如此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飞速地经过出生——成熟——死亡三部曲,芸芸众生看到的大多是每一天每一个时辰每一刻的衣食住行甚或名利悲欢,纠缠于世俗琐屑中无法自拔。只有智者,他们才是站在生命的云巅,静静地注视这一切。而洪叶是不可能站上云巅的,她是红尘中最微小的一粒。即使龚晓、司仪自己,也不是。那么表哥呢,他也只不过在经历生死一瞬间之后而略有领悟,司仪又想起了广州之行表哥的一番“地球”的比喻,不禁笑笑,站起来,对洪叶说:
洪叶,事已至此,还是冷静面对现实,世上比何良才好的男人多的是。何必为他而哭为他而伤为他而死呢?天涯何处无芳草!这话也适用今天的女人呢!你才三十七岁,在今天这个时代,正是火热的时候。重新开始,也许更辉煌!
洪叶凄然一笑:司仪,谢谢你!象你这样的朋友世间太少了。总是在麻烦的时候我才找你,而你每一次都能给我勇气和力量,分担我的烦恼和悲伤。又象是想起了什么,摇摇头苦笑笑:算了!我拖着他有什么意思?如果他的心已不在了,我还留恋什么?当初如果我知道今天会是这样,我就不会那么拼命挣钱了。现在这个样子,钱——又有什么用?
洪叶又淌下泪来。
司仪说:不要想那么多了吧?分开了你还是你,你损失了什么?钱还在,孩子还在,红叶商场不也在吗?为什么你平时那么果敢的人,会让一个何良才给弄得锥心刺骨痛彻心肺呢?
洪叶摇头不语。
司仪冒火了,大声质问:你说,何良才到底有哪一点好?论漂亮,他比得上罗舜吗?论学问,他比得上龚佳奇吗?论魄力,他比得上冯大力吗?论风度,他比得上——
司仪一时卡住了,只顾加强语气一个劲反问,没想到在熟悉的人里一时找不出合适的来,就顿了一下,脑海中掠过黄峰的影子,便脱口而出:比得上黄峰吗?
洪叶仍没反应,她自己却先笑了,跑去倒了杯水,喝了一大口,又问洪叶:你喝不喝?见洪叶摇头,便又说:不管怎样,我一直是你的朋友!过去是,将来还是!
在回家的路上,罗舜说:司仪,你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吗?男人的三大乐事?
哪三大?司仪在摩托车后座上双手紧搂着罗舜的腰,把头靠近罗舜的肩膀问。
罗舜大声说:升官、发财、死老婆!
司仪怀疑自己的耳朵,大声问:你放什么?
升官、发财、死老婆!——这是别人放的,不是我!
罗舜加大油门,摩托车后“突突”放出一股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