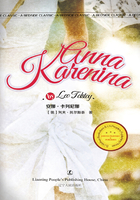这期间,司玲也去小学做了一个学期的代课教师,原老师请产假,一时缺人,司玲毛遂自荐请求代课,校领导考虑到她也是堂而皇之的高中毕业生,同意了。教小学语文,需用普通话教学,况原任老师是正规师范毕业的,普通话非常标准,而司玲许多年未曾讲过普通话,按书上的读音很艰难地教,一说起来却又不行,方言夹着普通话,常使学生阵阵哄笑。好在乡下的学生很淳朴,父母也不象城里的父母,对老师要求那么苛刻。一个学期也便在吃力中捱过去了。
司玲又在闲聊与麻将声中度过了一个暑假。龚晨到姑姑家度假去了,小表妹冯媛9岁,上小学2年级,两人年龄悬殊5岁,却玩得十分融洽,也借此躲过妈妈的唠叨,奶奶也在姑姑家。姑姑忙,整天不落家,姐妹俩便玩疯了。龚佳奇每天除了烧饭打扫外,便是坐到桌前写论文。象他这样的年龄,既无三十多岁时的浮躁与生气,也无五十多岁人的达观与淡漠,仍将责任、名利看得较重。尤其妻子下岗后,经济负担加重,女儿还小,今后上大学要花很多钱。光靠自己也够呛的。
一开学,龚佳奇便找校长要求带两个毕业班,另做班主任,而且还偷偷在外面当了家庭教师,整天累得够呛,晚上从班上查夜回来,总是疲倦得连澡也懒得洗。
当深秋的阳光早早照射到向东的窗前时,一夜没睡好头重脚轻的司玲收拾几件换洗衣服,拎着包径自出门,没跟龚佳奇父女俩打声招呼,才七点多就到了城里开发区红霞路上的公安宿舍妹妹司仪的家门前。按门铃,妹夫罗舜来开门。门一开,大惊:哟!这么早,玲姐!
穿过100多个平方的绿草坪,步上浅灰色大理石台阶,司玲机械化地换了拖鞋,走进不锈钢防盗门,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客厅令匆忙出走的司玲自惭形秽。以往每次来司仪家她总要发几句牢骚,抨击一下社会的丑恶腐败,甚至浅讽几句妹妹命好,嫁了个有用的男子汉,随随便便不费力就进了公安部门,没有几年又赶上分房子,生的是儿子——这点也比自己胜一筹,总之,什么好事都给妹妹碰上了。每次牢骚,司仪只是听着光笑,不辨解。“姐姐只是在嘴上不让人,其实心里也还不坏”——司仪事后总这样向罗舜解释,“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司玲将行李一撂,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脸色阴阴的象秋天的傍晚。罗瞬其实是司玲一届的毕业生,年龄小不了一岁,出于礼貌,常常称“玲姐”,碰上司玲心情好时,会调侃几句:“罗舜你这小子!当初怎么就不上我们学校?说不定就不是现在这个格局呀!”罗舜嘴滑,也爱顺杆子爬:“就是嘛,可惜走过的路不能重新来,来生我坐你同位。”司玲就大叫:“司仪,你听见没有?罗舜这小子在嫌你呢!你可要当心,男人有钱就变坏,尤其城里人!”
等罗舜调好一杯奶粉端到司玲面前时,司仪也从卫生间洗漱完毕出来了,欢快地叫了声“姐,你来得正好,罗舜要出差,你正好多住几天,帮帮我看一下司念——这家伙太调皮了,我的话快不管用。这么点鬼东西总爱赖在电脑前不下来。”正说着,司念蹦着下来,喊一声“大姨!你一个人来?姐姐呢?”
“姐姐哪不像你一样?要上课。”
“姐姐也真是,一天到晚只晓得钻在书里。她会玩电脑吗,大姨?”说着,就偎在司玲的腿上来了。一股由衷的喜爱漫出心头,司玲抱住司念,亲他的脸:“姐姐哪有你聪明!才八岁就会玩电脑!”
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一块面包,一根火腿肠,司念背上书包喊:“大姨,我上学了。你不要走,我马上就放学。”
罗舜追出去喊:念念,小心点!走路边上。
“知道!”司念大声应着,又小声嘀咕:“真罗嗦!还是男人呢!”
这话叫司玲听见了,噗哧——一下笑出声来,差点将面包吐了一地:“嗯,我们司家恐怕以后还是这小东西有点出息。”
“我们司家”这话让罗舜听了极不舒服。当初儿子生下不久报户口时,罗舜要儿子跟自己姓,取名“罗一雄”,司仪不同意,说“你兄弟那么多,三四个侄子。我家就姐妹两个,我爸很想有个孙子跟他姓司。儿子就姓司好不好?”罗舜极爱妻子,但儿子不跟自己姓,心中总有些不舒服,便说把两人的姓合在一起,叫“罗司”吧。
“罗司——罗司——?”司仪读几遍,噗哧笑了,“搞不清的人还以为是能吃的‘螺丝’呢!不好不好。唉呀!姓名不就是个符号嘛,我们哪还看重这个,只不过安慰安慰老人罢了。
罗舜便勉强同意,任司仪取名,司仪给儿子取名“司念”说这名儿谐音好记,也不俗气。罗舜开玩笑说“思念谁?你做了我老婆,还思念谁?”司仪便红了脸,捶了丈夫几拳,偎在怀里说:“就思念你嘛。”罗舜也不追问。
晚上司念睡下后,姐妹俩边看电视边聊。司玲满肚子苦水一个劲倒:你不晓得,我现在真是没法过了。我每月就那点生活费,还不够你的零花钱。你姐夫迂夫子一个,整天只知道上课备课改作业,头脑古板,又惜面子,从来不为我的事去找找人。小晨也不小了,自己的事自己能管得了,我想,我只能出去打工,看看行不行。
司仪说,姐,外面的钱也不好挣,你也不小了,又不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人家吃的是青春饭。你没听那话么?女人变坏才有钱。象你到外面去,能做什么呢?况且姐夫一天忙到晚,年纪也不小了,你在家总能照顾一点吧。
不碍事的。我走了,可以把他妈接来帮一下。
姐,你别忘了,你已35岁了。
三十五又怎么了?我就不服气。
司仪心中有些不高兴,那你说你能干什么?
这话问得司玲泄气。她确实不知自己能干什么。这么多年她的工作只是收一下费,有时打打杂,其次是擅长聊天,在家里的专业也只是洗衣,连饭也烧得不如龚佳奇的手艺。她根本就不曾想到有一天自己也面临下岗,也面临生存竞争,也面临考虑经济问题。17年前欢欢喜喜接母亲的班,那时还有多少同学羡慕,“商品粮”的靠山早就成一纸空文,这世界令她愈来愈感到不安全了。司玲陷入从未有过的沮丧与恐惧:司仪,你说,像我这样的人,现在就一点用也没有了?
司玲满脸的悲戚也令司仪不忍,赶忙安慰:姐,怎么能说一点用没有呢?只是要正确认识自己。现在连大学毕业生都下岗,有个大学毕业生下岗了去当修脚工,还是男的呢!一般人谁瞧得起那个职业,可他一月能挣五六千元。
司玲不吱声,眼睛盯着电视屏幕,却茫茫然不知放的是啥,心中依旧乱如麻团。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司仪接过:“喂,谁?”
“小姨,我是小晨,妈妈在你家吗?”
“哦,小晨呀,妈妈在这里。怎么?她没跟你讲呀?”
“在就好。小姨,让她多在你家住几天。我和爸吃食堂,很好。”
“让你妈接电话吧?”
“算了,我要上自习了。”电话挂了,司仪无奈,望着司玲,同情地说:“你女儿很关心你呢。小晨已很懂事了。”
“还懂事呢!骂我到了更年期。”司玲一脸委屈。
司仪大笑:“更年期?嗯——说不定。”一脸坏笑。
司玲便回敬:你也好不了多少。
客厅里便多了一些轻松气氛。电视屏幕上正放《水浒传》的片尾主题歌“路见不平一声吼呀该出手时就出手。”司玲司仪就都跟着哼起来。
司玲在妹妹家住了一个星期,心中也有些挂念女儿。正欲等司仪下班回来告诉她自己准备回去。
“姐,告诉你一个消息,你的小姑子龚晓这次当上镇长了,选上的。全县就她一个女镇长,说不定今后还有点出息呢,她比你小一岁,今年34吧?”司仪一放下包就说。
“哦,真是命!”司玲脸上没什么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