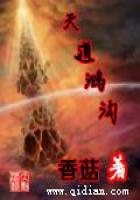芳芳心事重重。吃饭时,没像往常那样加入父母的交谈。她只在一旁默默听着,心思被另一件事情勾住了。小碗的白米饭只扒了一口,又站起身来,闪身进了小屋。不足六平米的屋里弥漫着五月份才有的霉味,不用的家什杂物沿三面墙根一溜摆放,轻巧一些的又往上摞起来。已经几个星期不见闲人进来折腾了,杂物表面已经积满了一层细腻的白灰,像心细的主妇蒙上的一层白荧荧的棉花纸。她差点被木桌前的一个矮板凳绊倒,身体朝窗户的方向趔趄了一下又站住了,眼睛顺着那个方向端详起来墙角的一摞纸箱。悬浮在空中的尘埃在鼻腔里痒痒作怪,最后的喷嚏使她倒吸进更多的灰尘。她奋不顾身地打开一个纸箱,终于找到一本旧版的新华字典,保护用的塑料封套早已不见,甚至前面的几页说明也残缺不全,但她仍然很兴奋。
她捧着脏兮兮的字典回到客厅,好看的鼻尖像撒了一小撮胡椒粉。她母亲关切地侧过身子催促道:“再不吃,饭菜要凉了。”“嗯,”她随声应和却不抬头,眼睛继续盯着在大腿上摊开的字典。还有两个月她就小学毕业了,早已用不着那几页丢失的偏旁部首。她在“刺”的第五个字义里,找到如下字眼:
尖锐像针的东西:鱼刺,刺猬,刺槐
这是整本字典中唯一出现“刺猬”一词的地方,她失望地合上字典,书页合拢时扑出的一股霉味,熏得她赶忙捏住鼻子。她重新拾起碗筷,无法像往常那样细心品出饭菜的香味来。面对母亲忧心忡忡地征询,她只得违心地敷衍道:“蛮好,今天饭菜蛮合口胃的。”在一小碗白米饭吃完之前,又站起来三次,几乎把脸贴到了电视机的屏幕上,凑近看里面的“动物世界”节目。画面上又出现了一些小动物,这是她站起来看的原因,眼睛由于近视已经眯成一条缝。地鼠后面又介绍猫头鹰的食物链,出现在山林间的穿山甲、松鼠和刺猬只是作为陪衬猫头鹰的画面在她眼前一闪而过。她想在屏幕上进一步抓住点什么的心理,使她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坐立不安。这一顿晚饭吃下来,只觉得胃里凉飕飕的,走出房门时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门外楼道的墙角里,拱着一团像垒墙用的褐泥状的东西,被开门的铁栅栏的声音震动后,迟缓地动弹了一下。它的头被四只利爪团抱着,使足劲儿钻进软腹,形成一个类似土窑的平底──那是芳芳把网兜拎起来所看到的景象。数不清的长刺倒下去,竟像羽毛一样温顺服帖。这副憨态可掬的模样,惹得芳芳想伸手顺着长刺捋几下。
网兜拎起来后,撒在四周诱它伸头的饼干屑在地上形成一个椭圆,没有丝毫动过的迹象,她有些着急起来。除了粗糙的喘气声(像冲过终点的运动员发出的),完全没有动物应有的动静。她断定它的生命力正在衰竭,掐指一算,心里越发不踏实了。从山里来到城市的这几天,它肯定滴水未进。
晚饭后,父母循着老习惯出门沿街散步,撂下她一人在家忙个不歇。这时方才意识到它不像家禽,能随便用饼干之类的熟食打发的。她开始把目光转向冰箱里的生食。她进里屋取出一把大剪刀来,在厨房的砧板上将一棵冰冷的青菜剪成了一绺绺的“面条”,随手拈了一撮来到楼道里。每一绺足有三寸长,她感觉这是喂食的安全距离。叶子穿过网孔后落在头可能钻出来的地方,不多一会,它满身披挂着绿菜叶了,甚至青菜的清纯气味暂时缓解了它浑身散发出来的尿臊味。但任凭用菜叶怎样刺激它,在那些长刺上磨蹭,它依旧巍然不动。芳芳蹲在它的上方,简直拿它毫无办法。她用舌头和嘴唇吹出各种声音,吹腻了又站起身来,在边上用脚跺地,末了甚至企图重演晚饭后她开门的那一幕,把铁门一遍遍拉开,再“哐”“哐”地用力关上。
隔壁的老太早已对门外的怪声心存疑窦,这会儿又听见对面的门震得哐哐响,只得战战兢兢从门上的猫眼向外看。芳芳的一举一动全在她眼里。当老太气恼地打开木门,一掌将保险门推开,芳芳立刻红了脸转过身来,她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打扰了对方。老太虽低着头,眼睛却乜斜了往上瞅她,这是戴老花眼镜的人常有的视物方式。“你在干嘛?”老太有些纳闷,刚才猫眼里芳芳好象正对着一堆垃圾吆喝什么。老太没容芳芳答话已走到跟前,又伏身下去看个究竟。“噢……原来是刺猬!”老太连忙后退几步,一股臊味熏得受不了,她更怕倒伏的长刺会竖起来。
芳芳接着她的话茬儿说:“它什么也不吃。”老太这才明白了她的良苦用心。
“这东西不能养啊,臊得很,得赶紧吃掉,只有楼下的陈叔会杀这东西。”老太担心她会在楼道里把刺猬养下去。这话芳芳听来有些刺耳,她听出了里面的另一层意思,她的倔脾气陡然升上来,但说话的方式倒像自言自语,“今天我非让它吃点东西不可!”她索性把网兜拎起来离地十多公分,尔后猛然撒手──刺猬落下去,还是巍然不动!在刺猬面前她完全像个年轻的不知所措的家长,说话间动作裹夹着不被理解的怨气,甚至有一刹那,泪珠儿在眼皮底下打转,差点夺眶而出。老太站在一旁察觉气氛有些不对,为了不使自己尴尬,赶忙顺着芳芳的话,献计献策起来。
在她漫长的记忆中事实和想象早已混杂在一起。“它好象吃一些活的东西,象老鼠哪,还有蛤蟆、蚯蚓之类的。”站在楼道三四十秒后,老太已经适应了动物的气味,说话间两条腿还朝芳芳这边挪过来。老鼠、蛤蟆或蚯蚓不是芳芳能够或者敢于找到的,她能够选择的只是家里现存的一些东西,除了饼干、糖果之类其余都超不出冰箱的范围。但老太的话还是一语中的,使芳芳一下意识到自己先前思路的错误,她早该把目光转向冰箱里的荤食。
进门时她甚至忘了跟老太打一声招呼,在明亮的节能灯的照射下,她的脸因为激动显得红扑扑的。她急切地从冷冻柜里取出一块硬梆梆的生猪肉来,把砧板上的青菜捋向一边。速冻的猪肉在砧板上冒起许多柱白色的雾气,当她艰难地切下肉块的一角,连刀刃也冒白雾了。她把猪肉切成一根根的,长度比先前的菜叶短了一大截,她早就没了先前的顾虑。她一把将砧板上的肉丝捋进右掌心里,同时感到了一阵彻骨的冰凉。
芳芳返回楼道时,老太已经悻悻地进屋去了,但刺猬明显挪动了位置。芳芳赶忙蹲下去,仔细辨认它是否真的吃了青菜。扔在它背上的菜叶确实不见了,但都被它捋到身下当了垫的。尼龙网兜团团裹着它的身体,也许冷给了它额外的刺激,它已向墙角挪近了半尺。下面的景象更出乎芳芳的预料。当着她的面刺猬真的动了一下,接着脑袋就钻出来了,鼻子还不停嘶嘶嗅着什么。芳芳手里的热气渐渐把硬梆梆的肉丝弄得软塌塌的。第一根肉丝扔下去,没能顺利地穿过网孔,被网丝勾住了,悬在刺猬头顶上方。芳芳伸出一根手指,想拨弄一下,却听见刺猬发出簌簌强烈的吓唬声,接着头和前爪向上一跃,顷刻间肉丝不见了。芳芳吓得猛地站起身来,这东西的厉害出人意料!然而食物到口,它马上平静下来。芳芳心有余悸地站在那里,直着腰,胡乱扔下去一些肉丝。
刺猬不停把掉在网兜外面的肉丝拖进去,甚至不惜在网兜里滑稽地打滚。吃到一些肉丝后,它对芳芳的态度明显好转,后来芳芳甚至能用指头捻着肉丝,隔着网兜喂它了。每回它的嘴只衔肉丝的前端,绝不碰她手指。芳芳兴奋得心嗵嗵直跳,但仍然面色紧张地注视着自己葱白一样的手指。不多一会,手里的肉丝全喂完了,她满心欢喜地冲进屋里,又切了一小把肉丝出来。如此往返了三次,刺猬才对猪肉失去兴趣。它好像很快从虚弱中恢复了过来,对被困网中表现出不满,试图用绕自己打转的简单办法摆脱网兜。芳芳用了好几块砖头才把它围在墙壁和两个废弃的花盆之间。
父母散步回来时,芳芳已经进屋去了。她把自己锁在南屋,拿着一支铅笔在白纸上胡乱画着什么,脑海翻腾着下一步的打算。父母经过楼道时,看见刺猬被几块砖头堵住去路,不禁对女儿下午不肯杀刺猬一事又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明白,刺猬只要在楼道里呆上几天,楼上楼下的议论便会雪片般地飞来,那时他们这一家便成为众矢之的。但女儿的心思他们也明了几分,她的确太爱这只刺猬了,舍不得把它吃掉。夫妻俩走到厨房里打开热水器,放了一脸盆热水,一扭头看见了砧板上的猪肉,证实她做的事正是他们所担心的。于是两人挤在厨房里叽哩咕噜商量一阵,最后决定今晚暂不打草惊蛇,还是让女儿暂时沉浸在养刺猬的喜悦中吧,但明天是最后的期限,母亲决定明天下午提早下班,回来找陈叔杀刺猬!
楼下的陈叔业已退休,平时赋闲在家,一份报纸、一杯茶便能混一天的,没见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但奇怪的是他会杀刺猬的事,整条巷子无人不晓。
由于困倦芳芳已经趴在桌上了,眼皮勉强撑开一道缝,她仍在掂量哥哥马荣给她买刺猬的事。母亲在门外喊了三声,提醒她该早点洗罢去睡了,她只当没有听见。马荣是在她下午放学时,把刺猬交给她的,当时引来了同学们的众多目光。马荣的办公室离学校不远,遇上急事小妹马芳自然成了马荣向家里通风报信捎带东西的小使者。下午马荣同其他家长一样,耐心地等着校门打开。在潮水般涌出校门的第一拨人群中,他一眼就瞥见了马芳,于是压低嗓门连喊几声,才把马芳叫住。芳芳一脸惊喜的样子站到马荣面前。马荣二话不说,把系着网兜的细麻绳往她手指上一套,然后解释道:“这东西是给你买的,吃了能治眼睛,特别是胆能明目,这东西难得买到,一定要吃!嗯?……呃,另外也告诉家里,今晚我不回去了,有事要加班。”马荣站在那儿如数家珍,交代完毕后又急匆匆瞥了一眼手腕上的表说,我得走了。便撇下芳芳一人站在那根电线杆下。好一阵子她才回过神来,毕竟网兜里的东西是头一回见,但还是认出来了,以前读过的自然史中的插图起了作用。她拎着网兜刚走几步,同学一下就围过来了,唧唧喳喳七嘴八舌问她拎的是什么,调皮的男孩还捡截小木条,隔着网兜捅它。末了大家惹得它把长刺竖起来,便有人慧眼识英雄地告诉大家,那是刺猬!接着众人又左喝右叱的,吓得它收起长刺,蜷成球状。大家哄闹起来的兴趣,很快被它身上的尿臊味抑制了,勉强陪着走了三、四十米,又一哄而散。
芳芳拎着网兜走进最后一条巷子时,简直有点无地自容,她唯恐别人会猜到这只小刺猬是买给她吃的,但巷子里的人似乎比她更清楚这只刺猬的用途。蹲在井栏边洗菜的黄奶奶,一眼就瞧见她拎着只刺猬走过来,还未走到井池边就扯着嗓子问她:“丫头,这刺猬是在哪儿买的呀?”芳芳立刻涨红了脸说不知道,是哥哥买的。黄奶奶感叹说,好多年不见卖这东西了,你今天碰上真算福气,吃了亮眼睛哪!
她走过大院门口的裁缝店时,又被在那儿取衣服的刘大妈看见,拉住问了半天。她一边微笑一边腼腆地耐心答话,末了刘大妈甚至还说出了一两种烹制的方法,以及这样吃后对眼睛的作用,她站在门外听得眼睛都要发绿了,刘大妈说这番话大概是知道芳芳眼睛的状况,她看书写字时必须带400度的眼镜。
芳芳走进楼前大院时,母亲正好下楼倒垃圾,见她手上拎一只刺猬,便惊喜地问道:“多少钱买的?”芳芳这时才像个孩子似的,歪了脑袋调皮地一笑,说:“不知道!”母亲拎着个塑料袋愣在那儿了,那些给他们家送东西的人经常把她弄得糊里糊涂的。芳芳见母亲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模样,忍不住咯咯咯笑起来,她把网兜向上一扬说:“是哥买的!”接着三蹦两跳上了楼梯,像是急于要给楼上的父亲看这只刺猬。母亲站在原地又想起了什么,忙高声喊住她:“你还是先下来!让陈叔帮你把刺猬杀了!”谁知芳芳听罢,扭头甩回一个“不----!”,咚咚咚又上楼去了。
由于用力过重,笔尖在纸面上啪地一声折断了,芳芳这才警觉地把目光投向床头的闹钟,时针已经滑向秋夜十一点,芳芳平身第一次体验到作决定的艰难。可以肯定今晚马荣不会回来了,但决定必须在今晚作出。她不会推开房门,去找父母拿主意的,她觉得大人总会举出更多相反的理由,来打消她的念头。她再次强打起精神,伸了个娇美的懒腰来到窗前,发现对面屋顶上的鸽棚竟还亮着灯。远远望去,有几个人正兴致勃勃围着主人聊天,主人不时炫耀地把手伸进鸽棚里,抓只信鸽出来。鸽棚的年岁比她还要大,她是趴在窗沿看着一群群在楼宇之间盘旋飞翔的鸽子长大的。她尤其喜爱鸽子在空气中振翅飞翔的姿态,从她窗前沙沙掠过的声音曾无数次引她心动。但鸽棚的丑陋一直给她强烈的印象,无数锈迹斑斑的铁皮向各个方向翻卷着构成了鸽棚。而现在一只白炽灯泡吊在铁棚的一角,给了她更加恶劣的印象。突然,芳芳眼睛一亮,一个想法像水底的气泡迅速浮露水面,她觉得自己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接下来,决定很轻易地作出了。
上床之前必需的清洗完毕后,她躺在黑暗中久久难以入眠,整个下午被刺猬折腾得疲惫的神经开始加速兴奋起来。尽管她竭力想控制住自己,不提早想第二天的事,但第二天仍像一个巨大的吸盘把她牢牢吸附在上面,迟迟无法坠入梦乡……第二天清晨,她在牛奶瓶当啷啷地碰撞声中醒来,隔一堵墙壁耳朵仍能清楚地辨出送奶的三轮车碾过大院门口青石板的声音。往常的这个时候,她还拱在暖烘烘的被窝里酣睡不醒呢。今天她惊奇地发现,自己是按照昨晚预想的时间醒来的。套上毛衣后,她努力静下来一阵子,隔着房门听了听里屋的动静。父母还在酣睡中,他们已经形成六点半起床的铁律。芳芳拿起木梳,又若有所思地坐在床沿。床头闹钟的时针刚刚滑过五点半,但为了保险起见,她仍然决定省去早饭的时间。对于一个刚刚开始懂得何为身材的女孩子,早饭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事了。洗漱完毕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趴在书桌上一笔一划,就着一张白纸写了两行字。
爸爸妈妈:
早自习后我不回来了,我自己在街上买早点。芳芳10.27.清晨。
她对照铅笔盒盖里的课表,细心把课本装入书包,又检查了不应落下的三角板、圆规以及当天应交的作业等,将书包套在肩上,顺手捻起桌上的纸条,来到窄得像过道似的小客厅里。她感到了从厨房半掩着的窗户吹来的冷飕飕的晨风,她特意用一个装蜂蜜的瓶子压住纸条的一角。关门之前她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轻轻把门带上,尽量不发出声音。
楼道墙角的刺猬还在酣然大睡,因为有力的呼吸,它的背脊富有生机地一起一伏。芳芳取出预先在厨房过道找到的废牙刷,小心翼翼把网兜挑起来,扔进她装过球鞋的包装袋里。这样手就不致碰到在刺猬身上磨蹭了一整夜的脏兮兮的网兜。她用草纸把废牙刷裹起来,塞进上衣口袋里。
现在一切准备停当,她可以拎着袋子出发了。
穿过马路时,她看见了那一群在大楼之间盘旋飞翔的银鸽,它们绕过大街东边的一座圣保罗教堂,在两边高大梧桐露出的狭长天空,划了一段优美的弧线,又不见了。芳芳的视线停留在鸽子消失的地方,她发现离树梢不远的树干上多了一个新鸟巢,她的目光在鸟巢上停留了几秒,然后气喘吁吁地跑向一辆正在发动引擎的十路公共汽车。
那是一种长长的,用风琴状黑皮裹住的弹簧连接起来的“大通道”车,说明芳芳选择的是一条横贯城市的主干道。公共汽车行进时,发出哐啷哐啷空荡荡的声音,车上连十个人都没凑满,大家却怀着过去物质匮乏时代的紧张心情,手忙脚乱地抢占紧靠车窗的单人座位。芳芳坐在倒数第二排,脚下正好是汽车的尾轮,这使得放脚的地方比别处高出一截。芳芳一手拎着袋子,一手帮着把脚放在凸起的地方。汽车驶过坑坑洼洼的路段时,芳芳感觉胯下的椅子仿佛毫无缓冲地直接撞在车轴上,反弹回来的力量不时震得尾椎骨麻酥酥的。为了不致伤着刺猬,她用手把袋子悬在两腿之间,尽量护着不让碰上周围的铁器。
公共汽车拐了一道弯后,便径直向市中心的方向奔去,巨大的树冠挡住了车窗外面的天空。晨风从车顶方向吹来,直直灌进脖子。车顶朝向天空的四方小窗敞开着,它像一个通了电的荧屏,快速掠过电缆、树梢、高楼、红色横幅以及彩色气球和巨型广告牌的一角。
市中心是她的第一个目的地,在人流高峰到来之前顺利地换乘上十五路。她依旧坐在汽车尾部,坐在那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全感。路途中早已感觉不到袋内刺猬的动静,她尽力把已经合拢的塑料袋口撑开一道缝,让空气流进去。抬头看窗外,高楼大厦稀稀拉拉的,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已经变成双排。上车后她没特别留心记站名,因为从前和同学沿着这条线路出游过几次。她隐隐觉得沿着这条线路走下去,一定有自己想去的地方。
车过清远门,她开始留意道路两旁的风景。车子轰一声驶出了城门下面的隧道,随着眼前一亮,葱茏的绿树和茸茸的草坪迎面向她扑来。车出城门后,顺着城墙一个急转弯向北拐去。越走树越茂密,房子渐渐稀落,道路两侧只剩下了杂沓的灌木,和一眼望不到底的杉树林。芳芳生怕遗漏了什么,开始目不转睛,心绪紧张地盯着窗外。她期待着一个标志性建筑的出现。车进了杉树林后,她才弄清了自己心里想去的那个地方,只要看见四方城,她就可以下车了。
汽车目空一切地在这条旅游线路上高速奔驰起来。这座城市的旅游区已经进入旅游淡季,有些路段两侧几乎空无一人。进入林区后,她的耳朵里只剩下汽车吭吭的加速声,以及它在静谧的树冠之间造成的轻微的回应。四方城的高大墙面隐在巨大的树冠后面,正门前方象征性地铺了几个石阶。城墙的垛口从芳芳的眼前一闪而过,她禁不住地站起来,空出一只手牢牢抓住前面的椅背。汽车驶过四方城大约三十米后才停下。一块已看不清文字的站牌,用一截铁管孤零零立在那儿,一块半掩在土里的石碑和它隔着一条杂草丛生的水沟。她只想尽快离开大路,从四方城一侧爬上路边的山坡。她惊奇地发现一场秋雨的痕迹还留在泥土的表面,晨风一吹,泥土和树叶的清香便弥散在林间,她的精神随之一振。
沿着坡顶台地向里延伸约三十米,城墙就断了。再向里,是一块高大榆树盖顶的林间空地。芳芳拎着兜,沿空地边缘走了一圈,心里暗暗琢磨着地形。她需要一块灌木丛生的草地。在空地的东北角,她发现了一条可以通向林子更深处的小径。小路外宽里窄,进到七、八米处,路只剩下一脚多宽了,几乎被灌木挡住了去路。芳芳奋力挣脱脚下的羁绊,从几棵低矮的冬青树中钻出来,只觉得头顶一亮,又一片榆树盖顶的林间空地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眼前。
这里乱草丛生,无路可寻,边上长着更茂密的灌木、杉树,冬青和榆树倒成了其中的点缀。芳芳觉得这是和刺猬告别的理想地点,从这里刺猬可以轻易地爬进后山。现在已经僵疼的左手可以放松活动了。刺猬倒出来后和网兜缠绕在一起,她用牙刷柄兜底一挑,刺猬便脱离了网兜,像一只足球似的滚落到灌木丛中去了。接触到杂草和露水后,它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敏捷。在绿茵地上显得格外扎眼的红网兜、白袋子以及浅黄牙刷,又被芳芳收集到一块,准备带走。为了刺猬的安全,她不想留下有人来过空地的任何迹象。
当她心情惬意地转回身子,立刻觉得天旋地转--一个男人堵住了她的去路。他像一只老练的豹在接近猎物之前,未发出任何声响。嗓子早已被什么东西卡住了,除了陡然急促起来的喘气声,嗵嗵的心跳声,两片颤抖的嘴唇已经发不出任何清晰的字音。腿一软,身子顺着一棵幼树溜向地面。这样她的眼睛无力地仰向被树枝割碎的天空,看见晨风摇曳的树丫上,几只山雀倏地一声腾起,振翅向后山飞去。
199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