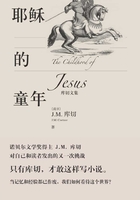季良策在客房里卧炕静养,不知为什么,尽管被打折了鼻梁骨,皮肉之苦也很疼痛难忍,可他躺在施家的土炕上,心里却平静如水。
他甚至想,要是能一辈子都在这里躺着,不回嘉峪关那个家里,未必不是一种幸福。
但躺了半日之后,他觉得缺少了点什么。前思后想,才明白从进施家,还没有见过施念慈。至此,他才明白,他一切的平静与安宁,还有那莫名其妙的幸福感,其实全部来源于那个叫施念慈的女人。没有了她,这施家的土炕一样不可爱,不温馨,不舒坦,不可留恋。
可是,如何才能见到那个可人儿呢?又如何才能躲在这里,多待些日子?想到自己的父亲会派人来逼迫自己回家,说不定还会为自己的荒唐举动受到惩罚,可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想办法见到施念慈。
他想,施念慈还是愿意回嘉峪关的,不然,为什么她被绑匪放回来不直接回肃州而是到嘉峪关呢?怪就怪在老爹身上,他硬要说什么名节。按他的想法,只要自己乐意,管他狗屁的名节干吗?
正在炕上胡思乱想着,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了。
季良策吓了一跳,以为是施文义又来找他的茬子呢。挨了那一拳之后,他从心底里有点怕这个大舅子哥。可是,他定睛一看,心里乐了,原来是施念慈。
施念慈被一股怒气顶着,闯入客房前,还想着见着季良策,就把他从炕上拎起来,扔出大门去。当她面对躺在炕上的季良策时,却又愣在了当地。季良策的鼻子肿得很高,连两边的腮帮子也跟着像发面团一般鼓了起来,整个脸全变了形,看起来滑稽可笑。
施念慈满腔的仇恨与愤怒都是由此人引起,看着他的怪样,实在又笑不出来。
“你来啦?请坐。”季良策的鼻子不通气,说话声音囔着,怪怪的。
施念慈突然又来了气:“你真是个贱胚子,挨了打还美气得很呢?嗯?”
季良策翻身坐起来,靠在炕头上:“挨打是我自找的,活该。”
“你真不要脸!”
“你骂得对!骂得好!”
“你爹,你,你们一家人,都不是个东西!”
“骂我就可以了,我家里人就别骂了!”
“我偏骂,就不是东西!”
“好。骂得好!”
“你到底想做啥?”
“接你回家。”
“回家?谁跟你回家?”
“你唦。”
“我凭啥跟你回嘛。”
“你是我的夫人,太太,说句乡俗,是俺的婆姨。”
“臭不要脸,谁是你的婆姨?你找你爹要你的婆姨去。”
“我爹做事是欠妥当,可我是真心的。满大清朝,我只娶你施念慈一个女子,永不纳妾。”
“你还想纳妾?”
“我对王母娘娘起誓,今生今世,绝不纳妾。”季良策举起右手的拳头。
施念慈更加气愤了:“我只说你是个坏人,没想到你坏得那么狠。快着些滚吧!你待在这里,一千年也没人跟走的。”
季良策真诚地表白:“我不要一千年,我只要一天。我求你明天跟我走。”
“你真想让我跟你走?”施念慈忽然平静地问。
“真心的。要不真心,让我瞎眼瘸腿。”
“那好,你起来,俺们现在就走。”
“现在?”
“是呀,你不愿意?”
“愿意,愿意。不过,你能否等我先回嘉峪关,等我说好了,再来车轿接你?”
“闹了半天,你还是没地方安排我?”
季良策翻身下炕:“不是没地方,是我不能如此草率地对待你。”
施念慈冷笑了一声:“那你打算咋样对待我呢?”
季良策激动地说:“我这就回嘉峪关,你等我的信息。安排好就来接你。”
“那好,我等着你。”
季良策脸色因激动更加变形了:“我这就回去。”
他匆匆忙忙地朝外就走,与站在门外的施文忠和小元子差点碰了个对面。
“慢着。”施文忠伸手拦住了他。
季良策抬头看见是施文忠,赶紧行礼:“大哥,我要赶回嘉峪关呢。”
施文忠脸色似铁:“你们方才说的,我都听见了。我明了对你说吧,这事不能成。”
“咋不能成?念慈都答应哩。”
“她答应了不算数。”
“哥,我答应了,算数。”施念慈不慌不忙地说。
“妹妹,你疯了?”
“我就是疯了。爹都说我疯了。”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我是施家泼出去的水,与这块地没有瓜葛了。”
“大大那是说的气话。”
“是气话也是实话,我总不能一辈子在施家吧。”
“你就不能再找个好人家?非要到那姓季的家里?”
“哥,这不是你该说的话。”
“我是生气。咱是嫁不出去还是咋的?”
“生气也不能不讲理,只要他季家收回休书,我就还是季家的人。”
季良策在旁边插嘴:“你放心,我一定要爹爹收回休书。”
施文忠哼了一声:“只怕是你一相情愿。”
正说着,施保过来禀报:“大少爷,嘉峪关来人了,老爷让你过去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