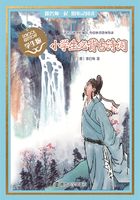那个大雪坠落的冬夜离开南京后,这几年内也曾几次回去过那座伤城,清空人事关系、转出户口档案、参加节目录影、带着母亲的病例报告咨询专家门诊等,但都俱已是路人,是游子,是过客,不再是曾居住在这座城时的模样。
它与我气质不再融合。它依旧车水马龙欣欣向荣,它与我无言生分。
我在这座城度过了四个春雷夏荷秋月冬雪,锐志消磨,梦想倦怠,偶尔眯起眼,那些深埋在大脑地壳中的潮湿的往事会像深海游鱼,翩翩汇聚。
这是一段偷来的片刻欢愉时光。
春天过后,一个人租住在繁华喧嚣的湖南路与马台街交会处的一栋破旧衰老的公寓,七楼的位置可以看到层层高楼遮掩之中的日光与云朵。有时夜晚伫立在窗前,也正好俯瞰整个狮子桥。
有时候,那里会摆开一条长龙的美食街。我会在微雨霓虹的傍晚,下了班去流连那些小吃摊,蚵仔煎、盐酥鸡、油炸章鱼、芋圆……那些美味的油腻的,好像从宝岛台湾漂浪过海来看我的,迷人的食物。
有时,我会在狮子桥南首等人,那里也好似成了迎来送往的约定俗成的码头,会经常看到远远拥抱然后亲吻脸颊的母女、中学生模样的两个男孩子、牵着手的年轻恋人。
始终记得有人说“第一滴雨淹没了夏天”。那个人,有孩童一般皎洁的天真,还有一颗暧昧温暖的痣。在狮子桥上,我们曾面对面站定,无声微笑;我们曾踩着有薄薄积水的地面,一边散步一边穿梭,直到月色染白了初夏的树枝。
有时,会下七楼,拐过楼下一家盐水鸭店,径直向东走一两站路,过天桥,走地下道,穿过高大的城墙建筑,会抵达玄武湖。
绕着湖面,融入三三两两闲淡擦肩的行人。路边是绿荫稀朗的树和建构成青白底色的石阶。
盛夏来临时分,湖中会绽放睡莲,还会听到蛙鼓声与蝉鸣,夜晚也会有居住附近的人如织来乘凉。我只逗留了一夏,竟未赶得上满池荷花的大好景色,想来定是晚风摇曳,莲香坦诚,有无惧无悔的美震慑出来。
与那时候工作的大厦距离不远,下班后,会从仅隔了一盏红绿灯的便利超市辗转买回新鲜大米、肉、鸡蛋、蔬菜、牛奶以及油盐酱醋。随心搭配,简易煮食,然后打开电脑,一边看剧集,一边用一个人的晚餐。无须迎合磨合,自得其乐。
若是十点下了夜班,收工回去的时候,路过巷子里的夜市,会买回五两盐水鸭肝,然后在深夜开机敲字。许多深夜里诞生的文字堆在一起,杂乱无章,竟成了习惯,也成了消磨漫长的无法入眠的长夜的好利器。
闹市的喧嚣街景与繁华夜色,即使高楼也不胜深眠。有时夜半醒来,恍惚还躺在方山脚下,校园的狭仄宿舍。以为窗外正下小雨,天色灰蒙蒙总是看不清它的脸孔。学校的升旗广播又开始折腾,而我还在与人在一起长谈,一直不曾离散。
也许你从来并不属于那座城,只是停泊过,却始终记得它的气味。你曾居住在它的一条街道,一座高楼。你曾记得,窗外楼下喧嚣的商业街上,挤公交的上班族、成群的学生与单车、买菜的居家男人或全职主妇、牵手的恋人们,在不同时段不同角落,次第出现在大街上汹涌成海,在清晨、在日暮、在深夜,空气中全部是烟火幸福的气味。
你会在那座城中有一个熟识的理发师,从前每次去这家店,都是只给他剪。像恋人种植出了默契,知道怎样的手势才是最宠爱。即使每次交集的散场都是他说慢走,你说谢谢,然后各自淹没在这大街上每天汹涌不息的人流中。你也会在那座城中有一家念旧的小吃店,每个清晨或者黄昏,你上班太迟或者下班太晚,都会去那里吃一碗牛肉饭或者小馄饨。在母亲不在身边的那些时候,那家食物的口味让你想起了故乡,暗澜潮生,心生温柔。
每一座城市都有这么一群忧伤的年轻人,即使他们的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但还是会漂亮地笑着活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知道日后丰盛的生活,总需要当下付出庞大的代价。
每天清晨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啃着面包去挤公交上班,傍晚的时候又单肩背着沉重的公文包回到自己租住的蜗居,即使谁也看不清楚未来到底长什么样子,即使汇流进大街上的人群会渺小到什么也不是,可是这么多年我们还是过来了,想想其实很伟大。
那一年,我在这座城看过了初春的桃花,再过几天,就会遇见冬雪袭来。2月1日是正月初六,那天离开母亲,我在奔赴这座城市的火车上倚着行李箱打出的一条信息至今还躺在发件箱:
“明早返宁,指碰未竟的彼地梦想,没有胜算,徒有倔强,太多牵挂皆做日后补偿,谁给我力量,催醒我成长,并且不悲伤。”
今时今日看来,除了押韵尚好,实沦笑谈一场。而你或者他,那天收到它的时候是否有感同身受我幼稚的虔诚,在那些双目明亮又心怀图景的岁月,我曾在这座城的身上寄托过多么真挚而浓烈、汹涌却惨淡的梦想。
直到血肉模糊,灰飞烟灭。
旖旎的初遇,一个一个似小青与法海彻骨的离散。来得耀眼,走得迅疾。这旅途真的不曲折,只是最后还是我们一个。
蔡康永说,“人与人之间只有一段,你会错过你的,我会错过我的,公平。”友情或爱情,亲密或疏离,早该明白脚本已先写定。这一站路,我与你,下一段戏,换风景。最浓烈的对手戏已杀青,我们只能陪对方走到这里,以后的寂寞,会有新的灵魂来填写剧情。
又如同,两个路人,驻足靠在街角,借个火,点根烟,氤氲一轮烟圈,冷却半枚烟蒂,尔后交错忘怀,足够。
天气开始寒冷的时候,那是2009年的冬天,人们刚刚度过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顾蔓桢小姐来宁,说见个面吧,我说好吧。于是颇有些顾蔓桢和沈世钧多年以后在桃花树下重逢的意思。各自聊起这些年的遇历与改变。只是,我已经回不去了,你也回不去了,我们都回不去了。每天都会发生许多事,一个星期内,一个月内,一年之内,我们都会与某些人遇见,与某些人告别,与某些人说爱,与某些人再也不见。
彼时我想,指不定哪天,我也会告别。夜太漆黑,路太漫长,而我也终于参透。不再希冀,谢幕退场。然后喂马,劈柴,养孩子,有一所房子,面朝菜市,春暖花开。
然后,一年之内,2010年的春天,我就真的告别了。
在我终于学会熟练地操一口地道的南京方言,可以在大街上给初到南京念书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指路,可以在每天早上去菜市场跟大妈们侃谈砍价然后买回一堆蔬菜生肉鸡蛋抱回我的七楼,可以模糊了清瘦眉眼隐失在汹涌人海再也找不出来时。
那一年来,我在南京看尽无常,比如迈克尔?杰克逊死掉,不老玉女酒井法子因吸毒被判缓刑,周迅不再爱文艺男青年,萧亚轩一夜之间经历了璀璨与永失,罗家英与汪明荃终于结婚。
南京入选2009年度“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十大城市时,我开始听李志的《我爱南京》,而后我终于决定离开。
曾戏谑地对友人讲,要是年末离宁,多想在走之前去找一找那个写过《我的帝王生涯》的男作家。停船暂借问,或曾住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