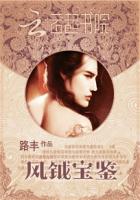体型较大的青鱼草鱼非常敏感,只要有一点光亮,一点动静,立即埋头窜逃。只有鲇鱼、鲤鱼、鲫鱼这类沉脚鱼动作迟缓。现在,人们隐蔽在凹地旁边的草丛里,不张扬,不打闹,烟头都不亮一个,静悄悄地等待。
夜色渐深了,月光洒落的凹地水面传来第一声水响,“啪——”
人们按捺着怦怦心跳继续张开耳朵听。
不久,水面又传来“啪——”“啪啪——”打水的声音。
还须继续忍耐。
紧张,心情紧张。腿脚开始灌入硬硬的力量,两手握紧拳头,呼吸开始急促,双双眼睛在如粉的月光下闪闪发亮。
打水的声音不再单调了:“啪——”“噼啪——”“噼噼啪啪——”“噼噼啪啪——”
不仅是耳朵听到声音了,眼睛也看到东西了:深灰色的长条水痕是犁铧的土脊,浅银色的长条水痕是犁铧的沟壑,一丛一丛的黑颜色是杂乱无章冒出水面的蒿草。在这一切色块色线的交错里,水面溅起东一朵西一朵银光闪烁的水花,无论深水浅水都掀起杂乱的、互相碰撞的波浪。不仅看到了水面的热闹景象,尤其令人心痒难捞的是一条条纵身跃起的大鱼,鲤鱼、鳙鱼、青鱼、草鱼、银光闪闪地扭摆着朝天钻去,没跳太高就“砰”地砸下水来。
散籽鱼必须跳跃。要跳,要拼命跳,不跳,它肚子里的鱼籽就产不下来。
这当然是件痛苦的事。什么生命的诞生都不容易。不诞生新的生命,旧生命活下一万年也是白活。这样,诞生生命的痛苦就变成了快乐。
散籽鱼没有小的,未成年鱼类没有享受这份快乐的权利。跳了一阵,力气用得差不多了,它们就腆着肚皮沿水中的土脊磨擦,一遍遍地,擦着游过去,又擦着游过来,于是变成了飞不起来的笨拙的蝴蝶群落,变成了秋风拂下的满地肥厚的落叶。
有些鱼并非一到场就急急忙忙去当不要命的产妇。这些鱼知道怎么悠着来。它们一对对,一群群,先把场地旅游一番,沿着沟壑,看看别人的风景,然后物色一个合适的地方,你嗅嗅我,我亲亲你,温情温情,缠绵缠绵。更有甚者,比如鲇鱼,一条雌鱼可能同来几条数十条忘情的追随者。到时候了,也不必抛绣球,大家一齐上,绕着雌鱼,你缠住脑袋,你缠住脖颈,你缠住胸脯,你缠住肚子,你呢,缠尾巴吧。还不够,还有许多的后续队员,又等不及,没什么讲究了,管他呢,一股脑儿,见缝插针。你缠了我,我恨你。甩!你把我甩下来?那哪行!冲上去!有些快要入港的就被这些捣蛋鬼吵得怒从心头起,张开血盆大口咬上去!
每到这时候,渔人看见的就是一团在水里胡乱翻滚的、一会儿白(肚皮)一会儿黑(鱼背)的鱼球。因为鲇鱼还能发出声音,这就是一团叽叽叽叽叫得可怕的怪物。没见过这场面的渔人,在黑漆漆的夜里,在你单独一人,在大片茫茫水域,不吓一跳才怪!
很多人,心清静些、仁善些的,性格懦弱些、凝重些的,就拔腿走开,不要了。当然许多人饥不择食,一把捞上来,回家一看,许多鱼已被咬得遍体鳞伤。
骆飞亮现在有个做什么事都跟秦天走的习惯。除了练石锁,天天捋起衣袖看肌肉,还注意起自己的形象来。学着他们拔胡子,用草药浸洗头上的癞疤。因为见自己脸颊日益地凹陷下去,圆脸变成长脸了,就找了两颗圆圆的石头晚上睡觉时噙在嘴里,要把腮帮子再圆鼓起来。谁知那次忘了掏就睡着了,吞进肚里去了。所幸第二天拉了出来,却也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他什么渔具都没有,到秦天那里借了把渔叉,正虎视眈眈蹲在旁边。
本来还应该等一等,忽然听到咚咚咚脚步声。骆飞亮说:“姚先喜下去了!”
“走!”
秦天带着这伙人一路跳跃着奔下去。
随着急促杂沓的脚步和难以抑制的兴奋的吆喝,人们扑向月光下的水洼地。
刚刚甩得晕头晕脑的青鱼草鱼立即嗅到了危险气味,感到了水波的不寻常震动,紧张窜动起来。这种急促游动形成的箭形水浪马上被秦天这类经验丰富的猎手发现,“噗”地一声,一只篾罩扑头盖来,鱼头就重重撞在篾罩上。篾罩全力压住,丝毫不动。紧接着一只手从罩上圆洞伸下来。罩里天地太小,它被强压在泥地上,两支仿佛长着眼睛的手指立即戳进鱼鳃,并且狠狠将它扣住。尽管你使尽全力拍打,却只能打起虚张声势的水花。
鱼被提起来了,摁进半个围椅大的渔篓里。
骆飞亮一边紧张激动地号叫,一边跌跌撞撞东一叉西一戳。明明白白看到一条鱼,死劲一叉叉下去,却深深扎进泥土里。等他骂骂咧咧拔起叉来,那狗日的已蹿出几丈远。只得举叉又追。水虽然不深,地面却高低不平。跌倒又爬起,爬起又跌倒,一连追了好远,眼看前面横着个土坎,“猪压的,这下看你往哪跑!”咒骂着就一叉飞过去,只听“啪啦”一声,那家伙忽地跃起,朝他脑袋狠狠扇了一尾巴,落到身后去了。待他回头再追,它已没了身影。
只听到秦天在叫:“来!跟我守渔篮,分一半给你!”
“不!我要自己捉!”骆飞亮说罢朝一道水浪跃身扑去,只听“哎哟”一声,鱼没扑着,胸前被大鳜鱼鱼脊刺出一溜小洞,手一摸,点点血迹连成一片,立即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他一声不吭,熟练地朝自己手心撒泡尿,往胸前一抹,揉揉朦朦胧胧的眼睛,又猫腰向四周窥视。
这是一片奇妙的水洼地。跳动的人影,飞跃的渔叉,低沉的吼叫,短促的詈骂。月光下一团团水花忽地冲起,到处是“扑通、扑通”的响声。逃窜的大鱼激起条条如箭的水浪,让那些使叉使耙专拣大鱼的人又兴奋刺激又气喘吁吁。手掌大个的鲫鱼群被追赶得“哗啦”一声一齐跃起,仿佛朝人迎面泼来一盆亮闪闪的银箔片儿,使你眼花缭乱,心痒难耐,又喜又骂。鲇鱼的最大本领就是钻泥。你看到一群鲇鱼在哗啦哗啦摆水,横着一耙撩过去,一条两条拴在你耙齿上了,其余的尾巴一搅,一崭齐的朝四周埋头就钻,好像四面都是它们的防空洞。这时就得放下耙子手脚并用去泥里掏。泥又不是纯粹的淤泥,半沙半泥里横七竖八穿插着众多的冬茅草根、霸根草根、黑蒿草根,这些强劲有力的根须仿佛编织成无数个钢筋网,要逮住鱼就得咬牙切齿拔起它们,常常是草根勒得双手皮开肉裂,那些滑溜溜家伙又从你眼皮下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