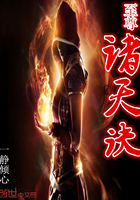日暮时分的华阳城,笼罩在火烧云那赤光杂烟的天光下,苍茫的天空此刻瑰丽如琉璃。城中的西路街头,人来人往,串串灯笼如璎珞明珠般耀眼。飞阁流丹的遗玉楼中烛火明灭,檐牙高啄恰似燕尾银钩几欲挑破天幕。
楼内歌台暖响,春光融融,鎏金狻猊香炉里焚着椒兰,清香缭绕,烟斜雾横。薄若蝉翼的鲛绡帐缓缓飘摇,时有时无地拂过美人们的钗环,葡萄美酒夜光杯在灯火流转下闪烁着迷幻的光芒。
楼层阁间里的贵介世家们百无聊赖地斟着美酒,对着满桌的玉盘珍馐却是一点兴趣也无。“铮”的一声,一指琴弦挑破这沉闷的氛围,这些纷奢惯了的贵介们慵懒而饶有兴味地抬眸看去,一时间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殿中央的白玉台上,紫藤色的鲛绡帐环绕在玉台四周,恰如紫藤萝瀑布般流淌而下,衬得玉台越发地流光溢彩。不疾不徐地,一首清绝的曲子如风过竹林般拂过楼阁的每个角落,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莫不如此。这样雅致清贵的曲子本不该出现在这个地方。
伴着曲子,鲛绡帐缓缓升起,楼内只剩下琴曲,连一点儿斟酒的杂音也消失了。杜蘅色的蜀锦裙摆柔顺地流曳在玉台,冷蕊花般修纤的双手在琴弦上轻拢慢拈,紫帐一旋,最终露出琴姬荣曜秋菊的容颜。直到琴曲停息已近一刻钟的时候,满堂依然安静得仿佛能听到鲛绡扶摇的声音。
这时,遗玉楼的幸娘轻移莲步,笑吟吟地走出来,敛衽一礼说:“不知冬至姑娘这一曲,贵客们可听得尽兴呢?”
“好!”不知是谁喝彩,就如石击平湖般,鼓掌叫好声顿时如涟漪般迅速扩散开去,一时间掌声如雷。
幸娘恰到好处地控制着笑容,得体而不得意。她侧开身子将冬至让在众人面前,笑着说:“还是老规矩,只是冬至姑娘还年轻,还请诸位怜香惜玉,不要吓着小美人。”
“不劳幸娘提醒,”一名华服男子喊道,“三千两!”
“不知阁下是三千两白银还是黄金呢?”一名年轻贵族笑着一拱手说,“在下出三千斛东海鲛珠。”此言一出满座哗然,哪怕一千斛鲛珠的价值也远超三千两黄金。
又有人慢条斯理地说道:“四千斛鲛珠!”又是一阵惊呼。
价钱越来越高,出价者前赴后继,叫价声此起彼伏,幸娘几乎笑得合不拢嘴,却故意叹息着说:“哎,若是大爷们愿意发发慈悲,把这冬至姑娘留在我这楼里才好呢,若得如此,这遗玉楼的花魁立时便易主了!”
冬至始终微抿着唇,端雅地站在这喧嚣的中心,视若无睹的样子,仿佛她只是个作壁上观的人。
最终,这场交易以六千斛鲛珠的惊人高价盖棺定论,那个志得意满的中年贵族遥遥地朝芒种伸出手,下颌一抬,示意她走过来。冬至无动于衷,犹然站着。
客人不由得蹙起眉头,幸娘一璧陪笑,一璧劝着:“哎呀,都怪我,忘了告诉姑娘规矩,姑娘定是见大人威风凛凛,因此不敢动呢。”客人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他随意地一挥手,身后的侍从们立即身手敏捷地跃到玉台去带人。六个魁梧男子一齐行礼道:“请姑娘上楼!”冬至淡淡地抬眸扫了他们一眼,将手拢在宽袖中。
等了片刻后,见她依然纹丝不动,一名侍卫走上前道:“得罪了。”却也不敢真的碰她,侍卫随手扯下一匹鲛绡纱,运了柔劲一抖,鲛纱顿时如灵蛇般卷向冬至,冬至侧身躲过,身形忽地掠至侍卫身前,柔韧至极的一掌,将魁梧的汉子打飞数丈远,那侍卫摔在地上,呻吟不止。楼阁再次安静下去,台上的侍卫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朝冬至抓去。当先一个人还未触及冬至衣袍,立即痛呼一声退回去,他痛苦地用手捂住鲜血淋漓的手腕。冬至手中寒芒一闪,一柄尖锐的铜簪赫然握在手中。片刻间,冬至竟将六名侍卫都打倒在地。
客人怒不可遏,他狠狠地一拍桌子吼道:“都给我上。”
一时间玉台前被带剑侍卫围得水泄不通,冬至忽然倒转簪头抵着自己的脖颈,尖锐的铜簪立即在她雪色的肌肤上刺出一滴鲜血。
客人急忙喊道:“不能让她死!”
这时,幸娘居然好整以暇地轻轻拍了拍掌,玉台上突然彩光缭绕,晃花了所有人的眼。只听“叮”的一声轻响,铜簪坠落,光芒消失时,只见冬至虚脱一般委顿在台上,她紧抿的唇里难以抑制地溢出一串呻吟。
幸娘衔着一抹妩媚而冰冷的笑说:“这玉台上所施的法术,正是为姑娘这样身怀绝技的人特意安排的,不惜命的美人儿我见过不少,但还从来没有人能死在遗玉楼的。”
“哦?她究竟欠你什么了,连自己的生死都管不得了?”一道清朗的声音不紧不慢地说道。
众人闻言,心下都有些惊讶,循声看去,朱栏楼阁边上站着一名少年,白衣襕衫,容止清润舒朗如泼墨画中的仙。
幸娘见他气度不凡,先是一愣,很快便圆滑地笑说:“先生此言差矣,冬至姑娘并非欠我,而是欠这遗玉楼,我不过是按楼中的规矩办事。”
少年浅浅地笑:“好,那就按你这里的规矩办,你要不庭山的白玉,苍梧野的青碧,还是灵山的琅玕?”这三样都是稀世之宝,好些人哂笑起来,少年不以为意,他将手伸进鲛绡帐里,从桌上端出了一样东西呈在众人面前。
乍一看,只见莹润剔透的玛瑙盘上竟生长出一枝如蛟似虬的古木枝干,赤木紫华,妍媚流变。但稍一细看,整株花树都是美玉雕琢而成,白色花蕊处则是极细小精致的珍珠。整个玉雕巧夺天工,世所罕见。
有人惊呼:“琅玕!真的是琅玕!”众人哗然。琅玕树是灵山上生长的一种奇树,通体为美玉,所结出的果实更是璀璨无比的五彩玉璧。
见惯了奇珍异宝的幸娘,几乎被这明艳的珠光照得窒息,好一会儿才叹息着说:“小先生真是多情,但幸娘仍是做不了主,如今冬至姑娘已是澹台大人的人了。小先生若有话,请对澹台大人说吧。”
澹台大人冷冷地盯了少年一眼说:“先生的琅玕的确华贵非常,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小先生还是仔细收好吧。”
少年放下琅玕,笑笑说:“看来大人对冬至姑娘真是很中意。”话音刚落,他突然翻身从栏杆上跃下,径直朝台上走去。
澹台大人大喊道:“拦住他!”
少年的袖中滑下一枝一指粗的青竹,如剑般握在手中。当先一名侍卫挥舞着大刀横劈而来,少年持竹一挡,削铁如泥的刀锋竟无法砍下竹枝,青光在少年手中一转,侍卫的刀锵然落地,少年反手一掌,将侍卫震倒在地,厮杀一触即发,淡青光芒游走于侍卫之间,迅疾地如一痕流萤光影。
很快,少年掠至台上,抱起冬至,纵身掠上顶楼窗台,破窗而出。
他高高地站在屋顶上,朗声喊道:“绿耳!”
远处突然响起马蹄声,一匹青鬃骏马在大街上飞奔而来,骏马纵蹄间,背上忽然展开一双三丈多长的翅膀,顺势飞上天际。少年抱着冬至纵身一跃,骑在马上。
绿耳马振翼而去,一些惊呆了的路人只看到一线天青色的影子在空中划过,如一痕飞鸿。
绿耳在高空中飞驰,很快,身后出现一些追袭的声音,远远地看去,也是数十匹带翼飞马,少年立即揽住冬至从马背上跃下,他们的脚下聚起洁白祥云,似虚似实,托着他们飞往另一个方向。
从玉台上离开后,冬至的体力便渐渐地恢复,耳边的风声呼啸不绝,流云似触手可得,这久违的感觉令冬至有些怔忪。
稳稳地落在一个小湖岸上,少年看向冬至微笑着问:“姑娘没事吧?”
冬至的手还被他握住,她微微蹙眉说:“少侠请放手。”
少年连忙松开手说:“哎,你别生气。”话音落下时,“他”忽然变成了一名荷衣蕙带的少女。她的身形并不挺拔而是婀娜多姿,容颜也不清俊,而是倾国倾城。。
淡漠如冬至,一时间也有些怔愣。
“小女子熏华,”女孩笑着说。
冬至没有忙着道谢,而是沉默地审视着面前的女孩,冷静地问:“你是仙人吗?”
熏华略一犹疑,淡淡笑道:“姑娘何出此言?”
冬至淡淡地说:“你方才施展的虽然只是寻常武功,但是你易容所用的幻术,寻常天人巫祝难以领悟,是只有仙人才能施展的仙法。”
“哦,原来如此,”熏华浅浅一笑,并不否认。
冬至向她轻轻一施礼,神态从容,没有平常人见到仙家的惊喜与恭谨,仅有几分淡淡的感激:“小女子命如草芥,全凭仙子出手相救,冬至无以为报,在此拜谢。”
这令熏华有些腼腆起来,忙说:“姑娘言重了。”这位仙子应当是冬至见过的最平易近人的仙家。
熏华端详着冬至,说:“我看姑娘也不是常人呢,你身中葶苎散之毒,两个时辰内都不可以调动内力,即便如此,你还是打倒了那些身经百战的侍卫,若你可以调用内力,武功应当堪比江湖上的一流高手。恕我直言,姑娘不仅身怀绝技,眼力见识也不凡,却流落于风月场所,莫非是家道中落吗?”
冬至神色平静,无波无韵地道:“我不能说,请仙子见谅。”
“无妨,”熏华淡然一笑说。
“那么,就此别过。”
“姑娘请稍等,”熏华叫住冬至,她转身从湖里掬了一捧水,她的手上流转着淡紫的光芒,那捧水悬浮在她的掌心上渐渐聚合成一大一小两只麒麟,水雕最终化成两尊白玉雕,纤毫毕现、栩栩如生。
冬至忽然想到,遗玉楼中的那枝琅玕或许也是这样变成的。
熏华手一抛,冬至下意识地接住了,熏华笑说:“两枚小玩物,姑娘若不嫌弃就请收下吧。”她虽然言笑晏晏,但话语里却有种不容拒绝的味道。
两枚白玉麒麟合在一起约摸手掌大小,玲珑精细,看不出什么异样,但冬至仍是犹疑地看着她:“仙子为何……”
熏华的眸色柔和,她的目光有如月色一般拂过冬至的眼角眉梢,语气中掺杂着几分高深:“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故人的影子。”
简陋的茶棚,寥寥地坐着几名停歇的人。一名少女粗布葛衣,戴着坠白纱的帷帽,径直往山路上走去。茶棚里的老人家喊道:“小姑娘,别往上走了,那山是吃人的。”
少女回头看向老人,淡淡颔首说:“多谢老人家提醒。”说完,脚步不停地往山上走去。
“唉,”老者无奈地摇摇头,“再不太平的日子也要过下去啊,这是何苦……”
冬至拂开重重青叶疏影,走在树影斑驳的路上,空中似乎飘着些青楸离霜的味道。前方缓缓转出高耸入云的巨大古木,遮天蔽日,人走在这巨木林中,似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高高的树冠上传来奇异的鸟鸣声,听起来很遥远,像某种哀怨的呼唤。此间寂寥无人、凄神彻骨、悄怆幽邃。
一道笛声于树林间悄然响起,笛音韵律悠长,从容清扬。
“什么人!”冬至警觉地喝道。
笛声戛然而止。一道声音缓缓地响起,遥远得仿佛从高耸入云的树冠上传来:“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听起来似乎是一名年轻女子的声音,声线清和婉转,遥远却清晰。
“我知道,枭阳山,”冬至抬头望着头顶上方冲入云霄的树冠,镇定地回答,她并没有因为距离而提高声调,依然用冷静平淡的语气说话。
而对方显然也没有受到距离的影响,嗓音和煦地说:“那么你应该也知道,有多少人被这座山吞噬。我是这座山中的山鬼,驻守着这里上百年,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葬送在这里。每个人登上枭阳山都有自己的目的,为数最多的便是为了去往凡界。这部分人通常是天地间的游侠,或者是罪恶滔天的逃犯,这些人罔顾自己或他人的生命,没有仙人会送他们渡过天梯,想要去往凡界,就只有涉险走枭阳山这一条路。可是每个人都不知道,这条路有多漫长,凡人想要走到尽头需要十年,然而,在枭阳山中,很少人能活过三天。你根本不清楚这里有多危险。”
“我很清楚,”冬至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如何我必须去凡界,请山鬼大人网开一面。”
山鬼是由天帝指派,守卫一方山水的天人,他们通常选自精通灵术的巫祝,他们永远年轻,有着近八百年的寿命,虽然没有仙家呼风唤雨的仙法,却有着介于人与仙之间的力量,因此被称作山鬼。
山鬼轻喟道:“山鬼的职责只是守护一方水土安康,封印这里的妖魔凶兽,所以我不会阻拦远方来的旅客。我只想告诉你,上百年的时间里,从没有人活着离开枭阳山。”
山鬼的声音越来越遥远,最终就如同一缕烟气般在空中消散。
冬至轻声道:“多谢。”
清寒的风不时在林间穿梭而过,风行草偃。冬至摘下帷帽,虽然是白天,但在树冠的遮蔽下,林中的光线暗淡得像傍晚时分。
忽然,她的身后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冬至的手向后一挥,手中帷帽迅疾地旋转着朝后方飞去,如离弦之箭。窜入半人高的草丛,深深嵌入土地里。
似乎什么也没有,下一刻,草丛中忽然游出数道黑影,乍看和普通的影子没什么两样,然而,这些黑影贴着地面像游蛇一样飞快地蔓延而来。
冬至的身形敏捷地一掠,飞快地奔逃。那些影子紧追不舍,距离始终没有拉开,四周不断地涌现出更多的黑影,好几次险些将冬至包围,冬至如兔起鹘落般一跃,总是堪堪从间隙中划过。
她的袖中滑下一只匕首,在空中一拧身,朝后飞快地一掷,将黑影钉在地上,影子略一停顿,依然如潮水般迅疾地滑来,冬至被围追堵截,距离越来越近,冬至纵身一跃,踏上树身,一借力,高高地跃出数丈远。数道黑影从地面上窜起,如千丈的黑色丝绸在空中绵延,一道黑影如蛇般咬住空中冬至的脚踝,一甩,将冬至重重地拍在树身上。她的脑中嗡的一下,又被狠狠地砸在地上,被摔得七荤八素。
她咬着牙,很快从地上爬起,硬是忍住身上的痛楚往缺口处跑,前方出现一个斜坡,她刚刚逃到边缘,一道黑影如箭般洞穿了她的肩膀,她眼前一黑,一头栽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她的意识短暂地清醒了一瞬,眼睛艰难地睁开,枝桠疏松,清辉映夜阑,一株古木的树干上伏着一只麒麟兽,俯首静静地看着她,月光似霰缓缓地流转在青甲麟羽上,泛出炫目的光彩。她把目光转开,看到一只更巨大的麒麟伏在地上,绀青的眸子像夜明珠般发着幽幽的光。她终于忍不住合上双眼。
真正醒来的时候,她感到有一样柔软潮湿的东西贴在脸上,轻轻蹭过。睁开眼睛便看到一只麒麟正低着头,亲昵地舔她的脸。她伸手把它推开,麒麟就很乖巧地退开一步。她仰躺在地上,映入眼帘的是傍晚时暮云叆叇的天空,绚烂的霞光染在她的眼眸里只余下一脉空寂灰暗,如同燃尽的香灰。
这里显然不是枭阳山,辽阔的原野,草地茸茸似柔毡,夕阳余温分外温柔。她起身察看伤势,惊讶地发现所有受伤的地方都已经完好如初。
一大一小两只麒麟温顺安和地伏在她身旁的草地上,冬至淡淡地扫了它们一眼,目光转开,寂寂地望着天边的晚霞,她不知道是谁救了她,心中只觉得无比地讽刺,以她的能力,在枭阳山连一天都活不下去。
“你很绝望?”一个清淡的嗓音忽然从不远处缓缓地传来。
冬至抬眸看去,便见一只巨大的似狮的兽朝这里缓步走来,它的步履稳健,带着兽类特有的优雅,那如银似雪的毛皮在暮光笼罩下,熠熠生辉。两只麒麟兽看到它,都露出恭谨的模样。
它开口说:“你原本是北天的凰鸟,承蒙神家帝子指点,法力高超,终身守护北天共工台。然而十年前天帝帝俊派兵攻打北天,北天倾颓,你身为北天臣子被俘,仙术被废,双翼也被斩断。如今的你,已经无法自由地上天入地。但你因为君臣之义,不顾一切也要来凡界,为了寻找高阳氏的血脉。”
冬至惊疑地打量这只异兽,戒备地问:“何方神圣?”
它轻轻地笑了:“想一想,你的师傅,应该说到过我。”
冬至审视着它,目中蓦地划过一抹惊讶与了然。
“想到了吗?”雪色的兽说。
霎时,流霰般的白光在兽的四周飘飖,如雨落雪舞,它在这片光影里化成了一名轻袍缓带的清俊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