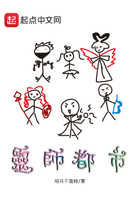回望来时路,直面人生,你会想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最初的心动,最后一次约会,最痛苦的记忆,当你沉思时,你就把故事写给你自己吧,就当作是送给你自己的礼物。
直面人生
吴华/内蒙古包头工学院
如果让我回过头来重新选择,我还是选择离开大连,尽管那是一个美得逼人的城市。
大连北京同样有着夺人之处,独闯北京,是我经过反复的权衡,最后定下的。因为我的路在前方,浅浅的海水能给人灵感,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每一个人都要发展,都要不断地接受新的挑战。
离开大连的最后一顿饭,我是咬着牙吃下的。那饭并不可口,有很多骨渣,还有辣椒,我知道自己是一点辣都不能吃的人,但还是咬牙把它全吃光了,这也象一种誓言,对于前方的路,再多坎坷,再多的挫折,我都不会怕的,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我要直面人生,咬牙一步步走下去,走出自己的风格。
在大连的站台上,我抱着沉重的电脑箱子一步一步地向开往北京的火车方向靠近,那箱子很沉,而我又不能放下来,我一直被沉沉的东西压着,而前面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咬着牙往前走。前面有一个大姐,她自己推着一个行李车子轻车熟路地在前方走着,我被她的走路方式震撼了,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因为,这就是我和别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路。
我离开大连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往家里寄1000元钱,我要让母亲知道,大连给了我温暖,也让她得到了爱。更主要的,总是在外面漂泊,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很长时间不敢往家里写信,以至于不敢提到家,这充满亲情的字常常令我泪流满面。那种想家的感觉也深入骨髓。我知道,自己的动迁,总要给乡下母亲带来无谓的担心,她虽没有能力改变我的处境,可总要在乡下的路口对女儿的方向望眼欲穿,而这穿透心灵的眺望却成了我的动力,我总觉得不断向前向前向前,不仅是为自己,更多是为了我深深眷恋的白发母亲。
现在的路,在心中已有一个坚定的目标,要实现它,我知道,我的脚还要被磨出许多血泡,这没什么,我已经习惯于用一只伤脚走路,去接近自己的目标。我学会了在难中求生存,直面自己的人生。
一个不得不讲的爱情故事
曾广平/北京理工大学
任燕萍一直是齐鲁的同学。所有人都有无意地疏远齐鲁的时候,这个文静漂亮的女孩却向齐鲁伸出了温暖的手。不知道为什么,齐鲁那双孤独不屈而忧郁的黑眼睛总能令她滋生出无限的怜爱。任燕萍的父母是一家小厂的工人,虽说厂里不景气,但总比齐鲁强多了,每当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燕萍总会多带一份,趁着课间没人在意的时候,悄悄放进齐鲁的抽屉。从不要人帮助的齐鲁却从未拒绝过燕萍的关爱,他从女孩温和的目光里看到了久违的真诚与友情。阳光明媚的日子,齐鲁也会到燕萍家帮着做些家务。买米,做煤球,他几乎包下了所有的体力活,他觉得这是惟一能报答女孩的地方。一个夏天的傍晚,在燕萍家的院子里做完煤球,燕萍拎了水让他洗手,自己则在墙角洗头,齐鲁无意中看见她闭着眼睛的侧影,还有那些发着光的水珠。几只红蜻蜒低低地飞在夕阳里,一尘不染的女生的干净和美令一身尘土的齐鲁吃了一惊,几乎看人了迷。那画面成为他少年记忆中一个最美的定格。
纯洁无瑕的友情让齐鲁的生活多了份温暖,那个时候,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他心中惟一的愿望就是考上大学!在校园后面的山坡上,他们曾一起数过天上的星星,齐鲁说总有一天他会出人头地,他要让所有瞧不起他的人都后悔,他还说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买一台电扇,再也不让母亲出去捡煤渣……每当这时,燕萍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她想如果能和齐鲁考上同一所大学该多好,她一定帮他的,让他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1988年,齐鲁如愿被北京大学录取,燕萍也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师范学院。那是两个少年梦寐以求的事,他们要一起去北京了,那个大都市里,他们将开始他们人生的另一次奋斗。
然而,齐鲁还未尽兴地享受考上大学的幸福,母亲却病倒了,常年的劳累使她体力再也支撑不住。齐鲁要把母亲背进医院,母亲却死也不背,那要花一笔大钱,那是她一元一元攒下为儿子读书的学费啊!齐鲁哭了,他说:“妈,你要不去看病,我宁肯不上大学!”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燕萍陪齐鲁送他母亲去了医院。她将500元钱塞进齐鲁的手中。那是家里人为她准备的生活费用,她说,自己读的是师范,省一点能行。这回齐鲁说什么也不肯,燕萍说,算我借你的,到时还我好了。
齐鲁这才默默地收下了。
他们的爱情没有盟约。
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齐鲁与燕萍的手第一次握在了一起。齐鲁涨红脸地说:“燕萍,到了北京该由我照顾你了。”燕萍羞涩地低下头。这一定就是爱情了,燕萍幸福地想。窗外,故乡正一点点地远去。北京是陌生而又熟悉的城市,齐鲁和燕萍因为学校离得很远,一星期只能见一面,其他的日子就在想念中度过。开学没多久齐鲁就发现无论他怎样地节省,钱总不够,燕萍来看他的时候,常会不声不响地往他口袋里塞50元。她说她找了一份兼职的家教。齐鲁又惭愧又感激。燕萍在家里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可现在为了他,什么都学会了,她甚至学会了缝被子,在他宿舍的大桌子上铺了很大一片,戴着顶针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缝,长发从耳后垂下来,让齐鲁想到他小时候看到她洗头的情形。他离她很近,闻到她的发香,和被子刚被太阳晒过的味道。那个时候,他的心中总是涌着甜甜的暖流。
1990年6月,燕萍分配刚有着落,齐鲁忽然接到了妹妹的信,信上说她不打算读高中了,她想去广东打工。看着妹妹的信,齐鲁只有眼泪。晚上,他和燕萍商量,打算退学:“去打工的该是我,我不能再让妹妹为我失学!”燕萍安慰他:“你就别乱想了,过一个月我不就工作了吗?我寄钱给你妈,你这边有奖学金,还可以申请助学金,再找份兼职工作,还怕什么呢?”
燕萍分配到市郊的一所中学,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寄给齐鲁的母亲,再拿出一些补贴给齐鲁,自己过得异常省俭。那时候北京能给学生做的兼职工作并不多,每次燕萍硬塞给他钱时齐鲁总是会鼻子发酸,尤其是他去她那里,看到别的女老师都打扮得漂亮,而燕萍却总是那几件旧衣服,显很那么寒酸。齐鲁很多次对燕萍说,他以后一定会带燕萍逛一次王府井,买燕萍最想穿的衣服,带她去吃想吃的任何东西。燕萍笑着说从现在开始她就列清单。齐鲁不知道他的誓言根本没机会实现。
大四的时候,齐鲁被推荐参加学校的辩论赛。面临毕业分配,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机会,他准备得很辛苦,燕萍总是悄无声无息地就为他料理好了一切,钱、入冬的衣服,什么都不让他操心。
辩论中齐鲁渐渐注意到李散心。散心长得并不漂亮,但据说有个官位不小的爹很骄傲。想不到她在辩论中的表现会很那么好,机智而且犀利,熟了之后李散心常常约齐鲁聊天。有一天,她忽然问齐鲁:“你想留北京吗?我可以帮你。”那天晚上,齐鲁失眠了,未来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印在他的眼前。留北京,找一家好单位,所有的人都在为此拼命,自己怎么就没有好好想过呢?李散心充满傲气的脸在他眼前晃动,她既然愿意帮自己,就不能让这个机会失去。
年末转眼就到了。那天下了很大的雪,燕萍来找齐鲁,和往常不同,她的脸色很苍白,鬓角沾满了雪花。齐鲁正要问她原因,李散心忽然出现在门口。三个都愣住了,还是李散心打破了沉默,她说:“齐鲁,你出来一下,有件事告诉你。”齐鲁看了燕萍一眼,然后走出去。在走廊尽头,李散心告诉齐鲁,他的父亲的一个朋友在外贸公司工作,想从北大要人,她推荐了齐。“据说还可以安排出国,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当然!”齐鲁脱口而出。李散心幽幽笑笑,“晚上我想带你去见一下我爸,我爸可不喜欢眼光差的人。你去吗?”李散心问。
齐鲁半晌才说:“你等我一下。”回到房间,齐鲁觉得脚上似乎绑着千斤重的沉石。“燕萍,我得出去一下,为工作的事。”燕萍默默地点了点头,转过身。“你等我,一定等我!”齐鲁说。
谈话进行得很顺利,李散心的父亲似乎对他挺满意。后来李散心又邀他去跳舞,跳舞的时候,齐鲁总想着燕萍孤伶伶坐在宿合里的样子,几次想告辞,可又说不出口。
齐鲁回去的时候已过了宿舍熄灯的时间。燕萍已经走了。同学告诉他,燕萍一直在门房等他,直到熄灯才走的。齐鲁有一种揪心的痛,他跑下楼,风雪迎面扑来,那风雪曾淹没过燕萍孤单的身影。他不由得打了个冷颤,立住了。
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想了很久,也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为人,他想燕萍不是爱他吗?那他一定能理解他的选择。然而要把几年的感情一下子剪掉,他真找不到合适的词,为什么人生总有不完美的事呢?
然而一个星期后,燕萍一封短信却让他如释重负,燕萍说她累了,想分手,她认识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很照顾她。眼泪涌上齐鲁的眼睛,“燕萍抛弃了我!”这感觉令他又伤感又庆幸,现在,他谁也不欠谁的了,摆在前面的是阳光灿烂的大道。
齐鲁顺利地留在了北京,分进了那家外贸公司,李散心以一种胜利的姿态和他谈起了恋爱,一年后结了婚。日子进入了一种模式,过一天忘一天,一晃就是四年。
李散心依然很时尚,很骄傲,辩论的才能在婚姻生活里发挥得淋漓尽致。齐鲁给母亲和妹妹寄过很多的钱,但却从未接她们来过北京,散心不习惯与老人一起生活,齐鲁也从未对她提起母亲捡煤渣的身世。这年秋天,李散心被派去了美国,齐鲁的手续还在办理中。等待签证的日子,他忽然想到燕萍,自从那个风雪飘扬的夜晚之后,他再也没见她,甚至没有她的消息。他又一次坐在了电话机旁,拨通了燕萍单位的电话,结果出乎他的意外,一个同事告诉他燕萍调走了,要求去了一个很偏僻的农村,在靠近蒙古草原的地方,教小学。
齐鲁听了很震惊,因为他知道她那么喜欢北京,后来也是很困难才留北京市郊,他不能想象燕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齐鲁隐隐地觉得不安,这很可能与自己有关。放下电话,往日的那些时光回到他的眼前,尽管很苦很难,可是燕萍却能令他感到内心平静和幸福,他真不应该放她走,他相信如果他挽留她,燕萍一定不会走的。她那么爱他,但是为了能留在北京,他竟出卖了爱情,他只想当着燕萍的面对她说,是他错了。
签证下来后,齐鲁回了趟老家。这是他毕业后第二次回家,不知道为什么,他害怕踏上这块土地。临别前的夜晚,他趁着夜晚,犹豫了好久,终于敲响了燕萍父母的家。两位老人像儿时一般地欢迎了他,这让他颇感意外,接着,他却从老人口里得到一个令他悲恸的消息:燕萍已经一二年前因白血病去世了!白血病?!齐鲁从未听她讲过!!
齐鲁已经记不得是怎样离开了燕萍家,昏暗的灯光下,燕萍的父亲将一封信交给齐鲁,老人颤颤微微地说:“这是燕萍留给你的,她说等你来了才交给你……”
那封密封的信,齐鲁一直不敢去开启,直到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齐鲁才小心翼翼地把信打开。
齐鲁:
如果你正在读这封信,说明你一定来找过我了,可惜我却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牵你的手了。
现在,我静静地躺在这所山村小学的宿舍里,窗外是绿绿的叶子和小鸟的叫声,一切是那么宁静。原想把一切都深埋在心里,像我的生命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可是,我又总会忍不住拿起笔,写着你的名字,齐鲁,你相信爱情吗?你相信有一个人在那么刻骨铭心地爱着你吗?
我没有离开过你,一刻也没有,那天李散心打电话给我,说她能让你如愿以偿,我就知道我将面临人生最大的痛苦。请原谅我的放弃,原谅我的躲避,我没有力量抗争,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没有告诉你只是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负担。还记得那个风风雪夜吗?我好害怕,我真地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现在,我已经不再惧怕死亡了,在远离都市的这所小学里,老师和孩子们给了我一生最大的慰藉。
齐鲁,不要以为我怨恨你,即便对我父母,我也只是说我们的分手是我提出的。在我心里一直因你而自豪。齐鲁,真想用我的爱情告诉你这个世界的温暖,现在,还来得及吗?
任燕萍
甘原为伙夫
海艳/中国政法大学
到大连了,我背着包很憔悴地站在这块潮湿的土地上,满目沧桑。
在一家部队招待所里,穿军装的老板上下打量着我,好,留下来吧,做饭。
做饭?当大师傅,也就是人们常叫的伙夫。这要是在几个月之前,我刚跨出学校门口,我会一跺脚就走,连头也不回。可现在我不行,我必须留下来,因为我已经无路可走。
母亲病得很厉害,我带上打工半年挣的1000多元钱,领着母亲到赤峰一家最好的医院就诊,在给母亲买药时,钱包被人偷去了,手里只剩下一把母亲就诊的药条子,包里有所有的钱还有我的身份证通讯录等,就在那一刹那,我浑身上下不名一文,成了两手空空黑户,最让我纠心的是,不远处,病着的母亲正眼巴巴地向我望着。
把母亲送到开往回家的火车上,我留下来,我要向法律讨还我不应失去的东西。案发地点是归南新街派出所管辖的,他们一个姓张的办事员把我的怎丢钱的过程和钱包特征都详细地记下来,边记边说,明天我们去给你查一下,当派出所的所长回来时,却说他们工作范围内不管这些,把泪眼迷朦我像打发一个要饭的叫花子一样支出来了。
我没有把自己丢钱的事情告诉妈妈,她血压高,受不得这种巨大的打击,我一直用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来对病中的母亲。祸不单行,迟到两三天回到原单位,老板便把我炒了。我提着行李离开了我所打工的单位,流不下一滴泪,我不会勉强。尽管处境艰难。可老板为了几十块钱的电话费,却让人追到火车站。
我现在工作地点是用一个浴池改建的。我站在炒锅前,头上正对着淋浴用的喷头,用塑料布包着。军人老板把油锅下面的煤气点着,火苗子腾地一下了冲天而起,上面的油铅子滋滋条件反射地响起来,面对眼前的一切我的头一下就大了,尤其当火苗子腾空而起时,我有一种受辱的感觉。
门后放着一个垃圾桶,看了第一眼,我就不敢看第二眼,我怕自己张口就吐出来,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比家里母亲喂猪用的泔水桶还要难看,斑斑驳驳;尤其是那个门面上贴着一个男字的厕所,门经常敞开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时不时地扑进来。人在什么的环境下都能生存,无论环境的好坏。越是艰难的环境越是活得精神,那才是一种本事,尤其是一个想做大事情的人,是不为环境所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