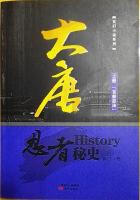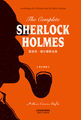白萍见他这样情形,不禁想起当日自己在他家里当书记教师门房几种兼差的时候,那时他是何等气焰,至今不及期年却已把地位翻了过儿,我已成了他的上人,他竟以仆役的身分来侍奉我了,真是人事转移,沧桑易变,令人不胜感慨。便自己独坐着思索。对于公司要如何重新组织,怎样延揽人材,过了一点多钟,才在腹中约略定了个草案。钱畏先已来察报,说是卧室业已收拾干净,请白萍去看。白萍随他走出,到了对面一明两暗的正房里。室中暖融融的,已把煤炉生起来,一切陈设,居然很是款式。白萍问畏先道:“公司里不是昭和早就断了接济,应该很穷,怎还有这样讲究的家俱陈设?”畏先道,“您没瞧见后院的演员宿舍,破烂得也和我那间门房差不多少。只有这一间,是我们东家特预备的会客室,家俱都是由东家宅里搬来的,所以好像座破大院里的皇宫,寻常老是锁着。今天是特为您开放。”说着又悄声笑道:“早先并不关锁,任演员们待客公用。只是这些男女们闹得太不像话。时常男演员同女演员借这房间来寻整夜的舒服。我也是听旁人说,今年夏初,一天东家大早晨跑了来撞到房里,恰见梅有影和那个吴翠瑛正在床上搂着同睡,惹得东家大怒,骂了一阵,把床上的被褥都叫人用火烧了,从此便锁起来,不许人进去。”说着又指着墙隅的铜床道:“所以床上光溜溜露着床篦,这都是那般狗男女的德政呢。”
白萍听着正自好笑,恰在这时,孔昭和派人送了一套很华丽的铺陈被褥。畏先忙把来摊在铜床之上,收拾得十分熨贴。白萍见他如此奔走趋跄,逢迎谄媚,究还不忍鄙薄,倒有些不大过意,便请他自去休息。钱畏先似乎还要和白萍长谈,好乘机用些巴结的功夫。及见白萍请他休息,倒误会是白萍厌烦了他,便不敢冒渎,居然做出仆役的工架,唯唯而退。迟了会儿,又走进来,买了一大盘水果糕点和香烟,放在桌上,又重换了一壶香茗。白萍忙道:“你怎这样破费?”畏先弯着腰道:“应该孝敬的,可惜天太晚,买不出好吃东西,您包涵着用。”说完又走出去。
白萍因他过分殷勤,更为不安。忽然想起他这是有所为而来,大约一来是营谋较好的位置,二来要得特别的关照,所以不惜工本,将小比大。想来官场中的钻营,也是如此。不过我能领略到这般滋味倒是奇事咧。又想到方才曾给过畏先一笔钱,他如今转用来买东西孝敬我,倒算是蜻蜒啃尾巴,自吃自,尚不为受之有愧,就领了这盛情也罢。当时便拾起个橘子,且吃且想。
桌上有现成的文房四宝,不过墨盒却已干冻,只可寻了张纸,用自己的自来水钢笔,草草地拟了个计划草案。这草案的大纲,第一,拍摄的一切器具,即日清查,利用原有之物,缺者添补。第二,公司的财政请昭和另派专人负责。第三,摄影师和布景师都要聘请高手。白萍恰有几个相识的旧友,在上海各电影公司担任着这类职务,应该通快信去接洽,要出很优厚的薪金,请他们弃彼就此。第四,要立即在各报上刊登广告,招聘演员和职员。白萍既酌定这几桩先决问题,便先拟了个广告稿,预备明天送到报馆去登,又写了几封信底,预备明天抄录后,寄到上海。这些事草草办完,已到了夜里两点多钟。白萍打了个呵欠,觉得身上微寒。看煤炉时,已将熄灭,忙自己去添了些煤。正要上床安睡,忽听外面有人轻轻敲门作响。白萍以为是畏先又来照应,便道:“你还没睡么?有什么事?”说完这句,门外并不答应,仍在继续敲着。白萍疑惑自己的声音被门壁隔阻,外面不能听见,又有些不耐烦,门外格地笑了一声,门儿向内微启,先探进一个剪发女人的头儿来,望着白萍微笑了笑接着才全身涌现。白萍才看清来人是谁,便已大吃一惊,原来竟是那个被称为东方玛丽壁克福的吴翠瑛。那吴翠瑛走进来,立刻又回手把门关上,满脸含着媚笑,向白萍点头道:“林先生,您还没睡么?这房里冷不冷?”说话时的神情,好似和白萍十分熟识,而且非常关切。白萍不由诧异,这位烂污女士三更半夜跑到我这房里,其意何居?她又怎知自己姓林?但一转想,便明白定是那梅有影所说。在白萍之意,原恨不得立刻下个逐客令,继而飨以闭门羹。不过一来因情面所关,二来为尊重女性,不好意思绝人太甚,只得应酬一下,就也点头道:“请坐,这样深夜,您有什么事见教?”吴翠瑛一扭身,便坐在床边道:“我没事,来瞧瞧你。”白萍看她脸上做出电影式的表情,不仅秋波送情,语声带媚,而且面上厚涂脂粉,眉抹得特黑,唇涂得通红,好像化好装要上镜头一样,料想必是加意装饰而来。白萍灵机一动,便想到她的来意不善,立刻在心中加了戒备,面上陪笑道:“谢谢密司,我不敢当您来瞧,请回吧。”吴翠瑛把腰一转,旋即凑到白萍面前,撅着嘴道:“官儿还有打送礼的?你怎么撵我?我偏不走。”白萍见她语意露出邪僻,又有撒赖之势,觉得不好应付,忙道:“您不走就请坐。”吴翠瑛忽又改容望着白萍一笑,仿佛表示自己得了胜利,就立起走到桌边,用手翻弄桌上散乱着的信纸,回头叫道:“林先生,这公司是您接办了,要把我们旧人完全赶走,一个不留,是不是?”白萍忙答道:“一切都由孔昭和先生处置,我个人无权干预。”吴翠瑛把嘴一撤,笑道:“我也得信啊?你有权也罢,无权也罢,林先生,我和你商量一件事,你接办公司,女演员总要用的。你用旁人也是用,落得的用我。”白萍想不到她居然同钱畏先走了同一途径。也是为营谋而来,便敷衍着答道:“我明天和孔昭和先生商量看,若有借重之处,一定请密司帮忙。”吴翠瑛又跳过来,和白萍面对面而立,两人的腹部几乎接触,一只手搭在白萍肩上撤娇儿道:“不成,敷衍我,不成。说痛快话,到底要我不要?”说着又悄声道:“只要你用我,我总对得住你,由着你的性儿还不成么?你一个人也是孤孤单单,别有福不会享。”
吴翠瑛这一说出要毛遂自荐、进贡内体的话来,几乎把白萍吓了个倒仰,真想不到她竟能如此寡廉鲜耻。倒仓卒得不着应付之策,只好退了两步,摆手道:“密司,请你自己尊重,有话也要规矩着说。”吴翠瑛又赶过来,似乎要拥抱一样,白萍反成了畏缩的女子,吴翠瑛似变作强暴的男人。两个一退一赶,直赶到墙角。白萍无处可退,只用手支撑着叫道:“吴女士,你再这样,我可要用严厉手段把你推出,那时别怨我不顾情面。”吴翠瑛挺着胸脯,眯缝着眼儿,向前凑着道:“你推,你推。你是会的,把我推到床上去。”说着就投怀入抱,直撞进白萍怀中。
白萍可没了法子,惟有扳住他的肩头向外推拽。吴翠瑛却一只手环住白萍的腰,一只手抱住脖颈,通红的嘴唇直向他颊边偎去,腰部以下也用力向白萍身边挨挤,好似要用这最后的法术把白萍的情欲引动。哪知白萍此际除了心惊以外,更不能发生其他的感情,惟有竭力推拒。吴翠瑛却只喘吁吁的笑着,不慌不忙地与白萍撕掠,因此二人滚作一团。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白萍心中才决定要高声大喊,把众人唤来,或是把这骚物儿惊跑,以解危局。却忽地门儿一声响,从外面闯然走进一个人,且走且叫道:“林先生,林先……。”最末的生字没叫出口,已改了声音喊道:“呀!这……。”原来这进来的人已看见白萍和翠瑛的活剧。白萍急忙回头,见进来的人却是钱畏先,正张着大口发怔,知道来了救星,忙叫道:“你快来,这是什么事!”吴翠瑛也出于不意,见进来了人,立刻松了白萍。白萍霍地跳开,向钱畏先发作道:“公司里怎有这样没廉耻的人?你赶快给我把她赶出去。”
钱畏先瞪着眼睛,还在怔着,猛然拉住了白萍,直拉到离吴翠瑛很远的屋角,附着白萍的耳朵很急切地低声道:“这怎么办,外面都散着人,要来捉你?”白萍大惊道:“捉我做甚么?他们是谁?”畏先道:“方才我从室里出来小便,走到墙角,就听有人说道:是时候了,咱们进去捉吧。又有人道:等一会,等翠瑛喊叫,咱们再进去。这下子起码也给姓林的小子个厉害。我听出这说话的是梅有影和周作方。另外又有人低声说。最好捉住了送官,只要翠瑛一口咬住,就告他个强奸罪。其余还有几人附和着说却听不清。我晓得这公司的职员全在那里,一定是阴谋陷害你林先生,所以赶快来……。”
白萍没等他说完,业已恍然大悟,怪不得吴翠瑛半夜来调戏自己,如此迫切,原来他们商量妥的计策。一定是吴翠瑛要把我诱得入港,在丑态百出之际,她便喊叫起来,然后大家一拥而入,她反咬一口,说我强奸,说不定把我凌辱-阵,然后送官,那时我有口也难分诉,幸而我没上圈套,不过已危险得很。然而翠瑛在扭住自己的时候,已可以喊叫,她何以迟迟不发,或者也许别有用心呢。
白萍这种思想,在脑中不过几秒钟工夫。猛又灵机大动,回头看吴翠瑛还走在原处向自己望着,暗想和她同处一室,虽有畏先在旁,也怕不妙。忙跳过把房门大敞四开,自己站在门限之间,向翠瑛叫道:“你请出去!快快!”吴翠瑛还是傲着浪态,不仅不动,倒向白萍招手。白萍转脸向畏先道:“她不走,就让她在房里独自呆着,我到你的门房去。”说着就直向外走出,畏先在后跟着,把个吴翠瑛丢在房里,追也不好追,叫也不能叫,眼见得羊肉吃不着,倒惹一身骚。此际再想叫闹,诬赖白萍侮辱,无奈对方业已出了屋子,到了院中,机会业已失去。又怕无法回复梅有影等人,不觉便暂时呆在房里。
白萍向外走了几步,恰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借着屋里开门露出的灯光。看了看,竟是那个梅有影,后面还跟着周作方。那梅有影撞着白萍,愕然向后退了几步,瞧瞧白萍,又回头去看周作方,周作方也只看着梅有影发怔。白萍却向他俩点头道:“梅先生,周先生,到这时候还不睡,太用心了。你们是寻吴女士么?她正在这屋里等着你们。”说着向后面一指,便仍领着畏先向外走到门房之处,回头看时,见吴翠瑛已从屋内出来。到了梅周二人一处。三个唧唧咕咕,不知说些什么,好似翠瑛受了他俩的埋怨,却又不甘,便哓哓分辩,却听不真切。又见梅有影猛然把脚一顿,高声道:“完了,全完了!咱们认失败吧。明天各自讨饭去。”说完便左手拉着小周,右手拽了小吴,直奔后院走了。
白萍方喘了一口气,向畏先道:“我要得谢谢你。若不是你来,我真很危险。这群人卑鄙阴险,居然到这步田地。这种心思,若用在拍摄影片上面,恐怕很有办法,可惜都用在邪路上了。”这时畏先仍然百变不离其宗,还是就题发挥道:“您就是我的饭东,我不对您尽忠对谁尽忠呢?所以我一听见他们的阴谋,连解手也顾不及了,就跑去向您报告,给您护卫。”说着“嗳呦”了一声,立刻解开下衣,“哗哗”地小便起来,一面说道:“这会儿一提起就憋不住了,林先生您别怪我没规矩。”白萍见他这样,倒觉好笑,便道:“果然亏你一片热心,我总要报答你。明天和昭和说说,给你个好一点位置。”畏先没等白萍把话说完,霍地转回身来,向白萍深深鞠了个大躬,说道:“谢谢林先生。”
哪知他小便正解到中间,只因喜心翻倒,忘了礼节,加以转身太忙,那下部的一股水箭直扫射到白萍身上,再加他鞠躬时身体一低一扬,便更像溅珠喷玉般,另外又浇上了许多水点。白萍忙躲不迭,畏先在黑影中却看不见,只当白萍谦逊,不敢当自己的鞠躬大礼,所以躲避。当时白萍道:“现在他们既都走了,料想不致再有岔头发生,我还是回到那房间去。不过你要把铺盖搬去陪伴着我。”畏先连忙答应,便进门房去把破絮被褥,抱作一团,随白萍回到原住房中,打了个地铺。白萍把门关好,便不敢睡觉,仍自一面草拟章程,一面和畏先说着闲话。直到天明,平安度过。
天到八点多钟,外面又有人敲门。畏先开了门看时,原来是梅有影。梅有影规矩正板地向白萍通知,说是卑男女演员们,都收拾停妥。刻下便迁移出门,特来告辞,并请监视。白萍只得客气两句,便出房立在院中。一见演员约二三十个,每人携筐抱箧,也有的抗着行李,好似一群灾民,鱼贯向外而行。女演员约有三四个,都是愁眉泪眼,看样子似乎出去便都无以为生。惟有吴翠瑛神色如常,走着还不老实,向白萍扭嘴弄眼做出许多表情。白萍更不敢再看。
等到众人完全走尽,梅有影的行李也被两个洋车夫扛出来。梅有影向白萍点点头儿,说了声“再见”,也走出去了。白萍倒送了几步,这才回来同畏先到后院去看。只见各寝室里桌翻床倒,尘土飞扬。最妙的满墙都画着春宫,污秽得不堪入目。又到了玻璃棚外,见玻璃差不多都已破烂,竟不知是什么时候打碎的,势必要重新建造了。再寻到器具室中,摄影机两架居然完好,但是其余物件,只就白萍所想到的已缺乏很多。又见这许多演员走后,除了自己便剩了畏先一人,不禁诧异这样大的公司,怎会连仆役都没得一个?将此意询问畏先,畏先道:“仆役当日原很多的,只因孔大爷不添股本,公司经费窘涩,便都由梅有影辞退。一切仆役职务,除了我一个赶忙,下等演员们也都帮着办。我们上回在西山拍片子,您是看见的,我这仆役能兼当演员,就可知演员们也可兼充仆役了。”白萍笑道:“想不到这般人居然有平等精神,泯除阶级制度。”畏先“呸”了一声道:“什么平等精神,穷挤得罢了。”
二人说着,又回到前院。畏先服侍着白萍洗了脸,又买了点心。正午以前,孔昭和派来汽车,接白萍到孔宅吃午饭。另外又派了个仆人来看守房屋。白萍便坐车到了孔宅,见了昭和,报告了梅有影等移出的事,又把自己草拟的计划说了。昭和甚为赞许,一切都请白萍便宜施行,又要把一个两万元的银行存摺,交给白萍,作为筹办之费。白萍坚意不肯管理财政,竭力推辞。昭和只得把自己宅里一个账房先生姓杨的派作公司会计,保管财政,言明白萍随时可以支配。
白萍在孔宅吃完午饭,又谈了些改组办法,便辞出来。因为公司急于开办,聘请人才不能稍迟,便给上海各朋友处打去了电报。再到各报馆去登了广告,却把公司改了名字,登的是:古城电影公司招聘演员职员,不拘性别,愿应聘者于一日内到狗尾巴胡同报名,一月后面试。广告登毕,再到印字馆里印了些信笺簿册,才回公司去休息。
到了次日,报端广告登出,便已有人来报名,或是询问章程。白萍忙收拾一间房屋,做为办公处。因畏先认识些字,就派他作个书记,办理报名登记,和应付来询问的人,一面商得昭和同意,雇工匠修饰这破旧房舍和建盏玻璃棚。这玻璃棚怎样盖法,不仅匠人不知,便是白萍也不大清楚。幸而后院的旧玻璃棚虽然破碎,却喜结构未伤。有精巧的匠人,便可循着旧观着手筑得大致不差。
这一草刨,便已费了十几天工夫。上海的回电早已来了,白萍的朋友高景韩在上海万华影片公司做着摄影主任,粱伯亨在上海鸳鸯公司做布景主任。这两人接得白萍聘电,都表示愿来北平帮忙。白萍甚喜,便又去了回电,请他们急速快来,并请每人带两个助手。其余的需要人才,也请代聘几人。电报打去,又分别给他们汇去钱款,这才算大致初定,只等他们到来和考取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