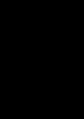七月的天气是有些热了,健志在家里穿着短裤,光着背,日子过得有些无聊,常常院子里的鸡,还有周围人家的鸡莫名其妙地啼叫起来,狗见了陌生人,“汪汪”地叫,惹得很多狗跟着凑热闹,结果是,狗吠声此起彼伏,孩子们的哭声、叫喊声、笑声,也传进院子来,搅得人心烦。还有麻雀,站在晾晒衣服的绳子上,扇动翅膀,叽叽喳喳的叫个没完。
“快乐是属于他们的,而我什么都没有……”,健志冥思苦想着,想努力写下几个句子,“我是开在路边的一棵小草,以孤零零的姿态迎风而立,我的生命本不平凡,经历过春夏秋冬……”
院子中的小花园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幼儿园里,老师教过一首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儿真鲜艳……”,那时,他只知道歌很好听,却怎么也不理解它的含义。
看着满园的花花草草,他又些陶醉了。其实,花园不过是自己用树枝围起来的一片地方,比不上有钱人家的水泥瓷砖的气派,却有自己的风格。
“《小花园》”他写下一个题目。
我住在奶奶的院子里,院子很大,在靠墙的地方,我用树枝做的篱笆墙,花儿大都是向别人要来的。
春天一到,在我的小花园里便能见到芍药花绽放了。在冬天的时候,叶子与茎全都枯萎了,只有根深深地埋在地下,而到了春天便从泥土里冒出芽,之后不长时间,便长成很大的一簇,花儿开在一大簇枝叶的上头,深红色的,颇象牡丹。芍药倒真像一位端庄的淑女,没有半点矫揉造作和娇弱的样子,大大方方,对冬天不卑不亢,对春天又那么向往。
与芍药相比,美人蕉倒是一位形容高贵,又不耐霜寒的“林妹妹”,她高高的枝干,到有点像家乡的玉米秆,花儿黄里透着红,枝干总是长在一起,高高低低不等,每一棵上都开着一朵或几朵花。含苞欲放的犹如嫩嫩的玉米棒,金黄的。已开的如贵妇人鹅黄的脸蛋上挂起几朵红云。冬天一到,我们只能把她的根茎挖到屋内,否则,很容易冻坏的。
月季要算是“辣妹子”了。月季的花是浅红色的,给人以淡雅、清新的感觉。但没人敢去碰她,她是高雅的女子,却又是得理不饶人的那种,浑身都长满了刺。
菊花是到深秋才开放对的,花是淡黄色的,细细的花瓣儿,从里到外密密地排列着,瓣尖弯弯的,倒像是温柔漂亮的女孩子额前的刘海儿。到天气变凉的时候才开的花儿,的确给人异样的感觉。就像人愈在困难的时候,越顽强地奋斗,微笑着。
记得我读二年级时,已到深秋,天气着实有些冷,学校里,有上级来检查,学校便要求学生拿几盆花儿来作点缀,我第一个举起小手。其实,我家只有一盆花,那是爷爷从人家的山楂地里偶然拣到的。她只有一枝瘦弱的枝干,上头挑着一朵白色的小花儿,开的正旺,我小心翼翼地捧着花到学校时,手已经冻得冰冷。我看到别人的花都是一大簇的一盆,花朵很多,我感觉我的花儿就像一个穿着单薄的小姑娘,比不了那些妖娆的贵妇人。老师微笑着,把她挤在那些“贵妇人”一起,然后说:“现在不是很漂亮吗?”有时我就想,我那时真好笑,但又一想,我的菊花是一个质朴、端庄的小姑娘,瘦弱的身躯里透着纯洁和善良,不是吗?
小花园里长势最凶的要数晚来香了,当初只是随便把他种在墙根,而后每年春天,她都从石逢里翘首相望,长的满园都是,往往我不得不砍去许多。在夏季,她的花开得最旺盛,一朵朵粉红色的小花儿,挂满枝头,犹如无数个“小喇叭”朝天而咏。应该说夜来香是个野姑娘,不要半点人间的关怀,也是生命力最顽强的。
那一棵石榴原本不是种在园里的,后来是因为在别处有妨碍,才被移种于此的。小红花开得时候,总是挂满一树,与细薄的叶子相称,便如一个小巧玲珑的江南女子了,样子活泼可爱的。
后来,有一年的春节前夕,我向一个同学要了一根牡丹的枝条,听同学说,要把她放在湿润的沙子里培育着,年后再种,后来竟把这事忘了。我想,一是大概是这花太娇惯了,那楼上的“千金小姐”又怎能“下嫁”到这“荒蛮”之地呢?二是,我对花太没细心了,想想看,一个在热恋中的小伙子,没细心,怎生了得!
我是很幸运的,一个不懂得养花而喜欢花的人能够尽享这满园的春色,品评数种,颜色、品格、气质各不相同的花儿,不能不说是一件愉快的事。
然而,在冬天,我只能是无可奈何了。小花园里没有傲骨的梅花,我又绝非是能耐“霜寒”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伤心的事情。
我读初三的时候,爷爷去世,之后不久,春节过后,精神分裂严重的叔叔突然失踪,我没有迎寒而开的蜡梅那样的筋骨,也缺少深秋里毅然绽放的秋菊那般的心性,所以我便感到秋是悲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