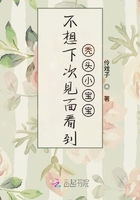韩献肃公守成都时,蔡君谟与之书曰:“襄启:岁行甫新,鲁钝之资日益衰老。虽勉就职务,其于精力不堪劳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闻年来补治有方,当愈强健,果如何哉?襄于京居,尚留少时,伫君还轸,伸眉一笑,倾怀之极。今因樊都官西行,奉书问动靖,不一一。襄上子华端明阁下。”此帖语简而情厚,初无寒温之问,寝食之祝,讲德之佞也。今风俗日以媮薄,士大夫之獧浮者,于尺牍之间,益出新巧,习贯自然,虽有先达笃实之贤,亦不敢自拔以速嘲骂。每诒书多至十数纸,必系衔,相与之际,悉忘其真,言语不情,诚意扫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僣紊官称,无复差等,观此其少愧乎!忆二纪之前,予在馆中,见曾监吉甫与人书,独不作札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约云:“曾公前辈可尊,是宜曰丈,余人自今各以字行,其过误者罚一直。”行之几月,从官郎省,欣然皆欲一变,而有欲败此议者,载酒饮同舍,乞仍旧。于是从约皆解,遂不可复革,可为一叹。
【译文】
韩绛(字子华,溢献肃)作成都知府时,蔡襄(字君谟)向他写过一封信,信上说:“襄启:光阴荏苒,又是一年,我生来就天资愚鲁,加之一天比一天衰老,尽管还能勉强从事本职工作,但是由于精力不济,有种难以忍受的劳苦。想起您的出生,和我相差十天,听说您近年来多方保养身体,或进补,或治疗,现在您定当更加强壮健康,不知真正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住在京城,还要停留一个时期,等着您受诏还京,那时彼此相见,将开怀大笑,高兴之极。而今趁着樊都官要到西边去,顺便奉上一信问候起居,其他的事不再一一禀告。蔡襄奉上子华端明殿学士阁下。”这张柬贴,语言简短,情意深厚,全然没有那些问候寒暖、祝福寝食、恭惟道德的客套话。现今的风气一天天地轻薄,虚浮的士大夫,在书信中弄出越来越多的新巧花样,且习惯成自然,弄得即使是通达务实的贤人,也不敢超越于流俗,而招来嘲笑谩骂。每次写信就多达十几张,信中一定写清楚官衔,在这相互交流思想的场合,全都忘了写信的真正目的,说出的话一点也不实在,真诚弃之无余。相互称呼不称字,都称某某丈,超越礼制,使官称错乱失序,不再有等级的差别,这些轻浮之辈看到这封信大概也会多少感到羞愧!回忆起二十四年之前,我在馆阁任职,看到秘书少监曾监(字吉甫)给人写信,硬是不用奏事文书的公文形式,并且对其同事称字,同事们因而相互约定,说:“曾公是前辈,宜加尊敬,称呼他应称之为丈,其他的人从今以后都以字相称,那些搞错了的罚他值班一次。”这个方法施行了将近一个月,郎署及台省的从属官员,都高高兴兴地想着一改旧习。可是,也有想取消前约的人,备酒请朋友的客,请求仍照先前的称呼。于是一起达成的协议被破坏了,从而再也无法改变,多么让人惋惜啊!
孔氏野史
【原文】
世传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书于清江刘靖之所,载赵清献为青城宰,挈散乐妓以归,为邑尉追还,大恸且怒,又因与妻忿争,由此惑志。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马温公为通判,夫人生日,温公献小词,为都漕唐子方峻责。欧阳永叔、谢希深、田元均、尹师鲁在河南,携官妓游龙门,半月不返,留守钱思公作简招之,亦不答。范文正与京东人石曼卿、刘潜之类相结以取名,服中上万言书,甚非言不文之义。苏子瞻被命作《储祥宫记》,大貂陈衍幹当宫事,得旨置酒与苏高会,苏阴使人发,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堕计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它如潞公、范忠宣、吕汲公、吴冲卿、傅献简诸公,皆不免讥议。予谓决非毅甫所作,盖魏泰《碧云狖》之流耳。温公自用庞颍公辟,不与潞公、子方同时,其谬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孙,佳士也,而跋是书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闻其言久矣,故录而藏之。”汪圣锡亦书其后,但记上官彦衡一事,岂弗深考云。
【译文】
社会上流传孔毅甫《野史》一卷,共记四十件事,我从清江县的刘靖之那儿得到了这部书。其中记载赵清献任青城县令的时候,曾带一名民间的女艺人回家,被县尉追上,夺还给人家,因而大哭大闹,又因迁怒和妻子闹矛盾,因此迷失了自己志向抱负。文潞公(文彦博,封潞国公)作太原太守时,任用司马温公(司马光,赠温国公)为通判,文彦博的夫人生日时,温公曾进献小词祝寿,受到都漕唐子方的严厉斥责。欧阳永叔(欧阳修,字永叔)、谢希深(谢绛,字希深)、田元均(田况,字元均),尹师鲁(尹沫,字师鲁)诸人在河南府治所洛阳时,曾经携同官妓游览龙门,半个月还不回来,河南留守官员钱思公写信要他们回来,也不理睬。范仲淹(溢文正)和京东人石曼卿(石延年,字曼卿),刘潜之流互相结交以博取浮名,服丧期间上万言书,很不符合服丧期间上书出言不要文采的规范。苏轼(字子瞻)受命创作《储祥宫记》,大太监陈衍管理宫廷事务,得到皇上的旨意置办酒席同苏子瞻畅饮,苏暗地叫人告发此事,以为不符合礼制,于是御史董敦逸就上了弹劾的奏章,刚好落入陈衍设计好的圈套。还说苏辙用骄文写的表章不成体统。别的如文潞公、范忠宣纯仁、吕汲公大防、吴冲卿充、傅献简尧俞诸人,也都不免受其连累。我认为这决不是孔毅甫所写的,大抵属于魏泰的《碧云狖》之类的东西。温公自己因为庞颖公的举荐而被征辟入朝,跟文潞公,唐子方并不同时,其荒谬自不言自明。刘靖之是刘原甫的曾孙,是品学兼优的读书人,可是为这部书所写的跋语却说:“孔氏兄弟和我的曾祖父同辈,怀念他们的为人就想听到言论,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所以把它抄录加以保存。”汪圣锡也在书的后面写有跋语,只是记录了上官彦衡的一件事,难道他们没有仔细看过该书的内容吗?
有若
【原文】
《史记·有若传》云:“孔子没,弟子以若状似孔子,立以为师。他日,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何以知此?’有若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谓此两事殆近于星历卜祝之学,何足以为圣人,而谓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损,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称“子夏、子张、子游,以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汉秋阳不可尚”而已,未尝深诋也。《论语》记诸善言,以有子之言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载有子闻曾子“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两语,以为“非君子之言”,又以为“夫子有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则其为门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书,于是为失矣。且门人所传者道也,岂应以状貌之似而师之邪?世所图《七十二贤画像》,其画有若遂与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译文】
《史记·有若传》说:“孔子去世之后,师兄弟们因为有若的相貌长得像孔子,就拥立他作老师。其后有一天,弟子们去见有若并请教道:‘过去有一天咱们老师要出门,叫从行徒弟们拿着雨具,不久真的下了雨。徒弟们就问凭什么知道会下雨,老师说:《诗经》不是说了吗,处暑前后,月亮附着于毕宿,就会使得大雨谤沱。昨天晚上月亮不是逗留在毕宿的位置上了吗?又有一天,月亮逗留于毕宿,却居然没有下雨。商瞿年岁大了但是尚没有孩子,孔子说他四十岁以后会生五个男孩子,后来果真如此。冒昧地问一声老师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呢?’有若没有办法回答。师兄弟们就促使有若站起来,说:‘有兄离开老师的座位吧,这里不是您该坐的!”,我认为这两件事大抵接近于天文学和占卜学,明白这些哪里值得当圣人,难道孔子只传说这些吗?有若没能了解这些,对他又有什么损害,难道师兄弟们会因此就立刻斥退他吗?《孟子》中称:“子夏、子张、子游认为有若相貌像圣人,想用侍奉孔子的礼节侍奉他,曾子不同意”,也只是说“孔子的道德学问就像在长江、汉水之中洗涤过,没有杂质,就像在盛夏的太阳底下晒过,光明浩白,没有能够赶得上”,如是而已,也没有进行严厉的批评。《论语》是部记录孔门师徒美好的言论的书,把有子的一段话排在第一章的第二段,在曾子的前面,假若真有避坐的事,后学弟子们肯这样排列吗?《礼记·檀弓》记载有子听到曾子转述的“流亡他国之人还是快快穷下来的好,人死了还是快快腐烂了的好”两句话,认为“这不是有道德的人说的话”,又认为“这是老师有所指而发的义愤之辞”。子游了解老师说话的背景,慨叹道:“有子的意见是多么像老师啊!”有子被师兄弟们尊敬亦非一朝一夕之事。太史公的《史记》,在这件事情上的记述是错的。况且徒弟所传承的是老师的道德学问,哪能因为相貌像孔子就以他为师呢?世人所画《七十二贤画像》,他们画的有若像就跟孔子像大致相同,这是很可笑的。
张天觉为人
【原文】
张天觉为人贤否,士大夫或不详知。方大观、政和间,时名甚著,多以忠直许之。盖其作相适承蔡京之后,京弄国为奸,天下共疾,小变其政,便足以致誉,饥者易为食,故蒙贤者之名,靖康初政,遂与司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予以其实考之,彼直奸人之雄尔。
其外孙何麒作家传云:“为熙宁御史,则逐于熙宁;为元祐廷臣,则逐于元祐;为绍圣谏官,则逐于绍圣;为崇宁大臣,则逐于崇宁;为大观宰相,则逐于政和。”其迹是矣,而实不然。为御史时,以断狱失当,为密院所治,遂摭博州事以报之,三枢密皆乞去,故坐贬。为谏官时,首攻内侍陈衍以摇宣仁,至比之于吕、武。乞追夺司马公、吕申公赠谥,仆碑毁楼。论文潞公背负国恩,吕汲公动摇先烈。辩吕惠卿、蔡确无罪。后以交通颍昌富民盖渐故,又贬。元符末,除中书舍人,谢表历诋元祐诸贤,云:“当元祐之八九年,擢党人之二十辈。”及在相位,乃以与郭天信交结而去耳。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誉,则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门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词,天觉所作,是以得执政云。
【译文】
张天觉为人如何,士大夫们中有些人并不详细了解。他在大观、政和年间名望非常之高,多人称赞他忠直。因为他作宰相刚好在蔡京之后,蔡京操纵国政干尽坏事,天下之人都痛恨,只要稍微变更他的施政措施,就足以获取名誉,就像饥饿的人不择饮食,所以得到了贤者的名声,靖康初年政治局面稍变,从而和司马光、范文正一起受到朝廷的褒扬封典。我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来考察他,他只不过是个奸险小人之特殊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