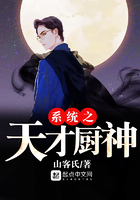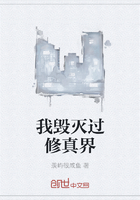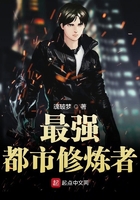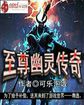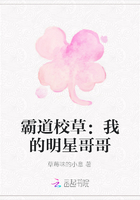郭向东的车停在了韩江家门口。
韩江从院里出来,夹着皮包,手里还提着个小型录音机。
郭向东问:“录音机带没帯?”
韩江说:“看你这眼睛,没见我手里提着吗?”
郭向东说:“我怕你忘了。”
韩江说:“这是我必备的家什,忘不了。”
上了车,韩江问:“那老东西怎么样?”
郭向东说:“又搭了一个桥儿。他已经搭过一次桥儿,反正现在心脏搭桥儿技术很成熟,也很普遍,再搭一次也无所谓。”
韩江问:“他的两个儿子呢?没来?”
郭向东说:“大儿子远在巴西,来不了;二儿子王安来了,派了两个人专门守护他爸。”
韩江撇了撇嘴:“够谱儿。”
车开了,韩江又有些失落地说:“其实,材料已经递上去了。”
郭向东说:“递上去就递上去了。但还是王通森主动交待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去录音。否则的话,因为时间太长,追诉人当时又只有四岁,最高检因此不予以核实批准,怎么办?”
韩江感叹一声:“我爸良心发现,看来那老东西也良心发现喽!”
郭向东说:“只希望他别有半点隐瞒,交待得越真实、越详细越好。”
车过村委会门口,程玉兰刚签收完一封信,见郭向东来了,便把那封信隔车玻璃递给了郭向东:“从澳大利亚来的,我估计……是那个王琼。”
郭向东接过信看了看,说:“还估计什么?不是写得很清楚?拼音字母,王、琼。”
程玉兰说:“那你就带给立秋吧。我看这事还真麻烦……”
郭向东要拆那信,韩江一把夺过来:“你怎能随便拆私人信件?说你懂法,你又不懂。”接着,他对着那信封,别有深意地说,“嗯,麻烦不小呵。”
郭向东笑了笑,继续开车。
出了村,隔窗向西望,可以看见打井的井架,也能听见窟咚窟咚井管下砸的声音,还有一个用竹竿简单搭起的牌楼,牌楼的两侧居然还悬挂着“争优质迎奥运”、“保进度建新村”的巨大红色条幅。郭向东说:“他们都是通森公司从山西分公司调过来的。进度不慢,已经下去十多米了。”
韩江问:“南庄的危旧房怎么样?老东西还管不管?”
郭向东说:“人家当然管,但咱们不想用,不能赖上人家。再说危旧房也不多,就那几户,村委会帮衬一下就可以。”
韩江又问:“小学校呢?”
“小学校人家也管。”郭向东说,“不过现在我倒考虑赶快给王通森盖上那几间房,你想,他出了院怎么办?总住在村委会?像什么话呢?再说他还要把他老伴从澳大利亚接回来。”
停了停,韩江又说:“他交待完了,如果他被判了死刑或是无期徒刑,那房子给谁住?”
郭向东笑了说:“你倒虑论得远。那就给他老伴住,让他老伴儿在咱们这儿念经拜佛。”
韩江也笑了说:“可是咱们这儿不兴拜耶稣呵。”
“那就光拜菩萨!”
郭向东说着,突然将车停下了。
韩江问:“干嘛?”
郭向东指指前面。
一位少妇肩上挎着个包,怀里抱着个孩子,站在路边正朝他们招手,好像把这车当成了出租车。
郭向东把头探出去:“这位女同志,有什么事吗?”
“请问大哥,去南庄怎么走?”那少妇问。
郭向东指给她:“简单,一直往北,再往西一拐就到了。”
“哦,谢谢您。”少妇移动脚步,往北走。
“也就五、六里地!”郭向东找补道。
韩江是南庄人,感到有些奇怪,便也探出头,朝北大声问:“你是出了门子的姑奶奶呀,还是媳妇回娘家呀?怎么连家都找不着了?”
少妇回头说:“我没来过,第一次来。”
“怪不得没见过你呢!”
郭向东要开车:“你这人,就不许人家是串亲访友的吗?”
韩江仍饶有兴趣地问:“你和南庄谁家是亲戚朋友呵?”
少妇重又站定:“我来找一个人,他叫朱立秋。”
郭向东楞了一下,韩江也愣了一下,然后郭向东又把车倒了回去,挨近那少妇。但不等他们说话,少妇又充满希望地一连串地问道:“请问大哥,你们是南庄人吗?要是的话,认不认识朱立秋?他现在怎么样?在家不在家?”
郭向东索性将车息了火,韩江也下车来,站到了少妇的面前。
韩江审视着少妇,郭向东则和颜悦色:“请问你怎么认识朱立秋?在哪儿认识的?能告诉我们吗?”
少妇说:“整整一年了,我们在三亚认识的……”一面说一面从衣服的兜里掏出一张折叠得规规矩矩的纸,打开,然后递到郭向东手里,让他们看。
他们看到那纸上写有两个地址,一个是立秋曾经提到的他的养父母家,一个则清清楚楚写着丰安市崇水县大王庄乡王家庄村南庄。
立秋除去在手术协议上以及在韩江的追诉申请书上签过字以外,韩江和郭向东还不曾见过立秋在别处写字,因此他们便不能肯定那就是立秋的字体。但纸条上的地址真真确确、无可置疑。
韩江觉得有必要问个清楚:“你和朱立秋究竞怎么认识的?结过婚吗?”
少妇摇头。
“你抱的孩子是谁的?立秋的?”
少妇摇头。
“这就怪了。”韩江说,“你们糊里糊涂认识,你糊里糊涂来找他,你们又没结婚,孩子也不是立秋的……那么你找他干嘛呢?”
少妇显出为难的样子,似乎千言万语,一时说不出。她只说:“求你了大哥,你们先帮我找到朱立秋,这以后的话以后再慢慢说,行不行?”
郭向东问:“你叫什么名字?”
“彭秀娥。”
韩江问:“你是哪的人?就是三亚人吗?我看不像,从说话上就不像。”
彭秀娥说:“我不是三亚人,往北,比你们还往北呢!”
韩江说:“有多北?内蒙?黑龙江?”
彭秀娥说:“承德那边一个县,说了你们也不知道,很小的一个县。”
郭向东说:“这么着吧,你现在跟我们走,去丰安市,到了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见到朱立秋了。”
彭秀娥惊诧起来,满脸狐疑地问:“去医院干什么?朱立秋到医院工作去了?还是他有病住院了?”
郭向东说:“所以我要告诉你,不管你和他是什儿么关系,你们是亲戚关系、朋友关系还是恋人关系,我告诉你朱立秋现在是个残疾人。他的左腿膝盖以下已经锯掉,养一段时间以后正准备安假肢。”
彭秀娥站在那儿不动了,脸立刻变了颜色。她怀里的孩子用小手抚弄着她,慢慢地,她淌下了眼泪。
“我料到了……做梦也料到了,”她喃喃地说,“怪不得他满身是血,我追他,可怎么也追不上,捡到他一件衣服,那衣服上也是血……还梦见他进了监狱,监狱里也有血……”
“他不会死!”韩江赌气说了一句,回到车里;郭向东也回到车里。韩江说:“我以为又是个麻烦,原来不是。”
郭向东说:“怕也不见得。我们原来认为王琼见了立秋那样子,她会放弃,会离开立秋,没想到……”
韩江说:“人和人不一样呵。”
郭向东又探出头去,劝道:“彭女士,回去吧,回承德老家近一些,如果在三亚有工作,就回三亚吧。”
韩江帯了些嘲讽的语气:“车钱够不够?不够给你点儿!”
“走、走,人家也怪可怜的。”郭向东重新发动了车。但车还没有起步,只听彭秀娥大喊:“等一等!”
郭向东踩着油门的脚只好又松开。他看着韩江:“我说不见得,你还不信。”
韩江说:“难道真又是个麻烦?”
郭向东重又下车,把后车门打开;桑塔娜旧了,老了,只有从外面才能打开后座上的车门。
韩江看着彭秀娥把小包袱先扔进来,然后抱着孩子钻进了汽车。
车开了,老桑塔娜发出了耕牛喘气一样的响声。韩江一眼一眼地回头看,郭向东从后视镜里看,彭秀娥低着头,奶着孩子;韩江和郭向东又不好意思看。
韩江问道:“孩子几岁了?”
彭秀娥回答:“一周零两个月。”
韩江扭身伸出双臂,要抱那孩子,彭秀娥便把孩子递过去。韩江抱在怀里,甚觉孩子可爱,小脸儿粉嘟哪,肉嘟嘟,刚会呀呀学语,也刚刚长牙。他惊呼:“还是个带把儿的哪!”
郭向东强调说:“彭女士,我可不是开玩笑,朱立秋真的做了大手术,真的截了肢。”
然而彭秀娥好像没听见,不到一分钟孩子就要找妈妈,彭秀娥拍了一下巴掌:“妈妈在这儿!”
车里的气氛变得温馨起来。
“我的天!”韩江说,“三亚离这儿几千公里,你一个人抱着个孩子,可怎么来的呢?”
彭秀娥说:“怎么来的,就那么来的呗……早晨起来,说走就走,只把主要的打个包,剩下的全不要了,先坐汽车,又坐火车,在火车上吃在火车上睡,也住过旅店,一共走了八天,下了火车,一路走一路打听,就到了这儿。”
韩江又问:“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找他?”
彭秀娥说:“做梦,就是因为做梦,梦见他满身是血,后来又梦见他进了监狱……那一宿也没再睡,所以第二天早晨我就跟孩子说,儿子,咱们找你爸去吧!”
郭向东说:“等等,等等,不是说这孩子跟朱立秋没关系?”
彭秀娥不答,只是笑,笑得格格的,然后又开始逗孩子。
韩江说:“但我还是要问,你为什么做那样的梦?很可怕的梦?”
彭秀娥静下来,沉沉地说:“……那天晚上,他说他要去讨一笔债,我问他什么债,那债有多大,他说,一个叫王通森的人谋害了他的父母,可那个人逍遥法外!结果,他到澳大利亚去了,从那以后我就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郭向东和韩江也都沉静下来。好啦,什么也不用再说,什么也不用再问了,一切都是真的,如板上钉钉一样地真。
车虽然老旧,但郭向东尽量把它开快。一百多里的路程大约用了一小时四十分钟,就到了。
他们下了车,彭秀娥抱孩子跟在后面。韩江手里提着录音机,郭向东替彭秀娥背着包。
立秋在病房里拄着拐,已经能下地活动了。
郭向东走到他面前:“立秋,可从来没听你说过,也没听别人说过……”
韩江当头一棒:“说!你先交待,老东西后交待,你搞了情人、恋人,还是泡了妞?”
郭向东说:“人家现在来了,找你来了。”
立秋问:“谁?谁找我?”
韩江放下录音机,接过孩子,把彭秀娥从后面推到了前面。
立秋一下楞住了。然而他也只楞了几秒钟,那刚刚上了些血色的脸便绽开了欣慰的笑容。这样的笑容,郭向东和韩江都第一次见到。
彭秀娥呢,满脸是泪,唏唏地哭,续而她扑过去,但中途停止,改为轻轻拉起立秋的手,扶立秋回到了床上。
立秋坐着不动,只呆呆望着彭秀娥。两人互相望着。
彭秀娥开始周身抚摸立秋,并喃喃自语:“是这样,是这样,我做梦梦见的,就是这样子的……”
孩儿找娘,郭向东从韩江手里接过孩子,替彭秀娥哄。但孩子不依,哭叫着非要找娘,并清清楚楚地叫出了一声“妈”;这一声“妈”,不知怎么,让郭向东和韩江都掉下了眼泪。
郭向东只好把孩子交到彭秀娥手里去,然后对韩江说:“咱走吧,这里没咱俩的事。”
韩江提起录音机:“对了,老东西还等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