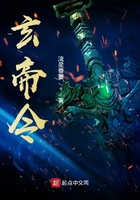晚秋,是黑土地万亩良田最佳的收获季节。风总在天空中飘来飘去,刮得人恍恍惚惚。山菊这两天不知不觉心里闹腾的慌,当东边早霞还在朦胧时,她却没有了一点睡意。山菊总是忍不住去想郭书记提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咋会有这么多困惑?她突然又想到家乡的大班长赵健,他高中应该去年就毕业了,是否考上大学?如果没有考上大学,他正在干什么呢?将近三年了一点他的消息也没有。山菊也曾想给他写封信问候,可又怕家乡同学及父老乡亲知道了,肯定会耻笑她。旧的封建思想和意识仍在家乡父老心中作怪。几次她手拿起笔和信纸又撂下了,两次给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写信问候过赵健,始终不见他的只言片语。想起那些年,在那种苦难的日子里,赵健对自己那份关怀,山菊的双眼止不住流出了几滴泪珠。
面对眼前的事情,山菊想,必须回场部一趟,和家人把这件事情说一说。师诚的家境和工作,有形无形中也触动了山菊内心的浮华。但她并不了解他的人品和秉性如何?这在山菊灵魂深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吃过早饭,山菊去鸡舍给刘阿姨请了一天假。搭上去团部送粮的方便车,心里忐忑不安的回到了家。大姐与姐夫还没有下班,母亲正在做针线活。看到山菊回来了,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忙放下手中的针线活,拉着山菊的手说:“你回来得正好,是休息吗?”
“没有,回来有点事情。”山菊和母亲说话也吞吐起来。
“哎!正好你回来。这两天你大姐和你姐夫为你的事情拌嘴呢。”
山菊非常纳闷地问:“我的什么事情?”山菊还没来得及给母亲说郭书记提亲的事呢,母亲却先唠叨上了。
“汽车队卫生所那个黄医生,黄阿姨看中你了。想让你跟她大儿子谈对象,说是她儿子在部队提干了。要是咱家愿意,她丈夫是医院的院长,能送你出去进修两年,进修结束,就可以把你留医院了。”
“啊!黄医生自己说的?”
“是啊!她前两天找你姐夫来,我出去时也遇着过她,当我面她也念叨过你。说她可稀罕你了。”听着母亲的唠叨,山菊脑子嗡嗡直响。天呀!这一阵子怎么了?咋都来提这个问题。山菊想,自己不知是该笑呢?还是该哭?究竟谁是自己胸口那一抹朱砂?她迷茫了。
男女之间的爱情,山菊没有品啜过啥滋味,又是怎样个美好!但她很欣赏很崇拜《第二次握手》里的苏冠兰与丁洁琼的那种崇高的爱情。这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吗?山菊觉得,自己的命运总是那么多凄凉。家境的卑微与内心的那种自卑感,始终缠绕着她。刚刚有了温饱的日子自己又能去祈求什么呢?埋头走好眼前的每一步是关键。可没有想到的是,眼前的事情还是有点让她迷茫。但又是多少女孩人生目标所追求的那份光鲜。怎不叫一个懵懂的少女纷乱了情怀呢?
“山菊,妈跟你说话呢,你发什么愣?”山菊一时间走了神,没有专注听母亲在一旁念叨。
“哦,那我大姐和姐夫咋说的?啥意见?”山菊问。
“你姐夫说可以考虑。你这就二十岁了,再去进修学习两年也差不多到年龄了。可你大姐心气高着呢,夸你是百里挑一的好人才,上门提亲的多得是,不着急。虽然家境穷点,咱也不图人家的彩礼,将来要为你挑选个,家室和人才都出众的小伙子才中意。”
“那最后她俩怎么决定的?”
“嗨!这不俩人争执吗,你大姐那厉害劲,还不是她说了算。”
“妈,那你啥意见?”山菊问母亲。
“我年纪大了,不懂个啥。还是你爸说得对,男娃憨厚、踏实、勤劳就好。”刘娣又念叨起了老伴的话。
山菊听着母亲这么一说,更不知该不该把师诚追求她的事情说给家人。如果不说,师诚再去找怎么办?传到大姐耳朵里岂不是更糟糕吗?山菊想想,还是跟母亲先说说吧。她望着年迈母亲手中缝补的旧衬裤,山菊的双眼湿润了。苦命的母亲,自从山菊记事起,就没有看见母亲穿过件囫囵衣服。想到这里,山菊很自责。
山菊坐在母亲身边。把郭书记给她介绍师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刘娣听后,摘下老花镜,用袖口沾了沾眼角说:“跟你大姐她们说说吧,看看她们咋说。妈老了也弄不明白了,可妈明白,俺丫头不愁找不到好人家。”
晌午到了。刘娣准备做一大家子人的午饭,白菜炖粉条。山菊也拿起水桶和扁担去水井挑水去了。到了十一点多,大姐姐夫也下班了。刘娣把做好的半锅白菜粉条端上了桌子。真是人多吃饭香,不到半个时辰,七八个大馍馍和白菜吃个一干二净。
山菊大姐邋遢个脸子说:“都死能吃,啥也剩不下。”听着大姐那冷冰冰的话语,山菊瞅着母亲,心里好酸楚。
下午还得返回连队。山菊皱着眉头,不得不把师诚的事情从头到尾又给家人说了一遍。只见山菊大姐那脸越来越阴沉,瞪个眼睛说:“我不是告诫过你吗,现在不许找对象。要找咱也得找个各方面条件优越的,你说的这家我们知道。但小伙子不太了解,哼,算个啥。”大姐一说话就带股傲慢与冲劲,盛气凛人的样子。
姐夫很温和地说:“啥事先了解一下看看嘛。”
山菊再也没敢多言。刘娣转过脸小声说:“听你大姐的吧,要不会惹多少气,等等再说吧。”
午后,山菊坐车返回了连队。一路上她也想好了,郭书记要是不提,自己就当没有这回事情,要是再问,就说还小,家里不赞成。师诚也不至于再来纠缠吧,自己端正做人就是了。
转眼一月过去,时光进入了十二月。风沙从天边刮来,从山林间穿过,像一股股皮鞭抽打的人脸火辣辣的疼。鸡舍几百只小鸡萎缩成一堆一堆的唧唧乱叫。野外几乎看不到闲人转悠,人们围坐在火炉旁,炕头上。翘个脚丫,嗑着瓜子暖和着身子,聊个闲话。打发着冬日里枯燥的时光。
最近连队职工都在纷纷议论,新的一年,国营农场农业生产责任制要有所调整。以大农业为基础,建立各种形式的农业大组。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效率,鸡舍和猪舍要砍掉百分之五十的鸡和猪,分流人员参加农业第一线。
望望这身后的大山,看看这望不到边的黑土地,山菊又焦虑起来。脑子也昏昏沉沉的。人生咋这么多十字路口,眼前自己是没有了一点其它选择,只有再拿起镰刀,锄头,撅个屁股弓个腰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了。如果把自己的前程放在以婚姻为跳板上,那就很有可能使自己的命运有一个大改变。这段日子山菊的内心又在不断地挣扎着。
“山菊门口有人找你。”正在走廊里装鸡蛋的刘阿姨在喊她。
山菊放下饲料盆,抖搂抖搂裤子上的灰尘,走出了鸡舍。当她来到走廊一看,山菊惊呆了。这个师诚咋又来了?山菊羞红了脸,转身要回鸡舍干活。
师诚紧赶两步说:“嗨!山菊,我大老远跑来找你,你咋能这样呀?”
一旁的刘阿姨也说:“山菊,人家大冬天的既然来了,你看看你这姑娘咋也叫人家小伙子进屋暖和暖和吧。你这么倔干啥?”
山菊这才稳着情绪,定情又看了两眼面前的师诚。一米七四五个头,长得一般个人。
“那你进休息间暖和一会吧。”山菊冷冰冰地说。
师诚笑嘻嘻地跟着山菊到了休息间。真到了休息间,两个年轻人都沉默了。山菊站在火炉子旁,手拿炉钩子一个劲地捣鼓炉灶,弄得火星子直往上窜。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山菊心里紧张极了!师诚倒不失时机的总想看一眼山菊。突然他先说话了:“山菊,咱俩的事情你回家说了没有?咋也不回个话?郭书记咋说也是你们领导,人家还总粘着你问,你也不给留点面子。我还挨我父亲一顿数落,这么多给我提亲的,可自从见了你一面后,我就喜欢上你了。别在这山沟里呆着了,我父亲会给你在场部安排个好工作,今后也能帮着你家里。”师诚在喋喋不休地,像着了魔一样表白着。山菊听他有意无意话语中,那种炫耀的劲头。心中觉得有种感动?有种厌恶?总之五味俱全。最后山菊鼓足勇气说:“谢谢你来看我,我还小,家里不赞成。”
师诚看看山菊那脸色,那生硬的态度无奈地离开了。临走他撂下一句话:“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我是真喜欢你,现在是婚姻自由。”事情当时也就此一段了。
1980年即将来临。连队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把来年的生产目标和计划大概作了安排。精简了后勤的畜牧业数量,鸡舍就留下百十只鸡了,就刘姨一个老饲养员留在了鸡场。山菊又要回到了农业第一线,她的心一下子又跌到低谷,失落透了。
元旦休息几天,山菊回到了大姐家。整个人没有了年青人那种朝气,垂头丧气的样子,多一句话也不想说。她也没有和家人再提起师诚又去找她的事情。大姐与姐夫知道了她从鸡场撤下的事情,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无奈地说了一句:“慢慢干吧,有机会再说。”
到了夜晚,山菊把这一年来省吃俭用下来的钱给母亲说了。二哥已经找了个女朋友,是东北人,人手很巧。等着夏季单位分配下来房子就准备结婚。除了他自己这两年积攒了几百块钱以外,家里是一无所有。山菊和母亲商量之后,准备给二哥买块手表,眼下也很时兴。他是男孩免得让人瞧不起。吃过早饭,山菊拿上这一百多块钱来到了百货商店。她在柜台前,先看了一下女士精美的手表,虽然自己好喜欢,暂时也只能算了。最后她花了八十块钱,给二哥买了块男士海鸥牌手表。又化了六十块钱,给姐夫买了一件蓝色呢子中山装。山菊再看看兜里剩下这十几块钱,常常地叹了一口气。现实的生活无法让她逃避,自己身上总像背着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内心的那份苦闷又能向谁倾诉呢?不能,说了母亲只能多份担心,多几汪眼泪。大姐说不好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与责备。但自己心里实在是郁闷啊!她准备写信与家乡最要好的女同学说说,看看她们啥观点,这样自己心里就会好受点。对,对,几次同学们来信要照片,自己也没照过一张像样的,所以几年来,她也没邮过照片给同学。现在戴上这只新手表,穿着这件毛领棉袄,自己也不算寒酸了。照个全身照片邮回去,让同学们看看自己长高了,还戴上了手表。一种小小的虚荣心涌上了山菊的心头。想到这里,山菊把这块男士手表先戴在了自己手臂上,左右看了几眼,美滋滋地朝照相馆走去。她刚想推开照相馆的大门,突然意识到师诚在这里上班,要是遇见了他,岂不是太尴尬?可大街上就这一个照相馆,不能就因为他在这里上班,自己永远就不照相了?这是不可能事情。再说了照相馆是农场的,肯定不会是他一个人在这里上班。山菊鼓足勇气推开了照相馆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