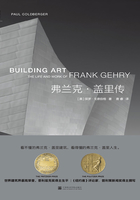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突如其来的倒春寒袭击了京畿重镇河内郡。
河内郡地处黄河冲积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历来就是户口殷实、农业发达的天下名郡。洛阳、长安两京钱粮用度皆出河内,被朝廷视为“股肱之地”。
然而,自从十年前黄巾乱起,诸侯为政,导致天下崩离,别说百姓饿死者以千万计,就连京城里的高官世宦,有的也是举家食粥,苦不堪言。年初以来,征西将军马腾与车骑将军李傕等人混战于长安城,煌煌大都,瓦碎屋倒,富人食树皮,穷家人相食,仿若人间地狱。
战乱频仍,太平这档子事就像月宫里的嫦娥,遥不可及,但即便身处乱世,人们依然停不了劳作奔忙。农夫们眼看着春种的各类作物焕出勃勃的生机,不承想老天毫不顾及人间疾苦,几场春雪过后,农作物大片死苗,都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而看眼下这光景,今年怕会是一个灾荒年。
半个多月前,马腾被李傕等人赶出长安。而各方势力经过拼耗,实力皆有所受损,难以再有图谋,长安获得了短暂的安宁,天子刘协下旨放太仓米赈济城中饥民,并传令各州郡开放官仓,以救百姓于倒悬。
皇帝的敕令传到河内郡温县时,已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这短短的一个多月,以温泉闻名的温县发生了一桩怪事。
原来,黄巾残流侵扰温县,县令率领全县军民奋力抵抗,不幸身中箭矢而亡。朝廷既无褒扬之词、抚恤之资,也不见新官接任,而堂堂万户大县,怎可一日无主?等待无果,经本地贤者长老推选,县衙日常事务暂由县内头号望族司马氏家主司马防主持。
司马氏世代为官,司马防又正处盛年,先前也曾担任过洛阳令、京兆尹这样的高官,管理一个县绰绰有余。只是这司马防自董卓入朝乱政以来,四处流离,等到董卓身死,局势稍见稳定,便以骑都尉的身份早早致仕归乡。功名利禄已成浮云,况且经过前些年的折腾,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现在对他来说,人生的乐趣,不过是读读《汉书》,陪陪家人。
县里只要没什么大事,司马防基本不出家门,只是教几个儿子读读圣人经典,好让他们早点有出息,早日光耀司马氏的门楣。司马防可以不为自己考虑,但必须为司马家族的未来摩厉以须,百年世家不能断送在自己手里。当然,一己之才毕竟有限,眼下最紧要的事,就是为几个儿子延请名师,尤其是次子司马懿,老大不小,再过几年就到可以出仕的年纪了。为了这事,他专门请来在此地游学的清河名士崔琰。
两人一见面,司马防开门见山,延聘崔琰做司马懿的老师。一边说着,一边让家仆将司马懿叫来。崔琰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然道:
“司马公耳聪目明,这次怎么走了眼?”
“崔先生何以说出这样的话?”司马防以为自己的诚心不够,急忙说道,“老朽虽然愚钝,但一片赤诚之心,丝毫不敢作伪。先生与犬子司马朗交情甚厚,对老朽家的情况想必是清楚的。老朽今天是真心诚意想请先生教教我的这个二小子,他年已十六,还只是读了些经史之书,因而想请先生帮他再提高提高。”
说话间,家仆已领着司马懿来到了门口。只见司马懿垂手立于一旁,待司马防向他招手,才将双脚踏进房间,恭恭敬敬地向崔琰行完礼,一动不动地立在司马防身边。
崔琰漫不经心似的看了一眼司马懿,微微一笑,“以前见伯达(司马朗表字),我已惊为巨人,没想到这位司马小弟的身材比起其兄来,更显壮硕高大。司马家真是尽出奇人。”崔琰乐呵呵一笑,整整衣冠,不紧不慢道,“司马公的心意,晚辈是理解的。我方才之所以说司马公走了眼,是因为司马公所请非人,以我对司马小弟的了解,我是教不了他什么的。”
说完,崔琰觑了眼司马懿。
司马懿仿佛一座雕塑般纹丝不动,立足之地离司马防既不远也不近。当崔琰看他时,他也回礼性地看看崔琰,此外,司马懿不插嘴,不走神,不晃悠,没有任何动静,就像他并没有出现在这里一样。
“先生此前从没见过犬子,这‘了解’从何说起?”
“了解一个人其实并不难,听人言,用眼看,即可知大概。”崔琰回道,“去年秋天我在伯达那里住了几日,他跟我详聊过有关司马小弟的事,比如‘桃子事件’。那时候你几岁来着?”
崔琰炯炯有神的目光投向司马懿。司马懿拱拱手,答道:“六、七岁间。”
司马懿的声音跟他的皮肤一样,粗糙,毫无美感,仿佛是从深不见底的山洞中发出来的一般。
如果不是崔琰说起“桃子事件”,司马懿或许早就忘了在自己的童年还曾有过这种事。
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司马懿和家中几个幼弟跟着哥哥司马朗在离家乡不远的黎阳避难。此时的温县正被黄巾军占据,有家难回。
一日,司马懿和司马朗还有两个弟弟路过一株桃树,树下落着十几个桃子,两个弟弟急忙跑去捡桃吃,司马朗觉得有趣,也跟着过去。这时,只听司马懿阴着一张脸说道:
“小心酸掉牙!”
两个弟弟不信,结果只咬上一口就吐了出来,口中直喊“酸死了,酸死了”,司马通还狠狠地踹了桃树几脚。
事后司马懿解释:“如果味道甜美,那桃子早就被人抢光了,还轮得着咱们兄弟吗?看你们急的,竟不信我的话,现在吃到苦头了吧。”
“伯达对此事想是印象深刻,时隔多年还对我谈起,并说日后司马家怕要全靠这个弟弟发扬光大了。我则说靠伯达的确不行,伯达比起司马小弟来差得太远。”崔琰沉吟片刻,又道,“人的天性是少年狂、老来顺,这合乎阴阳之道,而少年持重之事是不常有的。如若有了,便是与众不同,定有绝世之才、异人之貌,匡扶济事、毁邦灭国皆在一念之间。”
“先生的意思是,这样的人,既可大善也可大恶?”
崔琰严肃地点点头。
“我与司马公聊了快半个多时辰,按常理,司马小弟应该是双脚酸疼、力不能支了,但司马小弟此时仍然两腿笔直,神色自若,这一份坚持的心性,难能可贵。能藏者能放,说司马小弟少年持重,是没有错的。不过——”
崔琰又把视线投向司马懿,四目相对之际,心里咯噔了一下。
“我有一句话送给司马小弟:可以少年持重,但不可老夫聊发,而要老年持平。持平,即与他人和顺交融,使自己放下欲望,自得其乐而不为外界所惑,如此,方有人生意趣。既然我与伯达是朋友,那我再跟司马小弟交个朋友好了。”
“不敢不敢,先生是当今名士,而犬子不过一介顽劣,有辱先生名誉。”
“司马公不必客气,我与司马家也算是有缘。虽然我做不了司马小弟的业师,但有一人,我估计,于司马小弟的人生精进大有教导之益。”
司马防眼睛一亮,正高兴之际,却听崔琰说道:
“那人是隐士高才,住在洛阳城南的陆浑山上,轻易不见人。司马小弟与那人是否有缘,可就看造化了。”
“敢问那位先生姓甚名谁?”司马懿缓缓开口,声音中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姓胡名昭,字孔明。”
“原来是他,我听过他的不少故事。”这回司马懿的声音有了起伏,脸上也泛起了某种光泽。
不知不觉已到黄昏时分,司马防欲招待崔琰用饭,但崔琰告知身上还有些事,就此告辞离去。
出了司马府,崔琰冷不丁打了个喷嚏,大概是刚从炉火旺盛的房间出来,一下子置身于白皑皑、冷飕飕的雪境之中所致。下了几天的雪终是停了,可是下雪不冷,化雪冻手,何况是这样一个乱世灾荒的年月,在崔琰打喷嚏的这么点工夫,已经有几个衣服单薄的老者倒毙在地上。
放在往常,崔琰一定会掏钱请人安葬这些不幸的人,但此刻,他脑海中浮现的是司马懿那双专注中带着一丝鹰戾之色的眼神。那是狼的眼神,崔琰有些不安。
司马氏同郡人杨俊,评人论事眼光独到,与司马氏常有交往,和崔琰也是多年的老友。他曾对崔琰说:“司马懿非常之人,有狼顾之相,前途不可测。”
崔琰此时心中暗想,今朝一见,果不其然,希望司马懿能听懂我的一番劝言,只做忠良,不为篡逆。崔琰有点后悔把亦师亦友的胡昭抬出来,不知道这是好是坏。崔琰长叹一口气,翻身上马向北边走去。
“父亲,那个崔琰,巧言令色,徒有其名,还一口一个‘司马小弟’,像是与我有多亲近似的,真是好笑之极。”崔琰走后,司马懿向父亲司马防发起了牢骚。
“无礼!”司马防厉声叱道,“崔季珪乃清河崔氏名秀,又是经学大师郑玄高徒,可他偏偏不愿做你的师父,看来你没这份运气。”
“父亲不必遗憾,崔琰临走前提及的孔明先生,想必更适合儿子。不说其他,单论其一拒董卓强揽,二拒袁绍征召,坚守信念,义不能屈,就够儿学一辈子的。其实儿早先就想拜访拜访孔明先生,只是那时尚小,父亲又仕宦烦劳,就没跟父亲提起。”
“为父在洛阳时,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谈吐、气质颇不同于一般人,冉冉有神仙之风。你既有了打算,就收拾收拾择日起程吧,家中有你几个弟弟在,无须挂怀。只是你母亲多病,记得多来信为是。”
通常人家有人远行,必是设席相送,或叮嘱、或不舍,多有倚门落泪、抱头痛哭的场景,仿佛这一去便终生不复相见,司马懿却是不然,从小随着父亲四处奔波,大概早已习惯了聚散离合。
从温县到陆浑山,走官道,由五社津渡黄河,五日便到,但战乱之中官道早已废弃,如果走山路,则会面对许多险难。占山为王的贼寇、三五成群的黄巾残余不必多言,就是那看上去装潢考究、服务周到、环境敞亮的客栈,保不准哪家就是磨刀霍霍的黑店。
幸好一路上并未遭遇太多波折,只是沿途衣衫褴褛的难民,使司马懿的心情始终处于阴郁之中。行至陈县时已近黄昏,司马懿找了间客栈投宿,正准备吃饭,只听得门外响起“啪啪”的金属击打声,同时伴着咿咿呀呀的女子吟唱。司马懿寻声望去,只见一老一少伸着手向客栈里的客人讨要饭食。
那老人看上去六十出头,骨瘦如柴,脸上的颧骨如同悬崖上突出的怪石,乍看上去令人忍俊不禁,细细一瞧却又于心不忍,面上的肉仿佛被锋利的小刀刮去一般,只剩下一张皱巴巴的皮,仿佛稍一用力拉扯就会掉在地上,露出眼窝深陷的白骨。
那小姑娘与其说是个年岁尚幼的孩童,不如说是毫无生气的木偶。一双眼睛呆滞中带着茫然,愣愣地望着前方,原本应该红润的嘴唇干瘪着,一旁还长了几个黑色的小疙瘩。老人无力地敲着,小姑娘木然地唱着,嗡嗡哼哼的声响让店里的小二火冒三丈,他边将两人往街上推,边骂道:
“瞎了你们的狗眼,要饭也不看看地界!坏了老子的生意,小心你俩的狗命!”
店小二越说越气,索性抬起脚去踹腿脚缓慢的老人,只听“哎哟”一声,老人没踹着,他自己反倒抖着右手哀号起来,原来是小姑娘寻着机会在店小二的右手腕上咬了一口,蜷缩在角落边的几个乞丐拍手称快。
店小二急红了眼,捡起路边的一根断枝就往小姑娘身上抽去。顿时,小姑娘的哭声、老人的哀求声、看客的议论声混作一团,搅得司马懿心烦意乱。他走出客栈朝店小二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店小二气急败坏地转过身来,发现手上多了几枚钱,立刻变了脸色,恭恭敬敬地问有何吩咐。
“替他们换洗换洗,再准备几个好菜。”
店小二领命而去,不消两刻钟,美味佳肴已摆满了食案。卖唱的一老一少此时已洗漱干净,换了店里的衣裳,看上去倒也长了几分精神。司马懿从老人口中打听到,他们原是兖州人氏,只因兖州豪强叛应奋武将军吕布,兖州牧曹操为夺回领地与吕布大战数月,生灵涂炭,大家为了活命,只得纷纷逃难。途中,老爷子一家七口死的死、散的散,如今只剩下他与孙女两人相依为命。只是这逃来逃去,一会儿大旱,一会儿蝗灾,朝不保夕,哪里是个头啊!听完老爷子的哭诉,司马懿沉默良久。
如今的局势是天崩地裂,旧豪强拥兵自立,新军阀轮番登场,抢粮、抢地、抢人口,无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谁又真正为百姓着想?自诩英雄者不少,但不是今天大口吃酒,明天大刀断头,就是今天高卧软榻,明天身陷囹圄,既无战略做长久之计,更无良策保境安民。这样子你杀来,我扑去,苦的是百姓。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司马懿心中感叹,在现今这种情势下出仕,跟大哥一样做个小小县吏,又有什么意义?不如学胡昭隐逸山林,还能图个清静自在。
时近子夜。
司马懿打了个哈欠,将一册《春秋》收入包袱,正欲吹灯入睡。这时,房外隐隐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他屏气凝神,察觉到那阵声响正由远及近朝自己的房间逼来。他的心剧烈地跳着,手心已冒出了汗,他的第一反应是窃贼,后来想可能是强盗,最后又笃定是这家客栈下黑手。
司马懿瞪大双眼,像老牛一般怒张着鼻孔,抱起包袱缩到墙角,慢慢地向窗边挪去。窗外是一片高低不平的菜地,除此之外全无遮拦,更无垫脚的树木,贸然跳下去恐有生命之虞,但眼下这是唯一的希望,总比丢了性命要强,再说司马懿年纪轻轻,体格饱满,还从小跟父亲学过一招半式,哪那么寸就死了。
嘴里念叨一阵后,司马懿跳了下去,滚到地上才发现,二楼客房离地面并不算高,菜地还格外松软。正当他庆幸自己大难不死时,一起身便感觉不对,随后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脚腕处传来。
糟糕!脚扭了。
他疼得几乎大叫,但怕招来贼人,只得一边忍着剧痛,一边往前爬去。不知道爬了多久,眼前出现一片林子,他靠在一棵树木旁喘着粗气,双手使劲按着左脚腕。疼痛感较之最初稍有缓解,但依然像无数枚细针刺肉一般让人咬牙切齿。夜半冷得要命,他却热汗淋淋,衬服也已经湿透。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也不知道贼人是否还会追来,但他实在爬不动了,他需要休息。
他想到了母亲,母亲自从生下他后身体一直虚弱,好在起居饮食照料得当,才支撑到现在。司马懿心中始终有愧,如果不把自己生下来,母亲就不会变成如今这样,她应该长命百岁,看着儿孙满堂,人人出将入相。
母亲的脸上挂着微笑,那微笑像初夏的阳光一般温暖着司马懿饥寒的身体,但是很快,这种温暖渐渐退去,一种比身体上的寒意更冰冷的滋味朝他袭来——从母亲双眼里淌出的血水浸透了他的衣衫,母亲的头颅瞬间从肩上滑落,黑色的血液喷涌而出,迷住了司马懿的眼,等他擦去血污,定睛一看,母亲已化成血水向四周散去,血水所过之处石墙成灰,树木成冰,牲畜成水。
司马懿惊恐万分,不知所措,他想要逃跑,双脚却不听使唤,他的身体越来越冷,浑身发颤。他打算从包袱里取件外套御寒,却发觉身后伸出一双手紧紧地掐住了他的脖子,他挣扎着,拼命蹬着双腿,就在他觉得自己即将死去之时,那双手抽了回去。
司马懿大口大口地吸着空气,咳嗽不止,此时天已微亮,公鸡的打鸣声让他逐渐镇静下来。
他捏捏脚腕,还是有点疼,不过已能走路,除了衣服又脏又破,脸上挂点伤外,其他并无大碍。他回想着昨晚那个梦,担心家中的母亲出什么意外,犹豫着该不该回家,双脚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