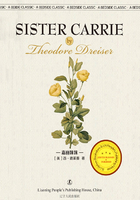劝业会虽然是以前青羊宫神会的后身,但有大大不同的两点。第一点,是全省一百四十多州县,竟有八十几州县的劝工局将货品运来赛会。经周道台的辟画,将二仙庵大门外的楠木林,用涂了绿色的木板,很整齐很幽雅的搭盖成一条弯环屈折的街道,你从入口进去,非将这八十几处小陈列店一一看完之后,找不着出口出来。而各个小陈列店确也有许多可以观赏的东西,吸引游人的眼睛。第二点,是容许女的前来了。若干多的大家闺秀,小家璧玉,在前绝对不许抛头露面的,而在劝业会上,竟可以得到警察和巡兵的弹压保护,而大胆的游顽观赏,并且只在进会场处分了一下男女,一到会场中,便不分了。
这种男女不分,可以同乐的情形,不但使吴鸿、黄昌邦等感觉了饱览成都妇女的美色,——在他们眼睛中,成都妇女,只要年轻,只要打扮起来,几乎无一个不美,无一个不比他们故乡的女人加十倍的美。——并且使许多笼鸟般的妇女,也得此机会,将抑郁的胸臆,略为开舒。如像郝香芸大小姐就是其中之一。
郝香芸、香荃是同着她们的哥哥郝又三,坐轿到柳阴街口,改坐马车来的。他们随着人群,将楠木林中劝工局陈列店游览了之后,顺路越过墙缺,来到青羊宫这面。走过八卦亭前卖细工竹器地方,大小姐忽然想起前六年,自己才十五六岁时,也是赶青羊宫,曾被几个流痞凌辱的事情。当日公共的地方,那么不容许年轻妇女出来,而今哩,举眼一望,随处都是年轻妇女,也随处都有年轻男子追随着在,可是像从前那种视眈眈而欲逐逐的情形,却没有了。
大小姐遂向她哥哥说起这事。
郝又三笑道:“可见世道变得多了!我早已对妈妈说过,淑行学堂你是可以进去的,妈妈偏不肯,只答应过了暑假,叫二妹妹去考。她说,你岁数大了,一个人在街上走不方便。大概她脑经里至今还想着六年前在这里的光景罢?”
大小姐道:“也说不定。我们那时的胆子,真个也太小了,见着痞子,就骇得不得了。如今纵然遇着痞子,就我一个人,未见得便会骇得那样。”
他们说话之际,三个少年恰挨身走过,都回过头把大小姐看了两眼。
二小姐发育得早些,快有她姐姐高了,便把大小姐衣角扯了一下道:“姐姐,有人在看你。”
大小姐回眸一笑道:“出来了,还怕人家看吗?”
她的哥哥道:“你的思想也变了。真的,现在讲男女平等,男的可以看女的,你们又何尝不可看男的呢?”
香荃道:“你讲男女平等,为啥子嫂嫂要来,你又不要她来呢?”
“那又不同了,嫂嫂当了母亲的人,应该在家里尽她的责任,不比你们当姑娘的可以自由自便。”
他们又游过二仙庵来,感得有点累了,遂一同走到一家考究的大茶铺中。虽也是篾篷搭就,但楼板离地有三尺多高,顶上幔着白布,外面临着花圃,茶桌上也铺着白台布,一色的大餐椅子。向左是女宾坐的,凭中悬了一条短幔,但家属男女,也可同坐一处,这也是会场中的一个特点。更方便的就是有洗脸巾,热热的,又有干净的吸福烟的水烟袋,有瓜子,有点心,堂倌也很周到。就只茶钱很贵,起码半角钱一碗,不过细瓷茶碗茶船,都很讲究。
郝又三坐下,洗了脸,靠在椅背上,很舒适的向着他大妹妹道:“歇一会,我们去吃馆子,你赞成吃聚丰园吗,还是一品香?”
二小姐低低说道:“那三个人也来了。”
郝又三注意一看,就是在青羊宫挨身走过的那三个。一个穿黄呢军装的,黑油油一张脸,又高又大,很粗气的。一个穿了身便衣,也是土头土脑的。一个顶年轻的,脸上有红有白,样子很不错。果然也走进茶铺,坐在他们的邻桌上。
那个穿便衣的顶讨厌了,一坐下来,便一双眼死盯着大小姐。一面又与同行的低低的在说话,自然是在议论她了。穿军装的和那年轻人有时也看她几眼。
二小姐有点忿然,向她姐姐说道:“那是啥子人,看得真讨厌!哥哥,叫他们走开些,好不好?”
大小姐假若还是六年前的郝香芸,必也同她妹妹一样的见解,不然,也会红着脸,羞得很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的了。现在,她不但神色自若,反而有点高兴样子,先把那三人看了一眼,才拍了她妹妹一下肩头道:“你这才小家子气哩!别人又没走到我们桌子边来,就像哥哥说的一样,许你也那样看他们就是啦!”
郝又三只管在笑,只管在点头,心里到底有点不自在,有时回过头去,把那穿便衣的恨一眼。
二小姐道:“样子那样土苕,就晓得看女人。”
大小姐笑道:“你这话才怪哩!样子土苕的,就不算人吗?”
花丛人堆中,忽然走出几个人来,距离茶铺约莫十来丈远,二小姐已看清楚了,站起来指着一个穿长袍马褂的人道:“那不是葛世伯吗?有葛世母,还有世妹哩。”
郝又三也站了起来道:“等我去打招呼。”
大小姐道:“用不着去,他们会走过来的。”
葛寰中夫妇带着他们九岁的小女孩,果然对着茶铺慢慢走来,一面谈说着。刚到相当之处,已听见郝又三兄妹打招呼的声气。便笑着点点头道:“你们也来了?很好,很好!我们也来喝碗茶,都转累了!”
葛寰中一进茶铺,正含着笑向大小姐走来,邻桌上那个把大小姐看得不转眼的便衣男子,猛站起来,恭恭敬敬向他鞠了一躬,脸上很有点忸怩神气。
二小姐向她姐姐道:“你看,他也认得葛世伯的。等我去告葛世伯,他那样看女人。”
大小姐正要挡她,她已跑了过去,拉着葛寰中的手道:“葛世伯,你问问他,为啥子尽看我们的姐姐?”
葛太太同她的女儿也走了进来,堂倌与打洗脸巾的,卖点心的,都知道葛寰中是个什么人,以及他的地位,不待呼唤,早已很殷勤的围了拢来。于是一角茶楼上,全是人,全是声气。及至葛寰中把身边的人与事件一一应酬交代清楚,来问询二小姐说些什么时,二小姐大不高兴的哆着一张大口道:“人都溜了,还说啥子!”
郝又三笑道:“世伯刚才进来,那个向世伯鞠躬的,是什么人?”
葛寰中嘘着纸烟道:“那是我的一个瓜葛亲戚,姓吴,一个极没出息的乡愚,你认识他吗?”
香荃道:“就是他,从青羊宫起,他就看起姐姐,一直到这里;我们一进来,他也就跟了进来。我真想你骂他一顿,偏偏他又溜了。”
葛太太笑道:“香荃才是火炮脾气哩。是不是因为他没有看你,只看香芸,才把你气成这样?”
都笑了起来。二小姐通红着脸,挽着葛世妹的手,到栏杆边看花去了。
大小姐道:“妹妹就是这些不开展。我想,既出来了,还怕人家看吗?”
葛太太道:“大小姐说得对。到了我们这年纪,想人家看,还没有哩。年轻姑娘,打扮出来,要不多收些眼睛回去,那才没趣哩!”
葛寰中拿指头把纸烟灰一弹道:“日本女人,……”
他太太忙止住他道:“你的日本女人又来了。真是呀!随便说到啥子,总有你的日本。我们今天打个赌,赌你一天不要说日本,好不好?”
又都笑了起来。
葛寰中笑道:“好!我就不说日本!不过,我还要说一句,像吴鸿这样看女人,在日本并不算一回什么事,只是在此地,风气刚开,却有点不对。”
他太太问道:“你说这姓吴的是我们家瓜葛亲戚,我咋个不晓得呢?这娃儿看起来,好土气!是那里人?现在在做啥子?”
“现在在进速成学堂,还不是我的一封荐书,才取进去的。说起亲戚,那就远啦,是幺孃堂兄弟媳的娘家侄孙。”
“啊哟!你说到胡家那一支人马去了!多年没有来往的了,难怪我弄不清楚。”
“岂但你弄不清楚,我不是那年奉委到卬州查案,不期而遇,到羊场避雨,同场上一位年老乡约谈起,还是不晓得有吴家这门亲戚。那时,吴鸿的老子还在,倒是一个好人,种着十来亩田,安分守己的。因为就住在场外,还来看过我,一定要请我到他家里,我没有去,送了我一只烟薰鸡。那时,吴鸿不过八九岁,简直是一个啥子都不懂的蠢虫。……”
“如今又懂了啥子吗?”他太太插嘴笑道:“光看那土头土脑的样子,就晓得是个乡坝老儿。”
葛寰中看着大小姐笑道:“你伯母的话简直不对!他若啥子都不懂,他又不从青羊宫一直把你看到这里来了!……哈哈!……你们不晓得,乡坝老儿若开了眼,比你们城里娃儿们还精灵些,还会作怪些。”
大小姐红着脸笑道:“世伯真爱说笑。你不要听二妹妹胡说,会场里这么多的年轻姑娘,他那里就专在看我!”
葛寰中道:“知好色,则慕少艾。像大侄女的模样,要说看了不跟着尽看的,那真是只有一事不知的浑蛋才行。吴鸿虽蠢,虽是土气尚未大褪,虽然眼界还未大开的乡愚,到底是个能辨妍媸的少年。……像那般女人,他一定不追踪着看了。……”
他手之所指,正是几个小家人户的妇女,头上包着已不时兴的青洋缎帽条,穿着滚了驼肩和腰袖的葱白竹布衫,银首饰,银手钏,脚是没有放的。一个个涂得一张雪白的脸,两颊胭脂死红的巴在粉上。有两个自己提着水烟袋,还有一个执着一根红甘蔗,当着手杖。正说说笑笑,一步三挪的,从楼外走过。
他还接着说道:“岂不丑得可以?像这类丑女人,在日本,……”
大小姐看了他一眼,他自己也警觉了,笑道:“犯了禁,犯了禁!”
他的女儿本已吃了许多点心了,走过来叫道:“爹爹,你说今天领我吃馆子哩,咋个还不走喃?”
郝又三忙让道:“世伯同世伯母只管请便。”
“说那里话!我早就打算请你们来耍一天,我招待的。偏你令尊大人总提不起劲,我以为他把鸦片烟戒了,精神总更要好些,却不晓得反而衰老得多。你令堂也是那样的不好,瘦多了,我上前天见着,把我骇了一跳。倒是你的令叔,纳了宠后,心安理得,也发了体,听说要生娃娃了,是真的吗?”
郝又三摇了摇头。跟着便说道:“世伯打算吃那个馆子?”
“聚丰园吃大餐去,好吗?”
他太太道:“吃大餐,你不要也去闹个笑话,着傅樵巴儿的《通俗报》登出来,才好看哩!”
葛寰中大笑道:“我何致于!”
郝又三问是啥子笑话。
“你没有看《通俗报》吗?”
“我讨厌傅樵村这个人,太乱了一点,一个《通俗报》,出版了两年,从没有继续出上三个月,隔不多久,又停版了。其实也没啥看头,只是一些诗钟灯谜,我真想劝他不要办了。”
“你却错了。傅樵村之为人,乱只管乱,其实不可厚非。第一,他舍得干,第二,他舍得不要脸,第三,他能得风气之先。你只看他桂王桥那院公馆门口,挂了多少招牌,办了多少事情,又是报馆,又是印刷所,又是图书社,又是代派省外书报的地方,又是通俗讲演所,又是茶铺,他本人还在里面住家。通共是一正两厢,一个过厅的房子。叫别人来,简直是不可一朝居的,而他居然干得很有劲。其可钦处,在此,一般人诋毁他的,也在此。公心评论起来,他不要只想做官,光拿这些事来做幌子,他一定是有成就的,像在……”
他又想说“像在日本”的了,却着郝香荃打断了,她急于要知道吃大餐闹的笑话。
她的葛世伯母叙说出来,才是前天的事。有两个温江乡坝老儿,是两亲家。听说劝业会办得比皇会还热闹,不觉动了凡心,两个人各揣了二百钱,就坐鸡公车赶到会场。游了半天,高兴得很,恰恰肚子饿了,便钻进聚丰园去。只说像乡场上的馆子,顶多吃二百钱就完了事的,不想一顿大餐连洋酒,吃下来一算,十元多钱。把两亲家骇坏了,先说堂倌欺负他们,后来竟大哭起来。闹到周道台晓得了,将两亲家喊去,说了一顿,替他给了钱,这台戏才下了台。
二小姐大笑道:“我代那两亲家想来,倒也值得,哭一顿,着人说一顿,到底耍了阔了。葛世伯,你请我们去,该不要我们哭罢?”
葛寰中笑着站了起来道:“说不定啦!我身边还没有带上二百钱哩,不说别的,此地的茶钱就开不起了!”
大小姐赶紧把她那时兴的蓝白头绳编成的银元包拿了出来。
“我是一句笑话,大侄女就信真了么?不管它的,我们走罢,何喜他们自会来清帐的。”
堂倌等人又都笑容满脸的排在门口恭送,一般赶会的男女也都很注意的看着他们,眼光灼灼的一直把他们送进花圃当中,那座绝大而绝讲究的篾篷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