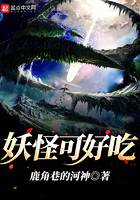第九章 弓将寒
三日后的大街上,晨曦刚起,街道上如昔的热闹非凡,来来往往的走商贩卒形形色色,各自忙碌。
本是平常得很,却忽地一声如雷的乍响,人们疑惑地停下了步伐,一同望向一家小酒馆内,那声响便是从胭脂小馆后堂传出来的,他们很好奇,于是纷纷上前,有的围观,有的索性进了店,皆为揣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胭脂小馆的店小二却似是未闻,店内进了客人,按理说他应该迎上招呼,他却视而不见,继续勤快地擦着桌椅,其实桌椅并不脏,相反地却是干净地发亮。这店小二到底怎么了?大家觉得很奇怪。
而更让人们感到奇怪地是,胭脂小馆一楼里最不显眼的角落里,靠着墙坐着一名带着面具的男子,浑身散发出“生人勿近”的信息。
只见他一身藏青长袍,背上背着的不知是什么东西,竟是用上好的鳄鱼皮包裹着,他们有些疑问,但引不起来他们多大的兴趣。真正引起他们兴趣地是,小馆里突然发生不明的暴响,他却仍旧悠闲地喝着茶,并无半点影响。
按理说,胭脂小馆是酒馆,自然是不卖茶水的,更别说是上好的名茶——君山银针。
但事实是,他确实就在酒馆里品着茶,且是悠然自得地品茶,而店小二不但没赶他走,反而对他礼遇有加,待为上宾。
这样的反常让他们很是纳闷,更自觉无趣,进了店的几人陆陆续续起身离去。一是他们打量了半晌,后堂已再无动静;二是店小二对他们是不理不睬,让他们碰了一鼻子灰。
花钱买气受,傻子才会干。
恢复了清静,店小二仍在擦拭桌椅,角落里的男子仍品着茶。两人各做各的,未曾说上一言半语,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整整三天。而在这三天里,弘苦自在林中昏倒后清醒,她便进了后堂下的酒窑,半步未出。
今日已是第四天,小为边擦着桌椅,眼神却不时飘向后堂,就这样来来回回瞄了数十趟。终于在将近午时时分,他瞄到一抹身影,有弹指的呆滞,只见眼前的弘姑娘已不再是蓝衣飘然的流仙裙,而是一身如血泣的艳红。
没有再迟疑,他立即笑逐颜开地迎了上去,献着殷勤:“弘姑娘,您可是饿了?小为这就给您做几样您爱吃的小菜去。”
弘苦没有应声,只是轻轻地点着头,便捧着手上的酒走向角落的一桌坐下。
她满身的酒气小为不是闻不到,只是他直接忽视了,步伐轻快地奔向后堂厨房。三日了,整整三日弘姑娘滴水未进,饭菜半点不沾,无论他是如何委声相求,还是如何壮言相激,弘姑娘就是不闻不问,了无声息。
无计可施之下,小为把希望寄放到他即怕又敬的陌生男子身上,但那面具公子却不为所动,把他晾到一旁不予理睬。就在他自动理解为面具公子乃是聋哑之人时,却听到有如一股寒流袭来的一句话:“让她喝吧,让她砸吧,等醉倒了,砸光了,她便出来了。”
果不其然,就在那一声暴响的两个时辰之后,弘姑娘果真出窑了。
这样的转变岂能不教他欢喜?无疑在此时此刻,填饱弘姑娘的五脏庙才是他最最重要的任务。
娥眉微蹙,惨白的容颜胭粉未妆,素面朝天,湿透的青丝在身后用一根红丝带随意束起,几缕散发错开垂下玉面,朱唇惨惨淡淡,眸若游丝,谈不上蓬头垢面,却是满身酒气,算不得残不忍睹,却也是惨兮兮。
她一出酒窑,便沐浴更衣,洗去一身的狼狈,但身上的酒气,她是一辈子也洗不去了,也不想洗去。摆开两个大碗,她抱起酒坛,倾斜的手臂却被人一把抓住,抬眼不解地看向端坐桌旁另一边的男子,与他四目相对。
“你不可再喝。”收回眸光,简单地说出他的意思。
放下酒坛,抓住她的手也收了回去,臂上掌心的温和也随着消失,她把十指收于宽袖当中,笑得有些凄凉,“再喝,我也醉不了。”
“既然醉不了,何苦再喝?不是瞎折腾自已么?”把酒坛撒下桌面,见她只是看了两眼,便不再坚持喝酒,他才暗松了口气。转眼却又见她拿起茶壶,他气定神闲地抢走茶嘴底下的白瓷茶杯,“空腹不可喝茶,伤胃。”
“心都没了,还怕伤胃?”她伸手欲抢却扑了个空,他已离了座闪到一旁,手上还拿着茶杯,她有些懊恼,却明白要他的东西实在不易,何况她现在可没有这个心情,“你让我喝茶,我便请你喝酒。”
“胭脂烫?”他问,人已坐回桌旁。
“是。”
“我不要这一坛。”他指着桌下的酒坛。
“它便是胭脂烫。”
“不是。”毫不犹豫地否定。
“是我亲手酿的酒,莫非我还会拿错不成?”没有拍案而起,她反而笑了,双眸闪着不易察觉的晶光。
看着她的笑,他却笑不出来了。明明心里苦得很,却还强作欢笑,这样的笑是世间最最难看的笑容,也是世间最最痛心的笑容。
接过她手中的茶壶径自倒了茶,他端起茶杯,面具下的表情无法得知,她却仍盯着他,盯着他那双唯一暴露在外的双眼,待他饮尽放下茶杯,方听他缓缓而道:“真正的胭脂烫只为一人而酿,真正的胭胭烫也只有一坛。仅仅一坛,绝无二出。”
“你到底是谁?”
“你想知道?”
弘苦瞪着他,恼他说什么废话,也恼自已的心意晴天没看出来,反倒让一名陌生男人给看了出来,最最气人地是,这男子还与她前后不过见了两次面,还是未曾以真面目相见的两次会面。
他没有回答,却伸手摘下脸上的白面具,露出一张平凡至极的脸,不浓不淡的眉毛,不大不小的双眼,微勾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唯一不平凡地是,在他冰霜傲如雪的脸上竟渐渐勾起一抹隐隐的笑,如春风如盈月般温柔的浅笑。
把面具放于桌上,他神情自若,“在下,弓将。”
“弓将?”弘苦乍听这一名初时有些讶异,随着了然地笑开,“原来是弓家堡堡主的关门弟子!怪不得,怪不得了。”
怪不得他箭术那般地好,怪不得她总跟不上他那凌乱却如飞龙在天的步伐。现今想起,那便是弓家堡第一代堡主弓八仙自创的凌波微步——临水八仙。
临水八仙,共有八部,每一部含有八种步伐,每一种步伐又有八式变化,如此层层递进,须有一定的修为及聪慧的天资才能融会贯通,一点点吸收其奥妙,进而运用自如,随走如风,就像是自已的呼吸那般来去自如。
传言,此精妙步伐传了十二代堡主,而其中真正能领会并且运用自如的却是廖廖数人,且从不传外家姓。看他年纪轻轻,年方不过二十五左右,便将临水八仙练得纯火炉青,出神入化。可见,此等修为与天资非同一般,更非随人便有的。
然而,在江湖上,他却是默默无名。
默默无名的人无非有两种。
其一,是真正的默默无名;其二,是表面上的默默无名。
而弓将,无疑是第二种。
弓将,弓家堡堡主弓八仙的关门弟子,行事低调,行踪飘忽,甚少在江湖上行走,几乎让人忘却了在江湖上还有这么一号人物。他原不姓弓,名字更非单字将,至于真正的姓甚名谁不详,身世不详。
——勾阵江湖记事
为此,身为徊生殿十二将之一的勾阵颇为不服气,有一段时日一直疯狂地搜索弓将的踪迹,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似乎弓将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的。引得勾阵更为之好奇,誓言非把弓将的祖宗十八代均摸得清清楚楚不可!
而她,自然也是好奇的,却始终无缘得见。如今见到了,却……有些许的失望。缘由无他,就是这个人太招人讨厌了!
小为陆续摆上热腾腾的饭菜,引得弓将的肚子咕咕地叫,叫得他平凡的脸庞添上了一片绯红,极为不好意思地握手成拳放到嘴边轻咳着,试图掩饰其羞愧,让一旁的弘苦看得忍俊不住笑了起来。
瞬间,沉寂的胭脂小馆内充满了如天籁的笑声。
端上最后一道浓鲜鱼头汤煲的小为正好看到听到这一幕,看着弘苦无法自制的娇笑连连,则是一会震惊,一会随着傻笑。
震惊是因为弓将那一张涨得通红的脸,平凡冷峻的面容此时也变得可爱得多。小为可没忘在这三日里,他面对地是冷冰冰的面具,冷冰冰的语调,冷冰冰的行事,连话也就说了那么一句,终日不苟言笑,让小为在心里直嘀咕怪人一个。
傻笑却是因为自家老板弘姑娘,灿烂如花的笑厣极俱魔力,见到她笑,他也禁不住嘴角弯起跟着傻笑。不同地是,弘姑娘是因为弓将而笑,他却是因为弘姑娘的笑而笑。
用完午膳,小为重新彻上一壶君山银针,相对于酒,他还是愿意弘姑娘多多喝茶的好。收拾好碗筷,他正想退去,却听到饭菜吃得不多的弘苦对着他说道:“小为,从今日起,把酒窑封了。”
“封了?”小为手中的动作定住,满面的诧异。酒窑他早就去看过了,里面岂是一个乱字可言。
酒坛碎片满地,澄澄如水的酒更是流淌于各个角落,酒气漫天,酒水横流,与刚被洗劫过的模样无二致。刚进去时,他差点被呛得缓不过气来,目瞪口呆了半晌,把他心疼得整个人都快碎了!那白花花的银子嘞!
“是,封了。”自此,她不再酿胭脂烫。
小为摸着鼻子悻悻然地转身进了后堂往酒窑去了,如她所言封了酒窑。
弓将轻叹,“其实弘姑娘不必如此,若木晴天在天有灵,他必是不愿看到弘姑娘如此消沉。”
双眸垂下,弘苦缄默不语,黯然神伤拂袖离去。
胭脂烫因晴天而酿,自是因晴天而封。
若不如此,她面对的岂只是胭脂烫?那是一把把利刃钢刀,看一眼便割她一下的利刃钢刀。如此反复,她焉有命在?可她不能死,在让和家老爷子血债血偿之前,她绝不能死!
片刻之后,她重新回到大堂,手里拿着一个与他同花色的白瓷茶杯,眼帘下的一双媚眼虽极力掩饰,却难以抹去那刻苦铭心的伤痛。她放下茶杯,一落座便对着弓将说道:“现在该请我喝茶了吧?弓公子。”
有须叟间的愕然,弓将神色随即恢复正常,他自献丑处,博她一笑,倘若她自已非要跟自已过不去,非得沉侵在伤痛中不可自拔,那也仅是一时的开怀,他便是拿自已当猴戏耍也是无济于事。
二话不说,他替她与自已满了杯,眸中多了一抹赞赏与心安,举杯敬道:“弘姑娘果真帼国不让须眉!弓将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好!”
双双饮尽,弘苦唇畔有着笑,目不转睛地盯着弓将,不言不语,只是浅浅笑着。
弓将被盯得莫名,更被盯得浑身好似不是自已的,一手不觉地搁置于桌下膝上,危机感告诉他,她定是生出什么鬼主意来了。
他不自在,他在想着如何开溜,弘苦都知道,她也想一笑抿恩仇,毕竟人家并无真正伤害过她,只要他将玉盒完好无损地还给她,也就罢了。
似是知晓弘苦的想法般,他掏出怀中一物在桌面摊开,碧绿色的小钻着晶莹的光芒,玉盒稳稳当当地搁于桌面,“在下拿走姑娘的玉盒,也是受人之托,现今完好归还,还望弘姑娘莫怪!”
“受人之托?”这倒让她意外,这偷东西还是他人之意?“是谁?是受了谁人之托?”
他瞥下眼,浅浅淡淡的神情微微思量,似乎在惦量着该不该说。
“是不是……晴天?”她拾起玉盒,小心翼翼地猜着,声音中有轻微的颤抖。
猛地掀起眼帘,他有着惊讶。
她却明白了,她猜对了。
晴天将行酒肆交与她,却又怕她发现了里面夹带的行酒肆后会心生疑窦,寻他质问,于是他让她去挖出玉盒,随后又让弓将去偷走玉盒,待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便物归原主。如此百转心思,却又是为何?难道他不知道她的一片心么?
若他有难,她定全力相助,无论生死。
若他不想她参与其中,她也可听他的,只求在危难之时凭她一身武功保他一命。不然,在那一晚夜宴之上,他若没有饲机让她吞下迷药,他也不会落到命丧火海的惨局,她亦不会在短短三日尝尽锥心之苦,蚀魂之痛。
“弘姑娘肩膀上的灼烧应是无碍了吧?”弓将忽而问道,打断了她的冥思。他怕,她再想下去只会再次钻入牛角尖;他怕,她再钻入牛角尖就永远出不来了。
思绪仍沉在晴天已死的哀痛中,朦朦胧胧中听到他的问话,她眉头微扬,美目直逼弓将,微眯了眼问道:“弓公子怎知弘苦肩上有伤?还是灼伤?”
“姑娘为我所救,我怎会不知?”轻声细语中,他缓缓举杯轻抿一口清香扑鼻的清茶,满容的惬意,似乎很是享受君山银针所带来的芬芳香气。
“为你所救?”她喃喃地重复一遍,在瞬间怔住。思及晴天之死,她蓦然起身,手一伸揪起他的襟口,尖锐的心痛在她脑海中叫嚣着,厉声质问:“那你为何不救他?为何不救他!”
“放火****。他若执意求死,我又能如何?”
“什么……”她的手慢慢松开,无力地垂下,力气在弹指间抽光,瘫坐于木椅中消化着那有如晴天霹雳的八个字——
放火****……执意求死……
那一夜,当她进入木府梨园时,他震惊,他痛心,他没有想到和英会瞒着他邀她赴宴。当他一句又一句地赶她走,当他一声又一声地残酷无情,当他喂她吃下迷药,全因他早就计划好与他们同归于尽,断了木府的根,也断了他们紧追不舍的逼害。
也在那一夜,木晴天死了,木府火光冲天,行酒肆下落不明,和老爷子欲吞并木府酒行的如意算盘毁了,王清想要掌握各方财力的贪念也落空了。
原来,这一切他早就打定了主意,打定了以死换回木家基业的主意,从未有屈于和家屈于王清之下的意图。他只望她离了那是非地,离了那一片他一手酿造的火海,却从未有与她同生死共患难的念头。
但他可曾想过?他若死了,木家就此绝了血脉,就算保住了富可敌国的财业又有何用?就算为了不让王清得逞,不让和家如意,但方法有千千万万种,他何必自寻短见?他又何曾想过,就算他把这一切送与了她,失去他的她拥有了这雄厚的财力又有何用?
失了他,她就算得了全天下,一切也是枉然。
“晴天为何非要选择死?为何非要选择死呢?”空洞的双眸看着同坐桌旁的弓将,几近自语的声音却是飘浮得有如轻雾,脆弱得仿佛只要教风一吹,便无了踪影。
良久,只闻店中小为擦拭着桌椅的沙沙声,走来晃去的脚步声,此时正值晌午过后,外面热闹的街道有了难得的清静。若换在平日,小为必定挂着笑脸扒在柜台上呼呼大睡,但此刻他却是清醒得不能再清醒了,只能不停地干着活,努力忽视店中一隅的窒人气氛。
“活着,未必会比死快乐。”
佛祖保佑,总算开口说话了。
小为双手合十,表神无比虔诚,待他听清弓将突然说出的句中之意时,又猛地惊出一身虚汗。心中大呼吃不消,他逃也似地奔回后堂。
弘苦浅笑着,很是赞同他话中之意,垂下黯然的目光,神情有些木然。
“你知道么?我宁愿你救的是他,而不是我。”她失了焦聚的眼瞳怔怔地落在手心中,泛着蓝辉的玉盒之上,成串的泪珠没入蝴蝶结上的碎钻,绿色的星光混着透明的晶莹闪着光,璀灿异常。
“砰锵——”瓷杯落地,清脆的响声击在人心不断荡漾,尖锐的刺痛在每个人的神经无限制的扩大。
弘苦睨向碎了一地的白瓷茶杯,眸光轻移向上,见他垂眉敛目,执杯的手指僵硬地定格,似是被了点了穴般一动未动。
闻声直冲出后堂到两人跟前的小为一见此景,识趣地缄默不语,迅速转身又回了后堂,一会便拿出拾缀的工具来,一边扫着碎片一边用眼角余光打量着两人。弓将沉侵在自已的思绪中,弘苦盯着他眸光不停流转,若有所思。
神情不同,脸庞却一样失了颜色,苍白得就似冷冬的寒雪,让他不寒而粟。
待到小为收拾完离去,重入了后堂,两人沉重的神色半分不减,气氛降到了最低点,期间有客倌进来者,还未坐下便心生寒意,脚步不由自言地退出胭脂小馆。
午后的人流接踵不息,却无半人敢入小馆喝酒解闷,更无人敢上前一探究竟。
不知不觉,夕阳西落,满天的余辉照在每个行人的脸上,残红如血的霞光万丈,似是催促着人们快些回家,快些回去好点上灯火,让这如血的红光继续延伸。
小为收拾了桌椅,关了店门,点了灯。无风自摇的灯光照在角落的两个人身上,地上拉长的黑影如它们的主人一般静止不动。
一下午了,整整三个时辰,弓将与弘苦两人静静地坐着,他不开口,她也不说话,就连小为期间挺起胸膛,斗胆地端茶递点心的小声询问,两人也未回上一句,甚至连或抬首或侧脸地看他一眼都没有。
都说弘姑娘是怪人,在小为看来,那弓公子也是怪人一个,且怪得很。
正当小为在心里嘀咕着的时候,弓将站起身转身便往店门走,小为直盯着其背影满目的不解,转眼看向自家老板,她却是连眼皮也没提,仍旧陷在自已的思绪中。嚅动着嘴唇,他想开口说些什么,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说弓公子要走了?不,弘姑娘怎会不知?何须他多嘴。
留弓公子在小馆过上一夜?不,弘姑娘生性随和豪爽,却也行事乖张,不按牌理出牌,他还是少招骂为好。
那就送弓公子一程吧。小为如是想着,便跟在弓将身后,抢在前头轻手轻脚地为他开了大门,即时凉风扑面,让人清醒了不少。
弓将的脚刚抬起,还未跨过门槛,耳旁传来娇柔却冷得让人发颤的声音:“弓公子与晴天可是至交?”
他没有回首,他知道背后有一双灼热的眼眸正盯着他,似乎想烧出个窟窿方能罢休。脚板沾地,他一脚踏出大门外,身影在刹那间涅没于一片夜幕中。
小为愣着,满容的不解纳闷,时而眨眨眼睛,时而掏掏耳朵,片刻过后回过神来,才想起要关起大门,嘴里小声念叨着:“弓公子说了什么呀?那么小声,我都听不清了……”
说了什么?静坐于角落桌旁的人儿却是知道的。
他说——
只要你活着,他便活着。
上穷碧落下黄泉,无论生死皆相随。
只要她活着,晴天便活着。
若晴天死了,她便随他而亡。
一切,血债血偿。
*本文版权所有,未经“花季文化”授权,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