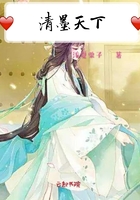2010年,我定居南方后决定去工厂打工。到2012年年底,我将在两家电子厂、一家音像带盒厂做普工的经历写下来后,发现有十几万字之多。这完全是意外收获。在我到达南方之前,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写下如此之多和打工有关的文字。
然而,我到工厂打工的举动却遭到了来自两个阶级的强烈质疑。
首先是来自中产阶级的嘲笑。他们对“打工”“打工仔”“打工文学”等凡和打工有关的词,都会撇嘴,并从鼻孔中喷出一声轻蔑的“哼”。他们有房、有车、有固定的社交圈,他们的孩子不屑参加中国高考,早已到国外学校,他们自己已经移民或正在移民,面对偌大中国,他们看不出有什么新花样值得留恋,他们的身体暂时滞留于此,而心思早已和这块土地距离遥远。无论他们对我多么热情、客气、礼貌,我都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看得起我——我的全部资产不及他们户头的尾数,我亦非社会名流,他们和我在一起,不过是凑个人头一起玩,打发时间。到车间后我深刻地发现,我和那个流光溢彩同时又虚幻迷蒙的中产阶级世界那么遥远,我从来和他们都是两类人,而这一点,他们发现得比我更早,于是,我们在心里互相删除了对对方的关注,让所谓的“好友”,成为陌生人。
其次,是那些从打工者蜕变而来的精英。他们是真正的打工:离开家,背着行囊,被治安仔查暂住证,烂尾楼、榕树下、桥洞里、车间的水泥地上,他们都睡过。他们的手上有伤,心里有痛,眼里有泪。他们有工友,有老乡,有亲戚,有同龄人,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让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也从来都不仅限于一个。他们热烈,激情,冲动,不断为同类呼喊,被冠为“产业工人”代表,但他们的队伍,从来都不会认可我这样一个人,他们认为我去打工是客串,是演戏,在本质上,我并非他们的自家人。
于是,无论是我的打工经历,还是我写下的打工作品,都遭到来自两个阶级的赤裸裸质疑(而他们质询我的语调又是多么地一致):你怎么想到要去打工?!
我对自己生气,感到委屈,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凌辱——我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写点大衣如何防虫蛀、马鲛鱼怎么煎、正午如何防晒,这样的话,没有任何人会来申斥和指责我,大家都会说我多么热爱生活,而我也会拥有更多的朋友。然而,我却自己拿着身份证,来到工厂门卫室,从窗口将证件递了进去。
是的,我并不是为了工资去打工,但我却是以打工者的真实身份去打工的。在进入车间之前,我对此中秘密一无所知。进入车间后,我和所有女工一样,有定额任务需要完成;如果我做得不好,一样要返工。没有任何人会照顾我,而我也因为这种不被照顾,看到了车间世界的真相。
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我是普工,坐在高脚凳上,从最基本的贴pass纸开始,装袋子、打黄胶、焊锡、装电子元件、使用砂轮机??这些活儿算不上重体力劳动,但重复多次后也会变得模样狰狞。在音像带盒厂,我是啤工118号。啤机二十四小时开机,啤工“两班倒”,除了中午吃饭的一小时,啤工每日工作十一个小时。在注塑车间,我坐在两台轰隆隆的啤机之间,用蘸了天那水的布擦模具,用钳子剪掉衣服架子上的凸起物,用吹风机将录像带盒边缘的披锋吹皱。当这些活计不停地重复时,我终于发现,汗不仅能从鼻尖流出,还可以从身体的各个部位流出。
我排队去打饭,吞咽下含混的饭菜,喝下看不清内容的汤,将胃填塞到鼓胀,可两个小时后,饥饿感仍会陡然变得强烈起来,让我意识到我所吃的食物多么没有油水;我将被褥搬进女生宿舍,惊诧地发现除了逼仄、肮脏、混乱外,宿舍的后门根本关不紧,夜晚冷风呼呼灌进来,厢式货车的轰隆声像从头顶压过,怎么都睡不着。
当我将这些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时,并非将个人看得格外重要,以至于向旁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我感觉我所经历的,不仅仅代表是我一个人的遭遇和体验,也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和体验。我看见自己坐在注塑车间那个倒扣的塑料箱子上时,我的内心忍不住想要说点什么,就像要为某个画面提供一段画外音般,我想要说出我的注解。
我总是忍不住想要说点什么。从西北迁居东南,我突然遭遇来自心灵的巨大震颤:我从熟悉的游牧文化、绿洲农业文化场景,猛然空降到烟囱林立、工厂成片的场景中,好像一阵龙卷风将我突然吹起,投到我此前根本没有准备好的地方。一切在别人看来常态的事,都被我陌生的目光放大了好多倍,我所感受到的,全是差异和震惊。我不能对此有所抱怨,而这也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获得的一种新自由。
我想写的文字,不是和现实生活若即若离,而是深入到实际中,和人类面临的问题呼吸相通。我希望这些字和词,是来自深处的呼声,而非轻浅的呢喃;甚而有时,我希望自己的文字像文献资料那般,无需纠缠于词语本身的修饰,而首先成为一种见证。在我看来,如果我不能处于描述对象的王国之中、没有参与到那些具体的活动场景中,只是以接受者的身份、用被动的眼光去记录事物的外部印象,那我的情感和文字就是有隔膜的。如果扛着摄像机或举着照相机对准那些正在干活的女工,她们会浑身别扭得想逃到地缝里去。如果我和她们一样,要完成一天二十箱的任务,上厕所要在规定的次数之内,那她们面对我就是松弛的。
然而,某种尴尬是我所必须面对的:我过往的经验,让我愈发孤立于我的新环境——我来自“另一个陌生之地”。当我在南方说出新疆草原上牧人看到陌生人会将之待为上宾、拿出家里珍藏的好肉好酒来招待时,我看到的不仅是对方眼神中的惊讶,更有一种公开的嘲弄。这刀片般的眼神,令我心悸。我像从人类的原始状态中缓慢走出,还携带着婴儿的痴憨和愚笨,对人性之恶、之复杂、之残忍,毫无洞见能力,于是我的智商连同写作都遭到颠覆:一个如此思考问题的人,能写出怎样的作品?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当我置身南方,回望新疆,我发现我已改变了几分。譬如,当我看到“大美新疆”这个词时,会感到异常别扭。这个词似乎是专门发明出来给那些“非新疆地区”的人看的。一个“美”,已经很武断;再被修饰为“大”,能完全代表新疆吗?到达南方后,我才发现,内地人对新疆非常陌生,这个距离,比起从深圳到乌鲁木齐的五千公里,更遥远。事实上,无论新疆的地貌还是历史、民俗民情,都比电视上、明信片上的更复杂,而这种复杂性,却被“美”这个词轻易取代。“美”本身是个很好的字,但是这种简单定义,以人为之力强行塑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新疆。
我经常感到痛苦。我的痛苦如此深切,似乎已无需什么理由。我的痛苦来自南方,也来自北方。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我都能清晰地闻到那股味道——不是好感,而是恶感。令恶感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有一个原因至关重要:陌生感又加剧了恶感。在东南沿海,中产阶级不了解打工一族,而普遍的仇富心理,又让底层对有车有房者既羡慕又厌憎;在西部内陆,诸如西藏和新疆等地,各族群之间因信仰、文化等复杂原因常有纷争凸显,绝非如明信片上的景物那般,一片静寂。
离开新疆大地已近三年,但是,新疆的景物,也许还有它的精神,从来没有遗弃过我。我是到了南方,戴上“啤工118号”的牌子,在车间里不断劳作,才充分认识到我从浩瀚广阔的新疆吸收到了多少养料——只有在那样的淳朴中浸染过的生命,面对这工业化时代不断重复的机械劳作,所体验的疼痛才如刀似剑,插入胸口,异常强烈。我所写下的南方车间,绝非一系列现象的简单拼贴,它们因西北底色变得奇异与丰富。
面对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场域,我浑身紧绷,异常敏感,不断地在笔记本上写下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并对这些事件进行检查、观察、验证。我描绘下我所看到的一切:车间、组长、快餐、瓦房、手指、油污、铁链、伤疤、疼痛,它们组合出一幅既遥远又具体的意象地图;同时,我写下我心中涌动的一切欲念,我的反感、欣喜、愤怒、悲哀、委屈、狂暴、暧昧、冲动。每一次,当我被这样或那样的情绪所控制时,我都在向着一个最真切的词靠拢——真实。我努力想写出我所看到的真实、我所体验到的真实。我希望寻求一种真实,唯有这种真实才能把自己从旧有的窠臼中解救出来。
在南方,我因脚踩那片广大的西北之地而获得了一个从高处观察车间的机会。同时,因我耐心地坐在啤机之前,我又得以巨细靡遗地观望它。这个双重眼界,成为我全部写作的秘密之源。这也是我不得不承担的双重角色:在西北和东南间,架起一座心灵的彩虹桥。
在工厂车间的机器轰鸣中,我会想起戈壁、沙漠和绿洲的寂静;穿上土黄色的工装后,我想起南疆那些穿艾德拉丝绸的美女们,怎样移步于街巷;由简陋寒酸的盒饭,我想起喷香的抓饭;从“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广告牌,我想到喀什大桥上晒太阳的人们。
在新疆的公交车上,我会听到两种语言报站名:汉语和维吾尔语;在南方,我常在公交车、地铁和银行,同时听到三种语言:汉语普通话、广东白话、英语。我总是置身于多种语言的丛林中,总有一些我听不懂的词语,彰显出某个区域于我的封闭。然而,我不禁陷入深思:难道语言的隔绝就意味着理解的隔绝吗?
我想起在南疆,有一次深夜车没油了,我们不得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公路上等救援。天地间除了一轮明月,只有我们这辆瘫痪的汽车。车上的男司机和他的妻子都不会汉语,他们只是顺路将我从村庄捎到县城。在等待救援时,做妻子的要把她的大衣让给我,并低声祈祷。那一刻,我的心猛然抽紧,浑身的热血涌动开来。我突然明白:人和人其实并不像想像中那么陌生,即便语言不通,我们却共同拥有一轮圆月,共同体验着生老病死。总有一个通道,可以把更多的人紧密相连,而非生硬分离。
在到达南方之前,我曾在北疆托里草原采访过当了矿工的牧民。他们的体能很好,是非常棒的工人,但是一发工资就去买酒,喝个酩酊大醉,深夜骑马狂奔,到草原深处痛哭:他们世世代代是牧人,突然转换成工人,百般不适应;到达南方,当我进入车间打工后,我惊诧地发现,在珠三角打工者的感觉系统已渐趋麻木,他们对各种规章制度的接纳都显得训练有素,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但同时,他们对生活本身的热情度,却被降到很低。
坐在巨大的啤机中间,听着轰隆隆的声音,闻着机油、塑胶、灰尘黏合在一起散发出的味道,我想,机器本身是无辜的,它是中性的,不过是人类手脚的延长而已,所有发泄到它身上的咒骂,都令它越发无辜。它被人发明出来,原本是为了帮助人,何以到了后来反而变得和人作对甚至压榨起人来呢?是人自己没有很好地使用机器;是人自己所建立的制度出了问题。某种可怕的恶性循环,把人变成了机器动物、经济动物、享乐动物,唯独不是“天地间那个大无畏的人”。
现在的珠三角,是不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西北地区呢?
在珠三角已露出端倪的那些问题,是否可以事先避免,防止它们在西北新一轮上演?
我终于明白:促使我走向车间的,是我内心那个真正的丁燕,她破坏了这个貌似闲适的丁燕。当我走进车间的一瞬,某种声音自胸腔内部发出:我来了!
当我敲打下这些车间经历时,我觉得轻松极了:那时,我的手指还疼痛着,鼻孔里还残存着辛辣的味道,脊椎骨还僵硬着,但语言却似流水,异常活跃地从身体内部流泻而出。我看到的每一个女工都不是小人物,恰恰相反,当她们把豪迈而狂放的灵魂呈现出来时,我惊诧地发现,那是一片波澜壮阔的大海,洋溢着无比巨大的力量。
我写下了她们的名字,她们的故事,她们的大笑,她们的眼泪,她们的梦想。以前,她们被人随心所欲地描述成一群未开化的人,可以被忽略,可以被随便安上什么名称:农民工、乡下人、外来妹、北妹,似乎都过得去,没有人会来评论和抱怨。她们提着箱子,拽着包袱,跳上公交车,从一个镇转移到另一个镇,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她们不是别人,她们就是我,我就是她们。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个农民底色在作祟:如果我不曾考上大学,不曾在城市里工作,我将和她们一模一样,扛着包,离开家,四处奔波。
我和她们之间的距离,只需要一个转身,就走到了。
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但可以通过文学来感同身受地体察别人的生活、了解别人的世界。正因如此,文学历来成为各国、各地、各族群间互相了解并增进理解的桥梁。我希望我写下的这些文字,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拉近人们的心理距离;我希望用笔定格这个瞬间,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刻,它经历的悸动与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