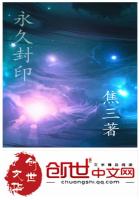第二节 闻一多·徐志摩·冯至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湖北浠水人。
闻一多是著名的诗人、杰出的学者、英勇的民主战士。闻一多的新诗创作开始于1919年,1923年9月出版了他的第一个诗集《红烛》,1928年1月出版了《死水》。他的创作活动,前后持续约13年。他的诗作大多收集在《红烛》与《死水》之中,这两部诗集也是他创作新诗的代表作。尽管闻一多早期创作深受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曾表现出对艺术和人生理想的虚幻追求,弥漫着唯美的感伤的神秘的色彩,但爱国主义始终是他诗歌创作的主旋律。
《红烛》中的《孤雁篇》和《红豆篇》是诗人留学美国的作品,其中不少篇什倾吐了诗人流落异国,饱受凌辱,倍感“失群的孤客”的痛苦。在《孤雁篇》中诗人哀叹:
不幸的失群的孤客!
谁教你抛弃了旧侣,
拆散了阵字,
流落到这水国的绝塞,
拼着寸磔的愁肠,
泣诉那无边的酸楚?
为什么会有“那无边的酸楚”?是因为“孤雁”流落之处充满了蛮横与罪恶:
啊!那里是苍鹰底领土
那鸷悍的霸王啊!
他的锐利的指爪,
已撕破了自然底面目,
建筑起财力底窝巢。
那里只有铜筋铁骨的机械,
喝醉了弱者底鲜血,
吐出些罪恶的黑烟。
……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如此险恶的环境,诗人自然会想起自己的祖国,而且,他是把祖国的形象和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一想到祖国的象征——“四千年的华胄底名花”——秋菊,就情不自禁地赞美“庄严灿烂的祖国”:
秋日啊!习习的秋风啊,
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忆菊》
故土与异域的鲜明对照,更增添了诗人对祖国焦灼难眠的思念。在《太阳吟》中,他将这种思念化为美丽而神奇的想象:
太阳啊——神速的金鸟——太阳!
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然而,驾驭太阳难免有些虚妄,所以诗人接着变换了想象的路线,思念之情却更为真挚热烈:
太阳啊,也是我家乡底太阳!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乡,
便认你为家乡也还得失相偿。
太阳啊,慈光普照的太阳!
往后我看见你时,就当回家一次,
我的家乡不在地下乃在天上。
这里的家乡,正如诗人所说,不是狭义的“家乡”,而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是伟大祖国的象征。《红烛》中的这些诗,洋溢着流火喷石似的爱国激情。尽管诗的风格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但由于有了真实的生活内容,早期诗作中那种超脱尘世的虚幻和隔绝现实的孤傲已有了显著的改变,诗风“渐趋雄浑沉劲”,诗体亦趋向匀称整齐。
1928年1月,闻一多出版了《死水》,这是诗人留学归国之后大部分诗作的结集。1925年5月,闻一多提前结束留学生活回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的蹂躏之下,异常黑暗破败,人民在苦难中挣扎。当他一踏上国土,发现这时的中国并不像他想象中的“如花的祖国”,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诗人一时难于接受残酷的现实,发出了悲愤的呼喊: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问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发现》
诗中热爱与失望两种情感相交织,以奇特的想象与幻想,表达了诗人纯真炽热的爱国之情。通过冷静的观察与思考,诗人对冷酷的现实有了深入的认识,从而发出了愤激的诅咒: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死水》
在《死水》中,诗人怀着炽烈的感情热爱祖国,关注现实,并非是对现实绝望而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显然是以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诅咒现实:既然现实已黑暗腐朽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那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加速它的灭亡。
从赞美文明祖国到诅咒黑暗的现实,反映了诗人由历史转向现实的认识的深化。现实的黑暗,人民的苦难以及对人民力量的确认,使诗人无法安坐于恬静的书斋之中。在《静夜》里,诗人宣称:
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虽然闻一多当时并未真正走出个人狭小的天地,投入到广大民众的革命洪流中去,但是这种可贵的精神,却是他最终与“国家主义派组织”、与新月派分道扬镳,最终毅然走出书斋,投身到争取祖国解放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之中并英勇献身的重要原因。
与《红烛》一脉相承,《死水》的主要倾向仍然是爱国主义的,但较《红烛》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艺术上更成熟。这是诗人对现实认识和爱国主义不断发展和深化的结果。闻一多诗中的爱国主义,充满了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面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表现了“五四”反帝爱国的时代精神,但带有向后看的怀古主义倾向。他曾多次说过:“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这使得他过多地沉湎于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而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揭露与批判,因而造成了他的诗作在思想内容上的某些局限。
闻一多不仅是杰出的爱国诗人,而且还是新格律诗的积极倡导者。针对新诗在形式方面的种种缺陷,他在《晨报诗镌》上发表了《诗的格律》一文。他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闻一多还指出,新格律与旧格律有着根本的不同。他并不主张用某一固定格式来写诗,他认为,“诗的格式是相体裁衣”,因不同题材、意境、情绪而异,力求臻于“精神与形体调和的美”。他提倡“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闻一多之所以大力提倡新诗的格律化,是针对早期白话诗创作中存在的过于散漫自由,流于散文化的倾向而发的。它顺应了新诗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新诗艺术水平的提高,其积极意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闻一多不仅理论上大力提倡,而且从创作上积极实践他的新格律诗理论。《死水》中的绝大多数诗都是新格律诗,这些诗音调和谐,字句整齐,词藻斑斓,多姿多彩,其中有不少诗,堪称新格律诗的典范之作。
闻一多的诗还十分注重意境的营造,追求意境的优美、新颖、完整、统一,他巧用暗示,有丰富的想象。这与他善于创造性地继承中外诗歌的优秀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因为如此,他的诗真正成了“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徐志摩(1897~1931),名章皘皃皐皊,浙江海宁人。
徐志摩的诗集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以及《云游》,散文集有《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小说集有《轮盘》,还有与陆小曼合著的剧本《卞昆冈》。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以诗的成就为最高,“当时诗人除郭沫若,当推徐志摩”。
徐志摩向往科学与民主,追求自由与人道,因而他一旦面对现实人生,就感到“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我忧郁,我信,竟然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这一思想感情的变化,也就促成诗人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徐志摩深受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的影响,诗风徘徊于清远超脱与热烈奔放、柔美和谐与悲凉阴冷之间。他最注重情感抒发的音乐性,运用白话(俚语以至方言)表达心灵跌宕的节奏,形成激情奔涌的旋律,以至于诗人诗句的流淌犹如“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
诗人徐志摩正是在对于“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的执著追寻中,将自己对于人生的追求,融入勃发的诗情,在外来诗风的吹拂下萌发出独特的诗美之芽,形成个人的风格:无论是捕捉瞬间感受,在狂热的激情中抒发灵感,还是郁积酝酿情绪,在冷静的挥洒中揭示人生,都能在如脱缰的野马的心灵咏唱中保持着至情至性,始终如一,保持着几分“天籁”,是那样的清新自然,明晰和谐。
1925年8月,《志摩的诗》由徐志摩自编自费出版。这部诗集由北新书局印刷了50本,其中收入1922年到1925年间的诗作55首。1928年徐志摩将这部诗集加以删改,于8月由新月书店出版,其中根据朱湘的批评删去15首,并将朱湘认为最好的《雪花的快乐》改排在卷首。在《雪花的快乐》这首诗中,“翩翩的潇洒”、“娟娟的飞舞”的“雪花”,去追求“清幽的住处”那花园中的“她”——“沾住她”,“贴近她”,直到融入“她柔波似的心胸”。作为雪花的“我”,对于梦中情人的“她”的热爱,是一种升华了的纯洁无瑕的理想之爱,是对纯真爱情的渴求上升为对理想、信念的希冀且成为心灵追求的诗意写照,并得到了音乐性的表达: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飞,飞,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在这首诗的第一节中,经过由开放柔和的“花”、“洒”,到响亮上扬的“向”的换韵,巧妙地传达出“雪花的快乐”的节奏感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在一句三顿之中,通过“飞”的复迭,使“雪花的快乐”上升到了最高点,展示了心灵颤动的主旋律。这一节奏感与主旋律在其余各节中反复再三,将诗情抒发推到了高潮。
在《沙扬娜拉》中,对告别时的瞬间情景,用“水莲花”作譬,来表达日本少女的“娇羞”,更运用日语“再见”的音译“沙扬娜拉”来传达出难以言传的“甜蜜的忧愁”。而在《沪杭车中》,诗人则别出心裁地以拟声词“匆匆匆!催催催!”来摹拟火车行进时的轰鸣,形成诗情抒发的基调,达到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渲染效果:“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客,催老了人生!”可见,徐志摩的确是要抓住每一首诗的“原动的诗意”以寻求相应的诗律。
在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中,出现了“一个绝大的进步”。这一进步是基于这样的意识:“诗的难处不单是它的形式,也不单是它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像颜色化入水,又得形式表现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所以,这个诗集中主要是爱情诗,其中潜伏着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的苦恋——“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因而感情真挚、热烈、缠绵、执著,或者借助一个新颖诱人的比喻,或者描绘一个别开生面的场景,或者叙写一个简洁明快的过程,表达那如缕的情思,如水的情波,如幻的情心,如痴如醉而甜蜜忠贞。有温柔的细语,有旦旦的信誓,有爱意的埋怨,有无尽的体贴,还有那爱的追求所产生的力量与勇气。
你我千万不可亵渎那一个字,
别忘了在上帝跟前起的誓。
我不仅要你最柔软的柔情,
蕉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
我要你的爱有纯钢似的强;
在这流动的生里起造一座墙;
任凭秋风吹尽满园的黄叶,
任凭白蚁蛀烂千年的画壁;
就使有一天霹雳震翻了宇宙
也震不翻你我“爱墙”内的自由!
在这里,通过每两句一转韵,来展示情感体验的有张有弛,显得更为自然亲切。而直白朴实的语言使诗抒发的冲击更能引发起共鸣,显示出真正的人之爱的永恒价值,从而激发在现实抗争中对于人的自由权利的追求。
当然,《翡冷翠的一夜》中也不乏对于现实丑恶的诗意揭露,仅从诗名《人变兽》、《这年头活着不易》,就可以看到诗人关于痛苦人间的呼吁。但是,诗人并不止于灵魂的悲哀,写出了《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来进行现实的呐喊:牺牲者犹如“梅花”似的“热血”不会白流,只有付出血的代价才能驱除那“冷翩翩的飞雪”,争来“真鲜艳的春景”。在这里,“雪”的意象被翻转,从天上回到人间,从而成为冷酷无情的屠杀者的象征,于是“梅雪争春”展示出社会变革的必然趋势。
1928年3月10日,徐志摩主编的《新月》月刊创刊发行。在署名“编者”的《新月的态度》一文中,他列举并批评了文坛上所谓的13种派别,提出要为“人生的尊严与健康”而奋斗。在创刊号上,徐志摩发表了《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秋虫》等诗作。前者有着“我是在梦中,黯淡是梦里的光辉”般的颓废情绪;而后者有如“花尽着开可结不成果,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等诗句,表现出某种消极的倾向。
尽管《猛虎集》及其以后的那些诗作,在内容方面流入了怀疑与颓废,呈现出一种“向瘦小里耗”的倾向,但是综观徐志摩的全部诗作,无论是写景记事,还是感遇抒怀,都具有极强的抒情性,形成了独特而不断发展的个人风格:诗风由细腻而多出一点深沉,由轻盈添上几分凝重;语言的运用也由稍显生硬而趋向圆熟,尤其是对心灵咏唱的音乐性表达愈加自觉而自由。因此,诗人在《再别康桥》里,将写景、记事、感怀融为一体,在音乐般的语言倾诉中,再现了飘逸而温柔、幽深而潇洒的诗人风姿,于是——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正是以其源于“性灵暖处”的咏唱来刻意追求诗的完美,尤其是音乐美,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河北涿县人。
冯至于大学时代开始诗歌创作。1923年与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等人在上海创办“浅草社”,1925年在北京与原“浅草社”部分社员一起成立了“沉钟社”。他先后出版的诗集有:《昨日之歌》(1927年)、《北游及其他》(1929年)、《十四行集》(1942年)、《西郊集》(1958年)、《十年诗抄》(1959年),1980年出版诗选集《冯至诗选》。冯至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三个时期。前期以1930年为界,主要收集在《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之中,是他最有成就的创作期。中期于1941年前后,诗人寓居昆明郊外写下的《十四行集》,诗情开始明朗化。1957年前后创作的《十年诗抄》,是他诗情爆发的第三个时期,讴歌时代和社会,成为其抒情主调。
冯至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于诗坛的重要抒情诗人。鲁迅曾将冯至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最大特色便是诗歌艺术的节制性。他将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化为单纯明朗的形象;将内心激越的情绪通过外形的节制,外化为客观物象,或蕴含于简单情节的娓娓叙述中。辑入《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中的诗,扑面而来的抒情主体形象,是一个为生计而漂泊异乡,满面尘土和疲惫,内心充满寂寞与孤独的青年沉思者形象。诗人在异乡的荒街上,看到的是满目的人世疮痍:“歧路上彷徨着一些流民歌女,/疏疏落落地是凄冷的歌吟;/人间啊,永远是这样穷秋的景象,/到处是贫乏的没有满足的声音。”(《北游》)他的落寞是时代的落寞。在这落寞孤独之中,诗人企望情爱,呼唤人间的温情:
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静静地没有言语。
你万一梦到它时,
千万啊,不要惊惧!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影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轻轻走过;
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蛇》
诗人将自己炽烈、真挚的情思寄寓在“蛇”的冰冷而寂寞的意象中。此外,《我是一条小河》,也是诗人企望情爱而终成幻影的写照。
诗人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着意追求诗意哲理化,这使他的抒情具有一种“沉思”的调子。朱光潜曾评其诗说道:“融情于理,时有胜境”。诗人在“沉思”之中,为自己深沉、含蓄的诗情找到了一种朴素的诗的外形:不仅诗歌语言外壳达到了“洗尽铅华”的明净,而且采用半格律体形式,诗行大体整齐,大致押韵,追求整饬、有节度的形式美。冯至的诗在探索诗体自由与节制自由间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
冯至作为一个抒情诗人,其突出之处还表现为:他的诗具有个性的鲜明和风格的独到。他将其内向从容、孤寂沉思的个性融注于诗的意象与外部形式上。象征情缘的缘起缘灭的“小河”,“月影一般轻轻地”走过的寂寞的“蛇”,“愁遍山崖的薜苈”,象征人生风雨飘摇的“小船”……无不浸透了凄清、孤苦的色彩。不仅诗的情调充满感伤苦闷,而且诗的节奏舒缓,音韵柔美,这就使冯至的诗在当时的新诗中形成独具一格的幽婉风格。
冯至在叙事诗的创作上也很是不俗,他创作的《帷幔》、《蚕马》、《吹箫人的故事》等颇有影响。诗人从德国谣曲中吸取艺术营养,采撷了我国民间传说与古代神话故事,歌咏追求爱情自由的艰难曲折,虽有一种神秘氛围,“含蓄着中古罗曼的风味”,但表现了对旧时婚姻制度的憎恶和对理想情爱的呼唤,留下了“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就不必打开窗门问:‘你是谁’”等清丽名句,这是现代诗歌中少有的优秀叙事诗篇。
第三节 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
李金发(1900~1976),字遇安,又名淑良,广东梅县人。
李金发在法国学习绘画雕塑时,受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影响,诗潮如狂。所写的339首诗结集成《微雨》(1925年)、《为幸福而歌》(1926年)和《食客与凶年》(1927年),寄回国内出版,获“诗怪”之称。他的情诗具有独特的诗的世界:一是生死意识的张扬,表现“对于生命欲挪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惊世骇俗;二是以意象暗示象征,实验新奇组合,拓展了新诗的意象艺术。
青年李金发汹涌而神秘的青春潮,“梦想微笑多情之美人”(《心游》),“为幸福而歌”,写尽“少年的情热”。他前两个诗集几乎占一半的诗就是情诗。《她》、《墙角上》、《记取我们简单的故事》、《钟情你了》、《明星出现之歌》等,写长天秋日的初恋回忆、如醉的幽会镜头及温柔的独语:“她是一切烦闷以外之钟声/每在记忆之深谷里唤我迷梦”,吹奏出了“痛饮生命之泉”的欢乐之章。
但是,李金发有他的复杂性。漂泊异国,呼吸《恶之花》颓废的空气,耽迷叔本华的生命哲学,加之个性多愁善感,“一生的矛盾/以生命作尝试”(《太息》),以及对茫茫时空中人的生生死死的观照和思索,他的诗律动着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的无尽悲凉,律动着“在永续之恶梦里流着汗”(《我背负了》)的生命体验。
“渴望痛饮生命之泉”(《Sonnet》),变成了“我有一切的忧愁/无端的恐怖”(《琴的哀》)和“幸福是不可摸捉的”(《灰色的明哲》)惊呼;“自己创造新的‘生命’”(《灰色的明哲》),变成了青春不再、生命短暂的“哀吟”。他感慨于人生的丑恶与物欲横流。“所有生物之手足/全为攫取与征服而生的”(《恸哭》),“用意欲的嬉戏/冰冷自己的心”(《巴黎的呓语》)更加剧了他对人生的绝望与悲观。他不知道为什么被抛入这世界,犹如一个“弃妇”,放逐荒原,孑然一身,“静听舟子歌”(《弃妇》)。他“梦见命运之征战”(《哀吟》)却又悲哀无奈,屈服于命运神秘之翼下,流泻着生命不可理喻、命运无法把握的无尽的苍凉感。“诗人凝视”的视角便深入到生命的终点,观照“一切生命流之威严”下“无牙之颚,无色之颧”,去探寻生命存在的终极形式及生命的终极意义。他的诗歌颂“死!如同青春般的美丽”(《死亡》),歌颂死亡,因为它“葬碎了一切忧戚”(《死者》)。《有感》典型地表现了诗人对生死的观照及整体的憧憬:“如残叶溅/血在我们的/脚下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作为“死神唇边的笑”,生与死近在咫尺,就像殷红的落叶殒落脚下一样。不过,不是恐惧死亡,而是直面笑对,在“半死”的月下对酒当歌,在情变之怀醉香,宣泄生命的“羞情与愤怒”,悲哀而无奈。这里生与死、歌颂爱情与歌颂死亡奇妙地统一了,因为“能够崇拜女性美的人是为有生命统一之快感的人”。虚无,“在海天的空处/一无所有”的虚无,形成了人的存在的永恒神秘之境,生死对照,生命才有它的美丽,悲哀的美丽。它大概就是生命的终极意义:“但勿轻信我们生命之短促可笑呵!”(《回忆Mikvlasee之游》)
李金发以他的诗表现了他的生死观照和“生命的寓言”,斑驳杂色,如上所述,源于诗人本人的全部复杂性。不过,仍具有某种典型性,即反射出那个悲剧的时代“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苦闷沮丧的情绪和精神状态”。
李金发在诗艺上求异趋新,“苟能表现一切”,表现一切生死的观照及体验,这种独创也就是象征意象的新的组合艺术。他追求诗的神秘和深刻,推崇暗示原则,领悟诗美就在于以象征“一点一点地把对象暗示出来,用以表现一种心灵状态”。他大胆引进法国象征派的意象暗示,实验新奇的组合。从另一角度说,即“观念的奇特联络”。诗是一种语言中的语言,诗的艺术就是语言的选择组合艺术。李金发把创造还给语言,以观念的奇特联络进行语言意象的重构,在强合的高压下造成陌生化的新奇效应,扩大了诗的暗示性和惝恍迷离之美。他不乏这方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拟人新奇。不谈破旧而说“衰老的裙裾”(《弃妇》),托出暮秋心境;不说仰望的高寒而说“巴黎亦枯瘦了”,传出寒夜幻觉。又如“数千年如一日之月色/终久明白我的想象”(《夜之歌》),“月的余光还在枝头上踯躅”(《景》),不一而足。新建构,新比拟,让人耳目一新。
官感交错。李金发的诗是色的世界、音的世界,他以各种奇特组合,如“粉红之记忆”(《夜之歌》),化虚为实;“窗外之夜色/染蓝了孤客之心”(《寒夜之幻觉》),为矛盾语法组合;“山茶、野菊和罂粟,有意芬香我们之静寂”(《燕羽剪断春愁》),为通感。语言意象重构,官感交错,如迷离动人的印象画风。
比喻怪异。比喻是李金发诗生命的全部所在。不过,是“远取譬”而不是“近取譬”,从不似之中求似强合而成,诗感丰盈朦胧,极具意在言外之致。如“我的灵魂是荒野之钟声”(《我的》)、“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生命如你眼瞳般清澈么”(《你的光》)。他善于联合几个不相属的比喻于一个观念上,给读者一种新的暗示。如“人说生活是随处暗礁?那么惟你的湿发与丰红的唇是灯塔之光”(《明星出现之歌》),把爱说成是布满暗礁的生活之海的“灯塔之光”,情人倾心联成妙喻不绝,美丽的诗就在读者的心中不断地得到重生。
由于把绘画雕塑艺术引入诗里,这种意象的组合有了某种整体性。他的一些诗,看上去尽是感官的随意涂抹,而光色音和谐流动如印象画,形成了整体象征。如《律》这首短诗,把秋月朦胧说成是“月儿装上面幕”,把桐叶的凋落说成是“桐叶带了愁容”,把落尽叶子的树形容为“树儿这样消瘦”,光音色浑成于“你以为是我攀折了他的叶子么”的妙问,在一片灰色背景下传出了自然(生命)之律不可逆的弦外音,“有一种浑成的情调的传染”。可见,李金发诗之美,其成功处就在“虽用文字,却朦胧了它的意义,用暗示来表现情调。”而其最大的失误也在这里:过于追求暗示性,过于追求象征意象的新奇组合及观念的奇特联络,造成诗的晦涩,并最终丧失了对诗坛的影响力。
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梦鸥,笔名江思、郎芳、戴月等,浙江杭州人。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1928年戴望舒就以这首凄美如梦的《雨巷》荣获“雨巷诗人”的桂冠,崭露头角。到1932年诗坛刮起了强劲的“戴望舒旋风”,形成了大气候。当年创刊的《现代》月刊一连发表其诗15首,风靡一时,同时刊登的《望舒诗论》,也就是《诗论零札》,被一派诗人奉为金科玉律,稍后不久出版的《望舒草》(41首,1933年8月),也成了他们的典范作品,全国上下,新诗却是模仿他的。
这股旋风凸现了戴诗的真正价值或意义所在:既有诗论也有创作,并有一以贯之的统一的思想情调和形式。具体地说,一是把30年代幻灭一代的幻灭意识化解为瞬间之美,梦幻美;二是把社会人生与自我巧妙地隐藏在想象的屏障里,呈现意象的朦胧美;三是散文入诗,创制“合式的鞋子”,以自由诗体洒脱自如地抒写诗情,呈现飘逸的散文美,从而开启了从新月诗走向现代诗的新纪元。
1927年大革命失败,戴望舒深感幻灭的悲哀。这幻灭流成了“雨巷”的凝视,“太息般的目光”,“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流成荒原如“深闭的园子”,衰草丛生,残垣萧然。戴望舒哀吟道:“忧郁着,用我二十四岁的整个的心。”(《我的素描》)他怀着现代乡愁的冲动到处寻觅温暖的精神家园,于是,他讴歌“天青色的爱情”。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26首,1929年4月),是给他的情人施绛年的,而《望舒草》也多为刻骨铭心的款款情语。在“桃色的队伍”里“不寐”,这场凄迷的单恋留下了“这沉哀,这绛色的沉哀”(《林下的小语》)。他不得不“将有情的眼藏在幽暗的记忆中”(《十四行》),他深情地倾诉这种怀恋:“我底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得甚于我最好的友人”。(《我底记忆》)“独自的时候”的沉思,因“秋”而起的“独身汉的心地”和对亡友的怀念……汇成了悠悠不尽的“悲哀的记忆”之河,诗人不禁为之颤栗:“于是,我的梦静静地来了/但是载着沉重的昔日。”(《秋天的梦》)为超越幻灭感,诗人唱起了“对于天的怀乡病”:“我呢,我渴望着回返/到那个天,到那个如此青的天/在那里我可以生活又死灭/像在母亲的怀里/一个孩子欢笑又啼泣。”从《单恋者》“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单恋到《有赠》梦中情人的怀想;从《游子谣》对于海的相思到《深闭的园子》对迢遥太阳的追求,《望舒草》把这幻灭感演绎成瞬间永恒的梦幻之美,那忧郁的望舒的天空和望舒的梦,反射出幻灭的一代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那就是世界无涯,时光无限,“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寻梦者》)。
因此,对戴望舒来说,诗是一种不能轻易公开于俗世的人生,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人在梦里泄漏自己的潜意识,在诗作里泄漏隐秘的灵魂,然而也只能是像梦一般地朦胧的。”他追求这种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隐藏度。在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建构艺术的张力,既显示又隐藏,不直露,不晦涩,是朦胧的蓝图,而不是永恒的不解之谜。这种传达、这种处理很有戴望舒的个人风格。
注重意象的感觉性。戴望舒论述诗“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他长于这方面的自觉追求与表现,抽象内感化,如“丁香般的惆怅”(《雨巷》);比拟,如“林梢闪着的颓唐的残阳”(《印象》);矛盾组合,如“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我的素描》);通感,如“我已隐隐听到它的歌吹/从江水的船帆上”(《秋》),把新的颜色、声音、嗅觉、味觉及触觉掺入了诗,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有迹可寻,具体可感,让人把握到那微妙的去处。
注重意象的整体象征性。诗人更多地从象征意义上运用意象,并巧妙地以感情(感悟)统摄整合,有文的整体性和自足性,避免了散乱无序,诗境朦胧而不晦涩,有特别的美感;而读者也从所提供的“窗口”(或线索)得以激发诗的审美效应,启发一种永久的诗的情结。戴望舒还擅长电影手法,以蒙太奇的组接方式把一些稍纵即逝的声音或难以捕捉的景物组合成整体象征,而读者也能解读获得诗美。如《印象》把寂寞印上一抹残阳,以蒙太奇手法把幽微的铃声、小船、珍珠如古井暗水剪辑成一幅“茫茫烟水斜阳暮”的印象画,构成了永恒的象征之境,有细部的清晰,也有整体的朦胧之美,读者也能充分领略悲凉风景之中映现的无限悲凉的心境,堪称为“印象和象征派的典范”。
注重意象的系统性。意象成了个人象征,就意味着一个系统可以破译,有着特别的飘忽不定的诗美。经过“旧的事物也能找到新的诗情”这一特殊处理,戴望舒诗中众多的古典意象便被纳入法国现代象征艺术而形成了个人象征系统,由此而筑成的典范模式就是《雨巷》。它由三个核心意象建构:“我”是永远寻梦的浪子,“丁香姑娘”是梦中情人或永恒的女性,“雨巷”则是生命之旅的缩影。诗以“我”在雨巷和丁香姑娘“相逢相失如梦里”,暗示人和理想的主题,即惶惶不安的人和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的主题。这种结构模式贯串于《望舒草》的始终。“我”不断转化为夜行者、寻梦者、单恋者、流浪者、陌生人或物化为秋蝇、乐园鸟;丁香姑娘投影在“桃色的队伍”,不断映现为“永远忧郁着”的八重子、“忧郁的微笑”的百合子、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的“我的恋人”或陌路的人。随着背景的不断变移,“雨巷”单恋的结构便演绎成“对于天的怀乡病”模式,于是有复调或变形。游子在海上“沉浮在海蟒鲸鱼间”,秋蝇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光映照中向往那迢遥的“天末的风”与“大伽蓝的钟磬”,薄命妾哀叹“还会有温熙的太阳吗?”最后定格在乐园鸟不断地飞呵飞。“为了对于天的乡思”,诗又回到原来的主题并加以深化:“自从夏娃亚当被逐后/天上的花园荒芜到怎样了?”
《望舒草》如一首诗,由《雨巷》模式不断置换变形而成,望舒的天空望舒的梦繁复迷离,极少“像面纱后面明媚的双眼”(魏尔伦《诗艺》)之美。
戴望舒诗的价值(或意义)还在于它的散文美,如《我底记忆》所显示的:
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
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
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
它生存在颓垣的木莓上,
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
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
在凄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
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
它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
口语入诗,散文入诗,不押韵,字句也不齐整,字句节奏变成了情绪节奏。对记忆深情怀恋、反复倾诉形成了亲切、淳朴、自然的谈话风格。情绪的漩流在记忆的河中流动着,在声音和感觉之间不断地徘徊,洒脱而自如,散溢着散文特有的飘逸之美。《我底记忆》的创制,使戴望舒得以超越《雨巷》的字句的节奏,而构成对新格律诗“三美论”的反拨,它体现了戴诗散文美原则:
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
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
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
“这是他给新诗带来了突破。”
整部《望舒草》便以这种自由诗体、亲切自然的说话风格自由不拘地倾诉他的单恋,或为《路上的小语》那样的对话体,或为《烦忧》那样的回文体,更多的呈现为《我的素描》那样的独白体,娓娓道来,舒卷自如,洒脱而有节制,淳朴而见功力,敏锐而不失风姿。现代象征诗艺得以充分发挥,诗的散文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望舒草》之后,1939年《元旦祝福》爆发出他的抗战第一声呐喊,戴望舒从个人地平线走向大众地平线,运用超现实主义,把个人的哀痛融于祖国深重的苦难之中,取得了成功。《我用残损的手掌》以“无限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透出沦陷区的一片呻吟。“用残损的手掌”“轻抚”永恒的中国,梦与现实交融成迷人的超现实,那灿烂的太阳与芬芳之春,系人心魄,可以说是戴望舒写得最好的作品之一。
卞之琳(1910~),江苏海门人。
卞之琳是在“五四”新诗潮感召下而成为诗人的。他在闻一多、徐志摩影响下写了大量新格律诗。他的诗短小精练,多是属于抒情短章。他一直探寻着在传统体式与现代意蕴间的一种契合。他的主要诗集有《三秋草》、《鱼目集》、《十年诗草》、《慰劳信集》等,1979年编辑成册,题名《雕虫纪历》。
卞之琳的诗,从思想情绪与意蕴内涵划分,以193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稿主要辑入《三秋草》、《鱼目集》及未曾出版的《装饰集》里。此一时期诗人主要是求学和从事中学教育。生之迷惘与感慨命运是其早年诗作的深层内蕴。他早期诗作勾画出一个“在荒街上沉思”的年轻人形象:孤独无聊,还多少有些绝望。迷惘、苦闷,并寻求解脱是他情绪发展的历程。他在《远行》中这样“沉思”:
如果乘一线骆驼的波纹,
涌上了沉睡的大漠,
听一串又轻又小的铃声,
穿过了黄昏的寂寞,
我们便随地搭起了篷帐,
让辛苦酿成了酣眠,
又酸又甜,浓浓的一大缸,
把我们浑身都浸遍:
不用管能不能梦见绿洲,
反正是我们已烂醉;
一阵飓风抱沙石来偷偷
把我们埋了也干脆。
诗人骑着骆驼走进大漠,正是象征人生之旅,长途跋涉之后的心力交瘁恰如“烂醉”一样。面对人生的挫折,无力解脱,诗人的态度是放弃抗争以至放弃人生。这种矛盾感、挫折感正是现代人在现实中的一种失落感体验。
1935年,诗人的诗歌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圆宝盒》等诗标志着他的诗歌探索已树起了一块醒目路标:它标志着在寻求解脱的努力中,诗人已能在苦闷之上玩味苦闷,在迷惘之外静观迷惘。但对生活的理解已进入一个更加深刻的层次,对待生活的磨难态度也随之变得开朗大度起来。这是《白螺壳》的表白:“请看这一湖烟雨,/水一样把我浸透,/像浸透一片鸟羽。/我仿佛一所小楼,/风穿过,柳絮穿过,/燕子穿过像穿梭。/楼中也许有珍本,/书叶给银鱼穿织,/从爱字通到哀字——/出脱空华不就成!”回首曾经有过的苦闷、忧愁以及一切感情的羁绊,诗人相信,正是它们使生活变得丰富而有意义,就像大海长期的冲刷造就了玲珑剔透、洁净空灵的白螺壳一样。所以面对难以抹去的昔日哀愁,卞之琳想到的是把短暂交给永恒,把有限交给无限,把生活交给时间:“我梦你的阑珊:/檐溜滴穿的石阶,/绳子锯缺的井栏……/时间磨透于忍耐!/黄色还诸小鸡雏,/青色还诸小碧梧,/玫瑰色还诸玫瑰,/可是你回顾道旁,/柔嫩的蔷薇刺上,/还挂着你的宿泪。”从《白螺壳》等诗中可以看出,卞之琳终于挣脱了沉重的白日梦,拂去了往日的忧郁,直面生活的苦难。“苦闷——解脱”的艺术发展轨迹,真实地勾勒出这位沉思的诗人从梦到现实的心灵跋涉历程。
抗战爆发后,诗人走出了个人精神的园囿,写下了“一切劳苦者,为你们的辛苦,/我捧出意义连带着感情”的《慰劳信集》,“协入了一种必然的大节奏”之中。
卞之琳醉心于诗歌技巧与形式的试验。他深受波德莱尔、艾略特和李商隐等中外诗人的影响,将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非个人化的“戏剧性处理”,传统的“含蓄”与西方的“重暗示性”融会于一体,形成了“平淡中出奇”,“用冷淡掩深挚,从玩笑出辛酸”的特殊风格。他的诗显示出着意克制感情的自我表现,追求思辨美的“非个人化”倾向。在诗歌语言上,他追求口语基础上的欧化词汇句法与文言词汇句法的杂糅。他对中国新诗文体的探索有着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