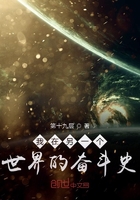这个星期天的遭遇日后将成为陈芳一生中最惨痛的回忆。刚走到那里,一桶污水从楼上泼下来,淋得她瑟瑟发抖呆若木鸡。山坡愣了愣,然后疯了似的冲上去。二楼有扇门刚要关紧,山坡用力一推,屋里关门的女人砰地摔倒,随即响起号炮般地嚎叫声:救命啊,强盗来啦!山坡愤怒地说,你再叫,我******揍死你!女人从地上嗖地爬起,一只肮脏的塑料洗脚盆在她脚下翻了个身,她尖声叫起来,你别过来!山坡弯下腰捡起脚盆,扔到她头上去,女人抱着脑袋逃到了阳台上。山坡刚要逼过去,女人突然从阳台上操起了一把铁锹,她把铁锹举在半空中对山坡喊,出去,给老娘滚出去,你不滚老娘就一锹劈死你!
山坡沮丧地走下楼,抱住陈芳。陈芳在他怀里呜呜地哭。楼下有一爿理发店,他俩就站在这理发店的门口。店里没有理发工具只有三个袒胸露臂的小姐。小姐们懒洋洋地挤在一张长沙发上,漠然地看着他俩,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有一位小姐动了恻隐之心,她说,进来洗洗换身衣裳吧,谁叫你们跑到这里来的?这里是贫民窟,没有道理可说的。
后来陈芳告诉他,小姐将她带到昏暗的里屋,她的眼睛好久才看清那里摆着三张小床,床上床下到处可见揉皱的纸团,一股腥味令她产生呕吐感。好心的小姐将自己的衣服拿给她穿,那裤衩和胸罩上都有一些洗不去的可疑的污迹。陈芳不敢坐到床上去,抖瑟瑟地站在那里换上一件露脐的短上衣,一条牛仔裤。丰乳肥臀的小姐装穿在她身上空荡荡的,她感到一阵阵冷风吹进衣裳,戏弄着她,她实在是尴尬之极。
两个人相拥着走出理发店,好像逃离一个噩梦。挂牌一万四的这套房子,跟那位泼妇只隔了一层薄砖墙,陈芳说她宁愿住到立交桥的桥底下去也不想住到这里来了。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感觉,她好像完全垮掉了,这种感觉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时常浮起在她的心头。山坡搂着她,感受着没穿内衣的小护士身上的战栗,任何不切实际的漂亮话对她都没有用处,只有每平米一万六以上的房子才会起到安慰的作用。
内疚感再次攫住了山坡的心,这种内疚是那么古老,那么陈旧,仿佛从嘉陵江一直流淌过来。小巷里遍地垃圾,两只苍蝇在他俩身边飞来飞去,好像化成蝴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山坡拉着陈芳的手,就在苍蝇嗡嗡的盘旋声中向她倾诉衷情,我这就给表姨写信,他语无伦次地说,我豁出去了,明天,明天我就向老师开口,向她借八万,不,借十万元。
他们回到出租房,陈芳立即冲进卫生间,悉悉窣窣地一阵响,那件露脐装被扔出门来,山坡刚接住它,那条牛仔裤又飞了过来。山坡怀抱着这套衣服,站在门外听到屋里的哗哗水声,感到那热水似乎流进了自己的身体,使他喘不过气来。很久了,他们没有在一起过了。他闭上双眼,仰着头,额上有一根血管在猛跳。有几秒钟的时间,陈芳在唤他,他却没听到,后来他蓦然睁开眼睛,才发现陈芳正从卫生间探出头来,向他要衣服。
我这里没、没有,他结结巴巴地说,没有女人的衣服。
你不必表白,陈芳向他翻了个白眼说,我能够感觉。
露脐装和牛仔裤从他的手里掉落下来了,山坡摊开双手,我表白什么了?他白痴似地问自己。他走向一只破旧的衣橱。他挑出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他回头说,先穿我的行吗?要是不行,我出去给你买新的。
雾气笼罩着卫生间,一盏节能灯半明半暗的灯光下,一个女人的胴体如一幅画,令他的眼睛定格。浑圆白嫩的胸臀展现在他面前,性感飘逸淋漓尽致。他想退出去,但是,她拉住了他的手。于是他把她小心地抱在怀里,她的头顺势落在他的肩上。他用手抚摸着她的脑袋,手指在她的秀发中被勾住了。他心中因此而产生了一种拥有的感觉,他说放心吧,房子会有的。
他确实是这样说的。他说房子会有的。
小护士陈芳的肩膀在他的双手中抖动,令他感到轻微的眩晕,她说,你不要骗我,我再也经不起任何人的骗了。
他们去看第二套房。
他们在卧室与客厅、厨房与卫生间之间来回踱步,房间里洒满明亮耀眼的阳光。天花板上传来楼上住户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一个孩子在嘭嘭地跳绳。陈芳抬头盯着天花板,她说,值夜班的时候,白天我要睡觉的呀。山坡说,那就再去看看城北那套房吧,这个天花板、这个墙像纸一样薄!
等了五十分钟才等来一辆公交车,城北离他们上班的地方太远了。公交车像乌龟似地在嘈杂拥挤的街道上爬行。车厢里有人放了个臭屁,山坡看到陈芳捂住鼻子,一张沁出汗珠的脸涨得通红。山坡拉着她往后面走,但是整个车厢挤满了人无处落脚。终于到了一个车站,车门刚要打开,有人喊皮夹啊我的皮夹子不见了!车厢里骚动起来,司机说都别动,等“110”来吧。山坡看见一个挺斯文的眼镜男往门边挪了挪,一只皮夹掉到了地上。山坡张开嘴刚要喊,陈芳却狠狠地在他手背上掐了一下,陈芳说,咦,这不是皮夹子吗,找到啦找到啦!
车门开了,眼镜男率先下了车,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个十七八岁的小男孩,其中一个剃光头的男孩朝山坡耸耸鼻子,目露凶光。山坡身上掠过一阵痉挛。陈芳又掐了他一下,陈芳心有余悸地对他说,你不要命啦,一车人都不吱声,轮到你来做英雄?
终于到达目的地已是中午。年生已久的梧桐和松树排列在通往社区的小径两旁,透过树枝,斑驳陆离的阳光洒在一片缓缓倾斜的草坪上,给人一种回到家乡般的静谧美感。没有汽车的喧嚣,没有商场的大喇叭,几位老人坐在草地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这环境不像在大城市里,倒让人恍若置身村外的石桥边。一阵强烈的思乡之痛突然向山坡袭来:我们干嘛要跑到这里来?一个小小的乡村医生带着一个小护士跑到大城市来干什么呢?
这是一套总价八十八万的二手房,有一个十二平米的大房间一个九平米的小房间,客厅、厨房和卫生间都是袖珍型的。山坡说,这房子造好有十年了吧,怎么还是毛坯房呢?陈芳说你又在心疼装修费用了不是?毛坯房多好啊,我们爱怎么装修就怎么装修!陈芳打开主卧室的窗子,作了一个近似陶醉的表情,这是一个遥远偏僻的地方,她像朗诵诗歌一样说,但是有一派与世隔绝的田园风光。至于上下班辛苦一点嘛,她闭上眼睛又重新睁开,咬着嘴唇说,就辛苦一点吧!
山坡对着窗口沉思。他看见正对着这套房子的一栋小楼门上挂着一块小木牌,一辆轮椅被推到门口,轮椅上的妇人回首朝他、朝天空和草地看着,那无比留恋的眼光使他心里猛地一沉。那是一张被病魔折磨得又干又小的脸,眼里满是无法形容的痛苦和哀怨。山坡觉得自己回到了县医院,记忆中如幽灵一样出没于脑际的垂危者的眼光全都浮了上来。那种绝望的神情,那种悲戚的阴影预示着他们即将扑向死神的神情,通常会出现在哪里?
阳光照耀着他的眼睛,他避开阳光,陈芳好奇地问他在看什么,他没有回答。昏暗的灯光将木牌上的字影影绰绰聚焦到他的瞳仁里,他的眉头紧紧地锁到一起。钴60放射治疗室。他终于读出了这几个字,他读得很慢很慢,伴随着嘴唇的蠕动涌上脑际的是脱发、再障、血癌。他转身朝门外走去,陈芳拉住他,陈芳说,你怎么啦,这房子不好吗?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下子想不出即便是笨拙的安慰话,于是陈芳先开了口,她放开了他,两只手紧紧地捂着泪水涟涟的脸。“你太不诚心了”,她呜咽着,“我对你实在是太轻信了!”
他们站在草地上,陈芳似乎流不出眼泪了。她慢慢镇静下来。山坡说,“你看见这些老人没有,他们的外套下露出的是什么服装?”陈芳傻乎乎地瞧着晒太阳的老人,终于显出惊讶的神情,“病号服!”她说,抬起头向小径前方张望,斑驳的树荫挡住了她的视线,山坡说,这是肿瘤医院的后门,没挂牌子。
放射室离那套房子不到十米,他们再也不敢回到那里去。回城的路上,小护士一直紧紧地闭着双眼,痛苦地抿紧双唇,好像要把刚才看见的那一幕重新收回去似的。阳光。草坪。小径。梧桐和松树。每平米只要一万六。白骨精美丽的外衣仍在诱惑着她。她梦幻般地对山坡说,那里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山坡挤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说,你也算是学医的,你说可怕不可怕?
表姨的回信到来之时,山坡正在晾衣服。他刚要把小姐的牛仔裤挂到窗外铁丝上去,房东在楼下喊黄医生有你的信,山坡的手一抖,牛仔裤落到了房东头上。被湿漉漉的裤子蒙住脑袋的房东,晃动着两只手发出悲惨的喊叫声,你疯啦,女人的裤子也敢往我头上扔?你给我搬出去!
山坡抖瑟瑟地拆开信。说实在话,他并没奢望能有什么奇迹发生,相反,他只是希望看看表姨的回答,期待着他能感受到她的歉疚之意。果然,表姨说她没有多少积蓄,她丈夫转业后在一家国有企业当车间支书,工厂的效益不太好。山坡从信上得到的唯一慰藉是:表姨说表姨夫的单位有一所职工医院,如果他愿意,可以介绍他去那里当医生。
黄山坡医生当然不愿意去。他知道这所职工医院,他有个同学就在那里当医生。医院穷得十几年没更新过设备了,连一台彩色b超机都没有,来看病的多半是下岗职工,稍微贵重一点的药就没人去配。同学说,几年来人心惶惶的,一会儿说要改制了,一会儿又说负担太重没人愿意收购,有门路的医生护士都已经离开,只有脑满肠肥的头儿们一如既往的忙于吃喝玩乐。
山坡不敢把信拿给陈芳看。他去看他的小学老师。他像往常那样勤快地帮助老师做家务,老师说,歇一会儿吧,哪有这么多可以打扫的!他坐下来,有点局促不安,不知如何开口。老师含笑注视着他的眼睛,等着他说话。山坡说,孩子呢?老师说上她奶奶家去了,自从了解了你的情况之后,她懂事多了,知道生活不易,也知道孝敬老人了。
老师的家离江岸不远,他们听见轮船的汽笛声,很清楚,很苍凉,很遥远,让他们想起家乡。山坡说起这些天看房子的遭遇,老师一会儿笑出声来,一会儿为之欷歔。山坡想自己的人生虽不曾纵意,但也算幸运,有关心他的长辈,有朋友和同事,还有陈芳,连大医院副院长跟老师生的女儿其实也挺可爱。老师说,你说吧,首付款到底缺多少,这点钱我能帮你。到了这时候,山坡反而犹豫起来,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他搓着手,迟疑地说,现在还说不好首付款要多少,等我看好了房子再来麻烦您吧。
老师叫他吃了午饭再走。山坡说中午要请客户。他在街上走着,阳光特别温暖。他请的是省医院两位科长和他们的太太,事先请示过陆总,陆总说地方找得好一点,不要小里小气的。他在张生记酒店订了一个包厢。他算过一笔账,请太太们出席比光请科长们合算多了,现在酒价跟房价一样疯涨,太太在场的话男人一般不会喝得太多。
人群熙攘的餐馆内,一位科长带着他的太太已经到了,这是一个经常在电视剧组跑龙套的女演员。你怎么没把太太带来啊?她说。黄山坡脸红了,他对她的热情寒暄很不自然地报以一笑。我还是王老五呢,他说。他那狼狈的样子惹人同情。女演员拿起一支香烟,黄山坡赶紧拿出打火机,但是手抖得厉害,她看他怎么也没法把手凑上她的香烟,便抓住他的手,在笑声中喷出一口烟。
“我给你介绍一个姑娘吧”,她说,“听说张艺谋都用过她的。”
她说出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山坡看过这片子,但是怎么也想不起那姑娘演的角色,其实他连这位太太演过什么角色也毫无印象。太太说,我演的是一位太太,在一场戏里跟另外几位太太搓麻将,那姑娘因为个子太小,演一个丫鬟。
她说过什么话吗?山坡好奇地问她。
她给我上了一杯茶,说了一句话。她说:太太,请喝茶。
科长笑了,刚进门的三位客人也在笑,他们都听到了这位太太的介绍。山坡的笑容却僵持在了脸上。人们发现了他的异样,包厢里安静下来,手足无措的山坡揉揉眼睛,只觉得全身的肌肉绷得又紧又硬似地,终于,他嗓音沙哑地说道,院长,您亲自来吃饭啊?
是啊,黄山坡同学的小学老师的丈夫,这位副院长说,难道让别人替我吃饭吗?
酒过三巡山坡才搞清楚,副院长原本打算回家吃饭的,走到医院门口碰到了另一对科长夫妇。科长太太随口说了一句有人请我们吃饭,副院长说,谁啊,科长略显尴尬地说出了山坡。他们没想到副院长也熟悉山坡,更没想到他会跟过来,他说,好啊,就吃他的吧,谁叫他是我老婆的学生呢。
山坡当然明白副院长的意思,这是在给他铺场子呢。有他老人家这句话,科长们跟他的业务关系就会牢固一些。他想起老师对自己近二十年不变的关心帮助,心里忽然对这位副院长也充满了感激之情,又不宜表露,他只好再次端起酒杯向他敬酒,他说,院长,我祝您全家永远快乐幸福。
“哪有永远快乐幸福的事啊,”副院长却叹气道,“上有老下有小,实在是太累了!”
满座的人皆是一愣,只有后来的那一位科长太太露出知情人同情的神色。她放下酒杯说,老太太又要换保姆了吗?今年已经换了十二个保姆,她还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还有您那位千金,今年高考估计连“三本”都上不了的,出国去拿一张洋文凭的事,现在就该张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