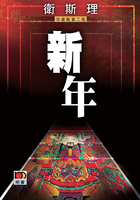人们看见他的额头还在淌血,他手里牵着的孩子在太阳下睁不开眼睛,脸色青晃晃的,孱弱无力地靠在他身上,好像站都站不住似的。人们骚动起来。韩东押着那个保安走到他们身边,韩东说,他们用电警棍打这位老师,网吧里所有人都能作证!保安捂着脸踉跄着朝台阶下走,他嘟哝着说,老乡,俺也是没办法啊,东家叫俺打俺能不打吗?韩东说你别喊俺老乡,俺嫌丢人。
协勤认出了他和唐胜。协勤气呼呼地说,原、原来是你们啊!到了这一步,唐胜也就豁出去了,他说,是的,是我们,我们走投无路了,不得不向上面反映。协勤跺着脚说,找上面有个屁用,强龙敌不过地头蛇,你他娘的迟早还得来求我们!唐胜冷笑着回答说,别忘了我也是本地人,从镇上到县里,我的同学哪个不比你强一点。
协勤正想破口大骂时被二级警司止住,回头看见镇上的一位副书记挤开人群走了过来。欢迎您,欢迎您亲自下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年轻的副书记走到张老师跟前,一把握住他的手说,那脸上的笑容如同中午的阳光一般灿烂。张老师接过他递上的名片看了一眼,脸上没有表情。你分管这方面工作是吗?副书记尴尬地点点头。那就请你按照有关法规秉公处理,张老师严肃地说,给家长们一个交代。
副书记请他去镇委“指导工作”,张老师说不急,我们还没找到孩子。
他叫唐胜带路,去其他四家网吧看看。最近的一家网吧只有三十米远,他们走到那里时,看见一群蓬头垢面的孩子正在作鸟兽散。网吧老板和保安站在门口驱赶着他们,嘴里说快走吧,快走。副书记说,你们搞什么名堂,逃避检查吗?老板嘿嘿地笑着,哪敢啊,他说,本网吧一向遵纪守法,每天都要把未成年人赶走的!
围观者哄堂大笑。唐胜也苦笑着,他说,张老师,算了,今天不用再进任何一家网吧去了。一杆红旗在镇委大楼的半空中飘动,张老师凝目沉思,脸上颤动起几条硬硬的皱褶。副书记看看手上的表,县文广局的领导马上就到了,他说,还是先去镇委吧。
唐胜参加了这个临时召集的座谈会,除了县文广局,镇上的工商所、派出所也来了人。张老师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县正在争取“全国文化先进县”,你们自己看着办。春寒料峭,县文广局局长头上冒出汗来,他说,县里搞图书馆搞文化馆,硬件上投了不少钱,没想到软件上老是出问题。局长对镇上这些干部说,我管不了你们,我只好向县委县政府去汇报,谁砸了县里这块牌子谁承担责任。
派出所来了一位副指导员,居然是张老师在部队时的老部下。他看着老首长额上贴着的隐隐渗血的创可贴,黯然地说不出话来。会散了,局长和镇委副书记要宴请张老师,他摆摆手说不吃了,我去唐胜家看看他父母。副指导员说我陪你去吧,他抢先一步,跑到商务车旁拉开了车门。
唐胜开着车往家走,他从后视镜里看见副指导员那张苦恼的脸,听见他泣血般的诉苦声。小小的一个镇派出所,所长副所长、指导员副指导员加起来有五六个,从部队副团职转业的他,排在最后。而第八天网吧的老板,那位二级警司,竟是排在他之前的副所长!县里、甚至市里都有人罩着他的,副指导员说,逢年过节他忙得人影儿都找不到,下面收来红包再往上送,连所长也不敢得罪他呢。
化工厂的大烟囱在冒烟,烟雾遮挡了他们的视线,大地沉没在泥泞和潮湿的空气中。窗外的景色与车内的人,皆显得萎靡不振,农舍在沮丧中如星星点点的船只漂浮。张老师看着窗外,眉宇间凝结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忧伤。他问唐胜,村口站着的两位老人是你的老爹老娘吗?看来你那个侄子还是没有找到。他的话像铅块一样沉重地坠落在车里所有人的心上。他说,我们对不起这两位老人家,我们拯救不了他们的孙子,不知道拿什么去拯救他。
县里还有几位在云南边疆打过仗的老战友,副指导员拉着张老师去跟他们聚一聚。张老师对唐胜说,他们会送我回去的,你抓紧时间去前堂镇上再打听一下,我估计这孩子不会跑的太远。
一队运送危化品的大型油罐车挡在他前面,唐胜的喇叭声根本不起作用。他想越过这个车队,但是油罐车蛮横地占据了半边超车道。那时候唐胜满耳朵都是打麻将牌的哗哗响声,阿辉在小姐们的指导下从腼腆生疏变得游刃自如。更糟糕的是,十五岁的少年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他的眼睛不老实,总是朝小姐们身上不该看的地方看。这些小姐又穿的如此节省布料,白花花的身子不仅老是在他身边晃来晃去,还时不时地挤他一下。“小猪哥”,唐胜耳边响起一位小姐对阿辉的称呼,他的方向盘抖了抖,差点撞到油罐车的车尾上去。
河边有一个被废弃的驳岸码头,唐胜在那里泊好车,遥望凤仙所在的足浴店楼上,心里像堆了一畚箕垃圾般地难受。唐胜没有直接上楼去,他沿着周边转一圈,好像侦察兵观察地形。一种不良的预感在提醒他,这种地方不是好惹的,黄金荣杜月笙打天下时用过的伎俩,不乏继承的徒子徒孙。
足浴店门前有一棵香椿树,树下放着一张竹椅子,一个少年手里捧一只大茶缸,嘴上叼着一支烟,坐在那里腾云驾雾。他那染过的黄头毛,那瘦小的体型和警觉的神情,都令唐胜感到心悸,活脱脱又是一个阿辉。这少年比阿辉大一点,大约有十七八岁了。一个脖子上挂一条黄灿灿粗项链,体重将近两百斤的中年男人路过店门口,少年立刻站起身来。老板,洗个脚,轻松轻松!男人犹豫了一下,店门开了,一位小姐探出身子来,胖哥哥,她说,人生难得享受享受嘛。
小姐出现时唐胜打了个寒噤。超短裙下两条赤裸裸的白腿,使他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唐胜认出这位小姐,正是约了两个冤大头到凤仙屋里打麻将那位。现在她又逮住了一个“胖哥哥”。这个胖哥哥想必很快会变成一头猪,放在案板上任人屠宰。
唐胜转身欲躲时被黄头毛喊住。黄头毛说这位老板你也来享受享受!唐胜不理他继续往后走,黄头毛追上来一把拉住他。黄头毛说跑什么呀亏你还是一个开本田车的大老板呢,一点男人的气魄都没有!唐胜这才知道自己早已被他盯上了,唐胜扭过脸去说,你才多大岁数,懂得什么才真正叫男人的气魄吗?黄头毛猥琐地笑了起来,说,有钱就花有妞就泡及时行乐,这是我们老大的语录。唐胜漠然地望着足浴店那两扇门,门前小姐的亵衣像旗幡在下午发臭的河风中飘扬,唐胜说,你认识阿辉吗?
你是阿辉的什么人,你找他干什么?黄头毛重新打量他了,歪着嘴像一条警觉的狗舔着舌头。唐胜突然明白,张老师猜得没错,他找对地方了。他伸出手去,一把抓住少年的胸襟。告诉我他在哪里,唐胜用一种压低的带着威胁的语气说道,我是他的亲属,他说,谁敢诱惑他强迫他干什么坏事我跟他没完!
一群麻雀被笑声惊起飞上了天空,少年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那嘲谑就在这细缝里转来转去。你是阿辉的亲属?可笑,真******可笑!他的嘴和鼻孔一起张开了,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样子。他说,阿辉他娘就在楼上,我老大是他的亲舅舅,你居然还敢来冒充他的亲属?他那狭窄的胸脯,如同污浊的河流,不断地起伏着,他说,你这人太欠揍了是吗,居然敢来这里叫板?!
唐胜被突然拔刀相向的少年所惊呆。那是一柄磨得雪亮的水果刀,虽然不是管制刀具,那锋利的刀刃依然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唐胜一躲,刀风擦过他的耳边,削去几茎头发。这是警告,少年收回短刃说,你识相的话就少管点闲事!黄头毛翻着白眼将手指点着他的鼻子说,脸上浮起轻蔑的笑容。
他的笑容维持了一秒钟,唐胜突然一个扫堂腿将他踢倒,然后弯下腰去,将膝盖顶住了他的十三根肋骨。黄头毛懵了,手上的刀落在地上。看上去文绉绉的唐胜,在学校里参加军训时获过奖,对付这样的小毛贼绰绰有余。他的膝盖往下一压,黄头毛的肋骨发出了吱吱的声响,小家伙惊慌失措地说,饶命,老板你大人不记小人过,放、放我一马。
足浴店里有一双冷冷的眼睛,目睹了这一幕场景。他把手一挥,两名身高马大的汉子冲了出去。唐胜警惕地往香椿树下跑去,拎起了那把竹椅子。他的脚一抬,地上的大茶缸飞了起来,猝不及防的一条汉子被滚烫的茶水浇得哇地一声叫,腿一晃,跌倒在地上。唐胜顾不上另一条汉子,他冲上足浴店的台阶,举起竹椅做出砸那落地橱窗的姿态。阿辉他舅舅你给我出来!唐胜站在店铺门前高喊,你还有一点人性没有,连自己的亲外甥都不放过?!
喊声惊动了左邻右舍,有人说见鬼了,大白天派出所跑来抓嫖抓赌了?
还有人说一定是黑吃黑,老板的仇家找上门来了!半条街上一阵混乱,许多跑出来的顾客衣衫不整,有的光脚有的趿拉着拖鞋。那个胖哥哥跑到门口猛地怪叫一声,项链,我的金项链还在包房里!他匆匆忙忙地回转身,撞倒了门边的迎宾小姐,小姐在地上呻吟着爬不起来,店堂里乱作一团。屋里的老大正要走出来亲自教训他时,听到了凤仙扑在楼上窗口前的惊呼声。他大伯,你别乱来,阿辉在我这里!
后来的日子,唐胜总是想起凤仙怀里抱着的一个婴儿。这婴儿平时寄养在外婆家,这天是满周岁的日子,几位小姐妹拉着凤仙为她庆生。婴儿睁开好奇的双眼瞧着他,使他冷静下来。他怕吓坏了婴儿,因此而没跟凤仙争论也没训斥阿辉。那是一个从来没有见到过父亲的婴儿。她的父亲在她母亲还没有怀上她时,自称是个有房有车的金牌王老五,等到凤仙肚子里有了她,才发现他在老家不仅有糟糠之妻,还有一对双胞胎子女。逃之夭夭的父亲连买一瓶奶粉的钱都没有留下,凤仙的泪水像雨水一样尽情淌落在孩子的襁褓上。
在一线可怜的楼道灯光底下,眼泡皮浮肿的阿辉脸上起着一层微微颤抖的鸡皮疙瘩,像拔了毛的冻鸭似的。他不想跟唐胜回去,唐家老宅那三间农舍哪有这里的嫣红姹紫有趣。但是他又不敢对抗,大伯的眼神像一把刺刀顶在他的胸口,他只能一步一步往楼下走。回避唐胜眼神的不仅有阿辉和他的母亲,还有那些小姐与麻将客。他们默不作声地看着唐胜押着这个俘虏上了车,寻欢作乐的兴趣因此而低沉了许多。
紊乱的小街很快恢复了平静,一个女声的骂声从足浴店传出来:胖家伙逃掉了,不仅找回了他的金项链,连小费都没付!同事们幸灾乐祸地笑起来,她们说那你今天不是想抓一个冤大头,自己却成了冤大头吗?嬉闹之间,一位小姐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她的肩膀猛地缩了起来,转过身往包房里跑,我的手机被客人偷走了!这个杀千刀的老嫖客,她凄凉地喊道,我被他折腾了整整一个钟啊。
被黄头毛称为老大的凤仙弟弟终于走出了他的办公室。他拍了拍前台台面,店堂刹那间安静下来。人们小声议论着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了,他站在橱窗前凝望那个被废弃的驳岸码头。唐胜的车子已经绝尘而去,码头上静悄悄的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从这个旧码头过去五公里是一个从内河通向海洋的新码头,巨型臂吊在半空中微微颤动。那里有许多仓库,看守仓库的有保安也有临时工,一些潦倒至身无分文的赌客可以去那里打工,挣到了几个血汗钱再回到赌场去。凤仙的弟弟掏出一支烟,身边那位被唐胜浇过一脸茶水的马仔赶紧摸出打火机,啪的一声,给他点燃了那支软中华香烟。
前几天你说看见唐利在那里替人看仓库,凤仙弟弟喷出一口烟说,你没有看错人吧?
那汉子迟疑一下说,他比过去瘦多了,蓬头垢面像个叫花子似的,但还是那副躲躲闪闪的神情。
凤仙的弟弟坐在前台上喝茶,斜眼瞟着他的马仔远去。那汉子怀里揣着老板让他送给唐利的一千元钱,嘴里哼哼着“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一肩高一肩低地走着像个醉汉。那歌声听来有点莫名其妙。他说老板你这么好心会有好报吗?说不定今晚他就全扔进赌场去了。老板笑笑说,那就随他了,反正他有这么一个好哥哥,总不会看着他彻底完蛋的。
四
马仔是在码头上一个仓库改建成的赌场里找到唐利的。那时他已经输得只剩下身上的羊毛衫。这件羊毛衫原本是唐胜放在老宅的,被他顺手牵羊穿上了身。那天凌晨,从老爹老娘的抽屉里他搜到两千元钱,这两千元使他没日没夜地在赌场里搏斗,直到弹尽粮绝。他瞪着血红的眼睛脱下羊毛衫,嚷着要换一百元筹码时,马仔拍一下他的肩膀,将一千元红包放到了他手上。走吧,马仔说,你那小舅子叫你该回去洗洗睡了。
赌场设在一个表面是台球房的里间,一片乌烟瘴气。一名保安手腕上拴着一条链子,链子的那头拴着一条高大的狼狗,向他吐出猩红的舌头。唐利打了个寒战,头脑总算清醒了一些。我连老婆都没有了,哪来的小舅子?他说,手里却没有放开那个红包。你没有老婆了阿辉总还有舅舅吧?马仔给他点上一支烟说,别硬撑好汉了,给你就拿着。
我不甘心,我要翻本,唐利说,你告诉阿辉他舅舅,就算我借他的,我翻了本就去还他。
马仔笑了。他等的就是这句话。无利不起早,他已经将老板内心深处的想法认真琢磨了一遍,老板告诉过他,按时尚的说法叫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如此,老板凭什么要做这样的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