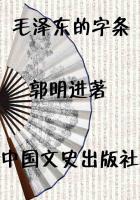第二是要有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创新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原动力。目前各地都提出了要建立创新型社会。然而,没有创业的创新是无本之木,只能是多几篇论文,多几个科技成果奖而已。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创业环境还较差。从对青年人的普及创业教育,到国家政策对创业的支持,以及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度都很不够。
第三是政府角色的变化。在新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政府要及时转变角色,否则很容易好心干坏事,在不知不觉中阻碍了企业的转型。在工业革命中企业将会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一大批传统的企业、传统的行业要被淘汰。有死才有生。而政府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去保护现有的产业和公司。政府会向旧工厂提供补贴,竭力挽回濒临死亡的传统行业。在我国,政府特别有可能会去帮助那些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落后国有企业和近期内能提供很多税收的旧行业,结果反而是人为地阻碍了企业的更新和社会的进步。追求增长速度,热衷于规模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正好与小型化、个体化、多样化的新工业趋势相悖。对于新兴行业,政府习惯于直接选择赢家,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支持他们认为是好的新技术。
教育这一块我们不谈,但现有“中国模式”下的国富民贫、行政垄断和政府角色错位,实际上就是创新型社会的根本阻碍。
首先是政府在做强做大的短视之下,保护了大量专门靠资源和垄断利润吃饭的垄断企业,他们既制约了创新也制约了下游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其次是国富民贫和政府掌握绝大多数市场资源的管理模式,给了政府官员极大的寻租空间,严重窒息了全社会的创业和创新精神。一个最典型的反映是国家公务员考试越来越热,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公务员考试总是人潮汹涌。国家统计局在重庆合川一个普通职位,吸引了9470名考生前来报名,而前几年,最热职位都是在中央一级部门产生,且最多也不过四千多人去争一个岗位。有记者去合川进行了实地走访,结果发现,这个差事算是不折不扣的“苦差”——可能从事各种调查分析,每月下乡数次,而月收入也就2000多元。腾讯网的“今日话题”做了个《万人争当月薪两千公务员的奥秘》专题,发现除了应届毕业生持续热衷于国家公务员考试,已经工作多年的社会人也对公职追求狂热。专题后面搞了个小调查:你认为公务员热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哪个?85%的人选择“有权有油水”,15%的选择“稳定和安全感”。
为什么万人争抢“苦差公务员”,秘密已经昭然若揭!公务员热说明在我国: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们,个人所获取的价值远不如从事分配性劳动的人;政府极大地掌握了社会上绝大多数财富和资源;是政府角色的错位。
一个国资委牢牢保护着央企的垄断地位,与民争利,窒息民间活力。一个发改委牢牢掌握着全国的产业政策和方向,仿佛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掌管着中国企业家的命脉和精神。北大教授周其仁有句话也说得非常精辟,而且通俗易懂。他说:为什么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因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政府没有这个能力知道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所以政府要去指定一个产业发展方向,指定一个技术路线,失败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手让千家万户的企业,让千百万人去探索。探索中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因为你是千千万万的企业和个人在那儿探索,总有一部分人成功,它的成功就能够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成功的道路。
以自由看中国发展
今天的课程,主要分析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历来推崇的所谓“中国模式”的种种弊端,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一度被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捧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奇迹,甚至说用西方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如果它真是什么值得推广的模式,我想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诺贝尔和平奖毫无疑问非中国人莫属了!
我们已经通过分析,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不过是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有可能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并非自始至终都一无是处,但是发展到后来,边际成本越来越高,边际效用越来越低,到今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当然,平心而论,就是中国最普通最底层的老百姓,和改革开放前相比,现在的日子确实要比原来过得好,甚至好得多。这又怎么解释?我的解释很简单:一是即使相对财富减少了,但大家的绝对财富还是大幅度增加了,每个人“自我游刃”的空间还是增大了;二是很多人虽然还不富裕,但是由于社会自由度的增加,比如择业自由和流动自由,每个人的机会还是增加了许多,机会就是预期,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增加,幸福感自然也会增加。
从积极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没有秘密可言,正如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所言,它逃不出两个基本主线:一是市场经济主线使老百姓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二是1990年开始尤其是1998年以来的资本化主线,将“死”的财富、土地、资源和未来收入,通过各种资本化手段调动起来,由此增加了创业资本,创造了就业机会,强化了财富再创造能力。
陈志武先生这一观点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看法以及《资本的秘密》作者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观点互相印证。阿马蒂亚·森认为,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应该从效率标准转向自由标准。德·索托也认为,穷国和穷人之所以穷,不是没有财富,而是其大量土地、房屋等财富由于产权模糊,无法成为可以进入市场流通的“资本”,进而严重影响了交易和财富再生。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有财产而没有“财产性收入”。德·索托领导的秘鲁自由与民主学会被《经济学人》列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智囊团”之一,其个人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
今天的中国,也必须回到“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基点上,以尊重财产自由、人身自由和创造自由为发展的根本依托。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成就来自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来自现代产权和人员流动制度下人和市场的解放。但过去几十年,我们只解放了极小部分的市场和资本,因为占全国土地和房屋三分之二以上的农地、农房没有自由产权,不能进入现代金融体系和自由交易体系,一方面导致农业不断碎片化原子化,另一方面导致边远地区农民土地、房屋财富不断贬值,无法变成进城创业的原始资本。而产权不明晰、不自由,导致乡以上政府机构可以肆意侵犯农民土地和房屋权益。
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这里的自由,就必须从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开始。今天的中国,财产自由、人身自由和民主一样紧迫,这些基础自由和选择领导人的权利、民主决策的权利一样迫切。否则,就像十多年来的乡村民主自治,没有财产自由和人身自由(迁徙自由)奠基,犹似空中楼阁,几十年几乎都在原地踏步,甚至在城市化进程中因为利益越来越巨大,对公民的财产乃至生命的侵犯也越来越恶劣。
告别“中国模式”,融入世界潮流
伴随着高速增长的经济陡然减速,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甚至进入临界点,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与此同时,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双雄并起。“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改革失败论”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公、社会矛盾都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30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中国必须回到政府完全计划主导的道路上。“中国模式论”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御用学者和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相当多的拥趸,在民粹派学者和官员中有相当大的市场,甚至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表面上看,“改革失败论”是对“中国模式论”的否定。但是,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言: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骨子里的本质却是一样的:都是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迷信“国情”和“特色”,不承认普世价值。他们都反对真正的自由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二者的不同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回到“文革”时代,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灭私人企业家,由国有企业统治经济,或许外加一点空想的大众的“直接民主参与”;“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
这两条道路,都是中国的死路!回到计划经济甚至“文革”,只会有共同贫穷而不会有共同富裕,而且,那种贫穷还同时意味着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彻底消失。因为那样的制度和环境,容不得有任何不满与反抗。固守“中国模式论”,只会导致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阶层仇恨和矛盾加剧,人人都没有安全感,使整个中国在环境、道德与人心破坏中人人自危。
未来中国,只有真正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从价值观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制度安排上全面与世界接轨,中国才有真正的崛起和未来。
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要崛起,中国模式不能崛起。现在我们政府一年花的钱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花的钱。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中国如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维持“低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中国应该改变,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主张。1949年以前共产党把那时的国有资产叫“官僚资本”,而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时的“国进民退”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所以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专利。
告别“中国模式”,融入世界潮流,中国的改革前景依然巨大,因为有很多“后发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迫切需要通过制度改革解放未释放的社会能量。过去三十多年,以政府为主体尚且释放了如此巨大的能量,以公司和个人为主体释放的能量将会更大。
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世界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因制度的不同而不同。规律即真理,任何个人、党派、团体和制度,都不可能改变规律和真理本身。只要是人类的一分子,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什么特殊性,充其量只是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已。
中国应该排除一切意识形态干扰,什么东方西方,什么姓资姓社,什么国有私有,一切都要落实到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与进步的制度建设上。只有去意识形态化,才能真正深入地研究规律和对策,从中央到地方,告别短期政绩思维,抛弃意识形态框框,认真研究和分析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样做,才能居安思危,改革才能深入彻底切中要害,国家未来也才会更加繁荣兴旺安定和谐。
2012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