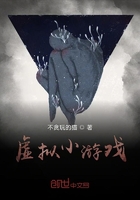在秦历717年的这个春天,孙铿一行人很享受的度过了他们难得的一段假期。不过对于车善行这位大器晚成的将军来说,这个春天给他的回忆,是永无休止的地狱级训练。
石湖关要塞指挥部后院的草坪上,春日的阳光透过云层,均匀的洒在人们的脸上。车善行轻轻捋着胡子,脸色铁青的望着面前一条狭窄的道路。这条路并不算长,只有不过百十米的距离。但这着实是他有生以来从未走过的险路。
道路上遍布着尖锐的铁蒺藜,能轻易刺穿脚板的尖角直指着天空,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慑人的寒光;齐腰高的地方,高低不平的横置着几根锋利的链条,一旦被碰上,就是一个血肉横飞的下场;更加让人惊心的不是这条看上去注定要让人流血的道路,草坪上站着几个持枪士兵,他们被蒙上了双眼,双手举枪做预备射击的姿势。枪里压满了子弹,在一旁带队的军官高高举起右手,等待着薛汉臣下达命令。
“这样真的不会出问题吗?长官。”在旁驻足的少年营军官忍不住多问了一句,但没人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薛汉臣在他身后踱了几步,阴声笑道:“看上去你有些信心不足啊,新兵。怕不怕?”
“不怕。”经过多日训练,车善行总算了解了这支军队的一些行事风格。皱着眉头喊道。
“看上去你有些信心不足啊。”薛汉臣道:“要不要先来一点热身运动?”说着,他指向旁边的几个盛满冰水的铁桶。
车善行随着他的手指看去,脸色苍白的摇了摇头。“我已经准备好了。”
“怕不怕?”薛汉臣的喊声突如其来的在他身后响起来。
几乎下意识的,车善行大吼了起来。“不怕。”
“上吧!”薛汉臣掏出腰间佩挂的手枪,对着地面扣动了扳机。清脆的枪响让车善行浑身猛地僵住。
他握紧了双拳,猛地一撩珍若性命的胡须。双目赤红的望向终点上的一面赤旗。
“杀杀杀!”年逾四十的精壮汉子咆哮了一声,埋头向前冲去。
“预备——放!”带队军官放下手臂,转头又低声补充了一句:“枪口抬高五公分。”
车善行赤着脚趟过密集的铁蒺藜阵,险而又险的仰天一个铁板桥躲过了一条铁链条。时光似乎定格,他看见了自己胡须的梢尖被铁链条割断。散碎的胡茬随风飘洒,他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幕。就在他的思绪还停留在上一根铁链条时,身体已经躲过了连续两条横置的铁条。一个侧身让过了滚过来的一个铁桶,就在这个时候,密集而整齐的枪声突兀的响了起来。
他下意识的弯腰抱头,一时不察,双臂已经被铁条撕开,鲜血迸溅出来。钻心的疼痛让他的感觉一瞬间更加敏锐。看上去荆棘满地无处下脚的道路在脚下如履平地。
他如同一头出笼的猛虎,快速狂奔起来。薛汉臣目光一肃,侧身抬手,连连扣动了扳机。将枪膛里的子弹发射一空。子弹准确的击中了旗杆,随着春风的拂动,向后飘去。道路的终点,摆着一盆炙热燃烧的火焰。
车善行几乎凭着多年狩猎的本能一鼓作气的向前奔行,眼前的赤旗触手可及。但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他的幻想,那面旗帜失去了凭仗,眼看就要落进火盆之中。
车善行发出一声怒吼,快速抢上几步,忍着炙热的高温,将那面赤旗紧紧揽在手里。火焰扑面而来,燎焦了他的须发。他浑然不觉,将那旗子高举起来。站定回身,骄傲的望着薛汉臣。如同一尊古铜色的铁塔。
薛汉臣背着手,沉寂了几秒钟之后。脸色终于松动,单薄的嘴唇轻轻吐出两个字。“不错。”
车善行喘着粗气,烧焦了的胡须随着他的动作片片碎落。回望着这条几乎是绝路一般的道路,他有点不敢相信。双臂传来的疼痛,让他真实的感觉到这不是一场随时会醒来的噩梦。木愣愣的站在道路的另一端,他望着眼前那个一手引领着他走上这条道路的年轻男人。忽然伤感的叹了口气。这种情感,在他过往的人生中,极其稀少的出现在他的心里。
“你怎么看?”林光一忽然转头,望着身边的司全。行动队在一天前已经抵达了石湖关,不知不觉在孙铿周围支起了一面隐秘的屏障。
“薛侍从官找错了方向。这个家伙明显身体素质不错。”司全的独眼堪称犀利,他忍不住讥诮道:“我看这个新兵蛋子应该交给一个普通的教官就行了。他天生就有战争的嗅觉,应该学的是我们军人的礼仪和规矩。”
“看来老白给咱们的头儿最后留下的礼物是一块没被雕琢过得绝世珍宝。”林光一叹息道:“也许我应该找薛汉臣谈谈了。”
翌日。车善行从睡梦中醒来。没有想象中的冰水热身行动,更没有薛长官的弹雨问候。他就这么自然的,平静的睁开了眼睛。
一瞬间,他都以为一切都不过是一场荒诞的梦,他从梦中醒来了而已。可是打量着手臂上被包扎的严严实实的伤口,以及光秃秃的下巴。他马上回味过来,这并不是梦。他真实的,完全的走进了一个铁与血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大门口上用铁和血写着两个字“军人”。
“醒了?”耳边传来一个熟悉而讥诮的声音。
他猛地坐起身来,惊疑不定的望着薛汉臣。二人间里,薛汉臣随意的坐着,手里翻动着一本崭新的书。
“把胡子烧掉以后,你看上去比老林年轻多了。”薛汉臣嘲讽了一句,正色道:“识字吗?”
车善行茫然摇了摇头。
薛汉臣痛苦的捂住了自己的脑门,将手里的书丢在他的面前。“给你三天时间,不管用什么办法,把这本书背下来。”
车善行感觉自己的脑袋骤然变大了。他为难的望着薛汉臣道:“我不识字。”
“先圣皇帝在上。在他治下七百余年的大秦国内,居然还有不识字的奇特存在。”薛汉臣嘲弄道:“你真是一个绝世珍宝。我碰上你真的三生有幸。”
车善行点头,望着那本书只感觉这个早晨比之前度过的若干个早晨都要糟糕。“糟糕透了。”他忍不住咕哝了一句。
“确实。”薛汉臣深有同感的点了点头。“新兵,我想我们遇上大麻烦了。”
两天后,孙铿办公室。
“最近后院消停了不少。”孙铿打开了窗,让略有些凉意的风吹进房间里。
“是啊。”林光一漫不经心道:“薛汉臣最近改变了调教方向,他正在让老车识字。”
“识字?”孙铿吃了一惊,“我的侍从官是个文盲吗?”
“也许现在不是了。”林光一合上书本,抬起头道:“四十岁再学文化知识会不会太晚了点儿?”
“只要有学习的念头,八十岁的小学生我都见过。”孙铿端起茶杯,示意谷雨给自己续上一杯茶水。
“那你会收获一个四十岁的中学生。”林光一开着玩笑道:“薛汉臣只能教他到那儿了。”
“那也没关系。”孙铿淡淡道:“只要能清楚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就可以了。”
“只要不是哑巴,大概都能做到吧?”谷雨插了一句嘴,三人同时笑了起来。
车善行的内心世界里,除了数不清的铁蒺藜,时不时闪出来能把人拦腰截断的铁链条,四处横飞的子弹之外,又多了些东西。这些东西他以前见过,却从没有动过使用它们的念头。那种厚厚的,写满了方块黑字的物品叫做书籍;那种细长的,能够蘸满墨水然后写出文字的物品叫做笔。原来军人的世界并不是只有那些枪炮武器,还有数不清的书籍,让他感觉到恐惧的海量知识他没有了解到。穷尽一生,能了解它们的皮毛吗?对此他一点信心都没有,而他的领路人,自然也是没有的。
“混账!这个字你又写错了。”薛汉臣一掌拍在桌案上,墨水瓶跳了起来,墨汁溅到两个人的脸上。“老车,今天这是第几次了?咱能不能不犯错了?”
“抱歉……”车善行放下笔,擦掉脸上的墨汁。看着薛汉臣白净的脸上星星点点的墨汁,形同醒目的麻子。想笑又不敢笑,只好撕了一张本子纸递过去。
“我不想听抱歉。”薛汉臣摆了摆手,努力调匀呼吸。“我们继续吧。不要让我再处罚你了。你看看外面的那条路,已经被我们跑出凹地来了。”
“跟这相比,我宁愿跑路。”车善行小声心虚的咕哝了一句。
“跑路?好啊。”薛汉臣指了指旁边已经收拾好了的行囊。几根没地方揣的虎鞭尖端露在外面。“打包走人,车票我帮你买。马上!”
车善行吞咽了一口唾沫,猛烈摇头道:“还是算了……”
深夜,薛汉臣小心的拧亮了桌前的油灯。侧身望着躺在床上沉沉睡着的车善行。中年大汉咕哝了几句,翻了个身。被子从身上掉了下来。
“队列在行进过程中……及时派出侦查部队对两翼……”车善行的梦呓传进薛汉臣的耳朵里。薛汉臣微笑了一下,下床捡起被子,轻轻盖在他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