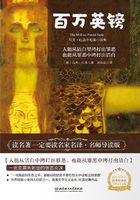端阳这一次上城,不但为了送鸭子,还为了枪而来。自从在小何那里得知武工队员的枪都是得之于敌人之手,端阳就老是想起那支在日本巡逻兵屁股上晃来晃去的“二十响”。这支德国造驳壳枪好多次进入了端阳的梦境。梦中的夺枪过程大同小异——先是把那个矮鬼子引进小巷,然后端阳吱溜一下跳上屋面,等那鬼子兵东张西望时,从屋檐上像侠客那样来个“倒挂金钩”,一手就从鬼子的枪套里抽出了二十响……
大福师把端阳接进城之后,就被宪兵司令部叫去了。现在,只要有比较重要的客人来,肥田一郎就会把大福师叫去做鸭子菜。
大福师走后,端阳就想去酱园大本营那里找胡顺他们,不想半路上就遇上了胡顺和大米。
那个地方叫小庙场,是一片广场。端阳看见广场一角围了个人圈子,里头传出来当当的小锣声和曼声曼调的吆喝声,就想:是不是大米在耍猴呢?仔细一辨那吆喝——果然是大米的破嗓子!
端阳并不挤到前排去,就在人群里混着,一心想看看大米和胡顺是怎么耍猴挣钱的。
大米上身赤膊,下身穿一条皱巴巴的灯笼裤,黑色的腰带蛮宽,用劲地把腰收束得很细。把腰带收这么紧,是想显出上身的强壮,可大米的上身实在不争气,看上去就是皮包着骨头的可怜样子,那肋骨一棱一棱的就像搓衣板。大米左手提巴掌大一面小锣,右手握一根小木棍儿,说一句话就“当”一下小锣:“嗨,嗨,黄毛黄毛,大米要你豁虎跳来!黄毛黄毛,跳来!”
那猴子脖子里有个皮项圈,连着一根细链子,紧绷绷地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红布短裤,看上去也是可怜得要命。它熟练地翻了几个跟斗,就再不肯翻了,眼睛眨巴眨巴地等着赏它吃局。
大米手里没空,负责赏吃的是站在一旁的胡顺。
胡顺只是个客串的外行,穿的也是平时衣裳,只是手里捉着个小布袋子,不时地从里头掏出什么东西来抛给黄毛解馋。
“嗨嗨,黄毛黄毛,大米要你倒立来!大米要你倒立来……”
黄毛就来个倒立,从红裤子里伸出来的尾巴晃来晃去的,大概是在平衡身体。大米当当地敲着小锣,催猴子沿人圈子走路。还没走满一圈,黄毛贪馋的目光又盯上了胡顺手里的小布袋子。
这一次,胡顺抛给猴子的是一把木制的玩具手枪。黄毛接住了手枪,有滋有味地舔着枪管,大概那上头抹了糖吧。
大米装出点害怕,说:“喂喂,你老总小心手枪走火哎!”引得观众一阵哄笑。
舔完了枪管,黄毛熟练地把手枪插在腰间,坐在一只小木箱子上,优哉游哉跷起了二郎腿,任大米唤它叫它催它骂它,就是不肯动了。
大米抹着额上的汗,说:“哎呀喂,看看这家伙,手上有了枪就成个人物了。都说‘猴子带帽子,像煞有架子’,我说不对,我说猴子有枪支,龟孙变老子……”
大家都笑起来。
大米从裤袋里挖出来一个香烟头,走近去谦恭地拍拍黄毛肩膀。黄毛不客气,夺过烟头就叼在了嘴上,还用鼻子哼哼着向大米示意为它点烟。大米就去向观众借来一盒火柴,为黄毛点上了香烟。黄毛还真的能吸烟,昂起头从朝天鼻子里向外喷烟,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黄毛更加得意,叼上香烟昂起脑袋背起前爪,像个大人物那样踱起方步来。
大米感叹道:“瞧这位,有了枪就成大爷了。瞧吧,多威风哎……”
不想,大米这番话惹怒了人群里的两个大汉。黑脸汉飞起一脚把黄毛踢出一丈多远,另一个穿黑香云纱的毛胡子一巴掌向大米扇过来。大米还算机灵,一闪身没让巴掌落在脸上,但还是着在了脖子上,踉跄几步倒在了地上。
毛胡子不罢休,解开几颗纽扣,把褂子敞了,露出来腰间的手枪,冷笑着一步步向大米逼来。
胡顺扶起大米,挺身拦在毛胡子面前,说:“你这是干啥?”
毛胡子说:“不是说有枪就是爷吗?我就是你爷!让开,让我扇他三个大巴掌……”话没完,提腿就把胡顺踢倒在地。胡顺抱着腿,痛得在地上打滚。
端阳在人群里一时挤不过来,大声喊:“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毛胡子猛回头:“谁喊警察?告诉你,爷我不怕警察,倒是警察怕爷!”
围观的群众冲着毛胡子起哄,拥上来,把胡顺和大米挡在了身后。
有人喊:“欺负小孩子,算个屁!还爷呢!有本事打小鬼子去!”
有人喊:“这位是土匪还是汉奸啊!”
毛胡子对起哄的人群说:“你问爷是谁,爷是忠义救国军,老子打过鬼子……”
有人接口说:“老子现在投了鬼子!认鬼子当爹啦!”
人群哄笑起来。
面对群情汹汹,那个黑脸汉子想找个台阶走人,一把抓住了猴子的链条,说:“我一枪崩了这畜生!”黄毛知道这不好玩,急了,尖叫着奋力向黑脸汉子扑去。黑脸没料到这个,闪身躲过,仓促间松了手里的链条。黄毛连着几个纵跃就通过一根电线杆上了屋面,在那里冲着两个强人尖叫抗议。
毛胡子掏出手枪,扬手就给了黄毛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只把瓦头击个粉碎。
黄毛一看不妙,又是几个纵跃,上了屋脊。毛胡子又放了一枪。黄毛尖叫一声消失在屋脊那边,也不知中了枪没有。
正混乱间,只听得两声难听的汽车刹车声,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在广场那头的路口停了下来。卡车上站了一些穿屎黄色军装的兵,吉普车里跳出个军官模样的人,问:“哪儿打枪?哪儿打枪!”
路边有人说:“两个忠救军,在那边打死了一只猴子。”
毛胡子和黑脸汉远远看见车子,别过身子就走,钻进小巷子不见了。
那个军官回身对吉普车里的人说:“司令,说是我们的弟兄,打猴呢。”
吉普车里的胡传魁说:“呸,在这里打猎啊。走吧。”
那军官跳上车。两辆车耀武扬威地穿过广场扬长而去。
如果胡传魁这时下车,说不定他就和儿子见上面了。没错,胡顺就是胡传魁的儿子。胡顺只知道父亲叫胡传魁,在江南拉部队打鬼子,他就是到江南来找父亲的。胡顺怎么知道父亲改叫胡传魁了呢?胡顺怎么知道父亲已经投降当汉奸了呢?
端阳和大米想把胡顺扶起来,可胡顺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他抱着右膝,脸色煞白,额上的汗黄豆一般大。他咬着牙,不肯哼出声来。
端阳掰开胡顺的手,看看他膝盖上并无伤口,就紧张了——没有伤口疼成这样,说不定是伤到骨头了。来关心胡顺的几个大人也有了这样的判断,主张马上去找医生。
一个穿黄马甲的青年挤上来说:“小兄弟,我送你们去丁先生那里,丁先生医术好,心肠好,我用车子送你们去。”原来他是个黄包车夫。
一旁的大米为难了,怯怯地说:“看郎中,我们没钱啊。”他说这话时,嘴角还在流血,看着叫人心疼。
黄马甲青年说:“丁医生是个大好人,他会帮你们的。小兄弟,这事不能拖的,走吧。”
端阳说:“快走!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不少人掏出些钞票来,塞到胡顺手里。胡顺本来忍着剧痛,不吭声,不流泪,这些伸出来的手倒把他的眼泪引出来了。
端阳说:“大米,你要紧吗?”
大米说:“我没事,我嘴唇破了。”
端阳说:“我送胡顺去医院,你收好东西先回去。还有黄毛呢。”
大米牵挂着黄毛,答应了,说:“胡顺,你就回来,啊。”他的眼圈也红了。
黄马甲青年把胡顺抱上了黄包车,又让端阳上车。端阳不肯加重他的负担,扶着车跟着跑。
驶过两条街,黄包车就到了引线街。
黄马甲说:“瞧,前头就是丁凡诊所!”
“丁凡诊所”的牌子挂在一个整洁的石库门上头,白底蓝字,还有一个鲜红的十字。石库门敞开着。一棵姿态秀气的乔木女贞树,一架疏疏朗朗的紫藤和几个花坛,使小院子绿意葱茏。地是用青砖侧铺的,砖缝里长出些小草来,更使小院子宁静而优雅。紫藤掩映着一幢带有走廊的白色平房。走廊上有几张白色的礼拜凳。礼拜凳上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人,大概是候诊的病人吧。或是受了宁静环境的影响,这里的人动作都是慢慢的,说话都是轻轻的。黄包车径直进了小院子,停在女贞树下。黄马甲青年和端阳合力扶着胡顺下了车。立马就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女护士迎上来接应。
黄马甲对护士说:“这孩子怕是骨折了,疼得厉害。丁医生在吧?”
护士说:“丁先生在诊室里呢,请跟我来。”就领着他们经过走廊,绕到房子的东侧,推开了一扇白色的门。里头原来是一个小小的治疗室,一张铺着白被单的单人床放在屋子中央,四周还有些椅子和药柜子什么的。
护士让胡顺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说:“你们稍等,我去叫丁医生。”说着就消失在一扇毛玻璃门后。这扇门是连通着诊室的。
护士很快回来了,她后头跟着一位穿白大褂、戴眼镜的中年人。
黄马甲青年说:“丁医生,这孩子被忠救军打了,伤了腿,疼得不得了。你给看看吧。”
丁医生说:“好,我看看。”就蹲下来为胡顺检查伤处。他检查得很仔细,动作很轻灵,不时轻声问胡顺:“这里疼吗?这儿疼吗?是怎样的疼,是针刺一样的疼还是火烧似的,还是被捩着般的疼……”
女护士去端了一只白脸盆来,从里头绞起一块毛巾,来给胡顺擦脸。
丁医生检查完了,站起来说:“不要紧,骨头没伤,是脱臼了。”
黄马甲青年松了口气:“谢天谢地,骨头没伤就好办。”
丁医生说:“是被人踹的吧,这一脚踹得好狠。”
黄马甲说:“还有谁,是忠救军,那帮龟孙子投了鬼子,就跑到城里来学着鬼子欺侮我们老百姓,不是人呐!”
丁医生对胡顺说:“孩子,你找对人了。我是西医,还学过中医,你这膝盖只要用我们中医的办法来治。来,我们换个地方动手术。”
胡顺听说要动手术,挺紧张的:“要动手术啊!”
丁医生笑了,说:“别怕,这个小小的手术要到后院里去做。”回头吩咐护士道,“你重新打盆清水送到后院来。”指挥黄马甲和端阳把胡顺连同那张椅子一同转移到了后院。
后院也是侧铺的青砖,没有树,只靠墙处有疏疏的一丛竹子。
丁医生让把椅子放在小院中央,叫胡顺脱了小褂子和长裤,命黄马甲和端阳一边一个按住了胡顺的身体,说是怕动手术时病人乱动。
丁医生右手握住胡顺伤腿的脚踝,左手在膝盖那儿轻轻摩挲。
这时的胡顺紧张得要命,端阳感到他在发抖呢。
丁医生见护士端着脸盆走来,说:“看,紧张得都流汗了,先擦把脸吧。”
胡顺听说让他擦脸,知道还不会动手术,暂时松了一口气。不料,这正是丁医生的声东击西之计。那小护士也是老吃老做的,配合得默契着呢,走近来时,突然朝胡顺倾盆一泼。胡顺猝不及防,猛一激灵,一时全忘记了他的膝盖。就在这一瞬间,丁医生握着脚踝的手往下一拉,又带点旋地向上一搡;另一只手也做了一个配合动作……
胡顺觉得膝盖那儿“咯”地响了一下。
丁医生朗声道:“手术完毕!”
胡顺试着动动伤腿,还有点儿疼,但已不是刚才那样的剧痛了。
丁医生说:“看,这个手术应当到院子里来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