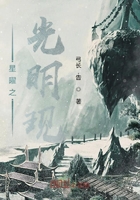“还念大学呀!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又在轰轰烈烈地反击右倾翻案风了?高考制度早流产了。况且我妈妈又不知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婷婷的脸上,刚才那会儿的看似风趣的神情,一忽儿不见’代之而见的是一副忧郁的怨愤来。
“哦,听建平说过,你妈妈去年已经重新出来工作不是?”夏华瞧着婷婷的眼睛,不解地问。
“是的。可去年出来后,也一直没给她什么实际工作做,闲搁着。今年四月的运动头上又给弄走了。这一次比先前更糟,连面都不让我们母女见了。我找过好几次,都没找着,听说已不再干校,就是不知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婷婷说到这,眼圈红了,眼眶里涌出了泪花。
夏华同林建平是高中的同学,对于林建平家里的事,多少知道一些。林建平与婷婷是同父异母兄妹,林建平的父亲同他的母亲离异后,再娶婷婷的母亲,而后生下婷婷。但这个重新建立的家庭,也一直矛盾重重,主要的是林建平同后母水火不能相容。据传闻,建平的父亲离异建平的母亲,有着婷婷的母亲的原因。建平自小起就一直对后母心存芥蒂,持不友好态度,从来没叫过后母一声“妈”。背着她,都是直呼其名——“舒芸”。而后母对他,也是越来越冷淡。及至建平大了。这种敌对情势越发激烈。林建平上高中以后,干脆从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学校的学生寝室。若没有非去不可的事情,绝不跨进家门一步。但有一点却叫人费解,后母所生的妹妹林婷却与林建平相处得和睦亲善。夏华虽然从没见过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每每听建平提及他这个妹妹时,他都是亲昵地称之“我的妹妹婷婷。”
林建平对父亲也很反感,他怨恨父亲离异了他的母亲,使他失去了应有的母爱和家庭温暖。父亲对他的关切。随着岁月的推移,也渐次少了。父子之间唯一能维系的,只是作父亲的尽义务,每月付给儿子一定的学习和生活费资,作儿子的也只是看成天经地义的每月支取这笔费资。所以,当“文革”中,林父不堪忍受屈辱,而自己结束了生命之时。林建平连看都没去看一看。高中毕业,他随着人们在乱哄哄的社会上疯狂了一阵子。此时家里也已和他断绝了仅有的一点经济关系,恰逢到处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浪,他索性自动申请同夏华等十六个同学结伴南下,去了边远林区插队落户。
当时一起上山的十六个同学中,是九男七女。在大山里受过一段煎熬之后,其中便有十三个通过不同的渠道或下山或返城走了。至如今,还留在大山里的便只有夏华、林建平和肖嫒嫒三个人了。媛嫒回不了城,是因为那个与她有着抚养关系的外公被打成反动医学权威还没有得到“解放”。建平呢,父亲是“走资派”加“叛徒”,且还在运动中对抗运动,“自绝于人民”,像他这类的顽固派的狗崽子,是不可能让他回城或招工招干,甚至参军或推荐上大学什么的。所以,他是一时走不了的。其实,他也没想过要马上走,一则城里没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再则还有个特别的原因,那是他与肖嫒嫒是一对恋人。嫒嫒回不了城,他哪能撇下她下山走掉。再说到夏华来。夏华则更是没有回城或通过其他的途径下山走掉的希望。母亲的来历问题,一直是公安部门专门研究的课题。母亲在世时,任凭公安部门用什么办法查询,母亲总是守口如瓶,而母亲又一直是安份守己,循规蹈距,从无违法之迹象,公安部门后来也就放松了对她的查究,没当回大事了。但是在户籍管理的档案里,母亲的履历表中好几个栏目,一直是用“?”写着。对作为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的儿子。在这“左”得出奇的“文革”时期。一经逐出城,哪还能再将他收回去,或者也让他通过其他途径下山呢?大概人们在想,这种人最好的是把他抛进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中,让他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的就那么与野兽野物相伴为邻。对于这一层的道理,不知夏华意识到了没有。不过有一点倒是完全可以看得出。在母亲去世后的这段时日,夏华已是打定了主意,一辈子就在那个深山老林的九峰山生养死葬好了。
这些亦即是说,夏华、林建平和肖媛嫒这三个在命运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人,都因为各自不能回城或走下山的原由,今后说不准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在那九峰山当“山民”。现令夏华诧异的是,好端端的在城市里念书的婷婷。竟然也赶来凑这份热闹。
夏华想到这里,心里不由得涌出一种莫名的滋味来。这滋味,一半是感伤于婷婷命运的悲哀,一半也便是由此及彼,联想到自己这一生的落寞,但他天生是一个不愿太多地表露心灵情感的人,因而,听过婷婷一席充满哀怨的诉说,他也不想以什么形式去安慰,只是淡淡地问道:
“那你来之前,写了信告诉建平吗?”
“没”。婷婷低垂眼帘。脸上的那种感伤和哀怨似乎又增加了几分,她抑郁地说,“这三年中他只在前两年断断续续地写过几封信给我,今年我还没见过他只言片语,反正他跟我妈一直相处不好,家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所以,我也懒得写给他。”
“哦!”夏华似乎对此有点惊诧,不过在这么“哦”了一声之后,却没再说什么来着,关于建平跟家里的事。他不想在婷婷面前发太多的议论。这不仅缘于他的冷峻寡言的性格,还有着另外一层缘由。他所想的是,这是别人的家事,自有别人的道理,无须他来说三道四。
婷婷见刚谈了几句话,夏华又眯起了眼睛,不言不语,那样子又像自顾自进入了另一个什么情境之中去了。自然也就索然无味。于是。她收起了话尾,也半合起双眼,仰靠在椅背上,学着夏华的样子,也假寐起来。但没一会,又像想起了什么来着,睁开眼,瞟了夏华一眼说:
“夏华,我倒忘了问你,那个桠湾窝是个什么样儿的地方?”
夏华见问,便也张开眼帘,笑了笑,然后说:
“深山老林,方圆几十里难有十户山民。要进山。下了火车,还需坐三、四个钟头的汽车。然后下汽车,然后再爬呀爬、攀呀攀的近三十里,就在那‘白云生处’见着了我们那群‘半拉子山民’的‘人家’。那地方,便是了桠弯窝。”
“哟,看不出来呀,你还蛮有些浪漫情调的啰?”夏华这一串很有点儿诙谐的话语,想不到一下子竟把个本来心情抑郁的婷婷逗乐了,她“咯咯咯”地抿嘴笑了起来。她笑着又追问道:
“那何谓之‘半拉子山民’呀?”
夏华又似乎受到了婷婷的情绪感染,也跟着笑了起来。他笑着回答婷婷说:
“这所谓的‘半拉子山民’是我们后来自己叫开的,意即并非土生土长的,世代相传的山民。”
“那么,我也即将成为一个‘半拉子山民’吧!”
“但愿你的山民生活不会太长吧!”
“唉,一切听天由命吧!”婷婷收敛起脸上的笑容,又回到了抑郁之中。
“你相信命?”夏华将刚刚投向车窗外那朦胧夜色中的目光收了回来,有些好奇地盯着抑郁的婷婷。
“这其实我也说不清。不过,我似乎觉到,我们活在世上,谁也逃不脱一种说不出所以然的什么力量摆布操纵一样。夏华,你说是吗?”婷婷也瞧着夏华的眼睛认真地说道。
“你问我么?”夏华苦笑一声,摇了摇头说,“我跟你一样,说不清。”
谈到这里,两人又相对无言了,陷入短暂的沉默。
短暂的沉默之后,仍是婷婷率先提起了话头:
“夏华,你这是回城探亲的吧?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建平至少还有一个你这样的妹妹,可我。我在这个世界却什么也没有了!”婷婷这句话无意中又勾起了夏华无尽的痛楚,把他重新拉扯到母死家丧的悲哀之中。他沉重地叹了口气。
“哦。真对不起,我让你伤心了。看来你也是个苦命人!”婷婷见此时夏华表现出如此的抑郁痛楚。说着话儿的当儿。似乎眼圈儿都潮润了,便赶忙赔个不是。
然而,夏华此时并没有怪罪她的意思,反而一改抑郁。瞧着她笑了笑劝慰道:“别太多心,我没有怪罪你的意思。”
婷婷见状,也还他一个笑靥,但却在心里想:这夏华表面看似冷峻无情,想不到其内心却是极丰富极细腻的,说不准他心中还有好深好深的苦情呢!想到这里,她不禁又细声地问道:
“夏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点关于你的情况?”
“以后再说吧。看,已经下半夜了,我们还是养养神吧,明天下车后,上山还要很多气力呢!”
说罢,又眯上了眼帘,斜靠在椅背上,养起神来。
婷婷看夏华又这样了。只好知趣地不问他了,整了整自己的衣襟,同时心想,夏华说的也是,是该养养神,准备明天跟他爬大山的。于是,她也将头靠在椅背垫,合上了双眼。而此时,才过一会儿,夏华却又将眼睛打开了。他瞧了一眼似已困着了的婷婷。心里忽然涌起了一种说不出是为什么的感觉。他想,他有生以来从未与人作如此长时间的闲聊,今夜在这列车上,怎的会跟婷婷谈了这么久,谈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