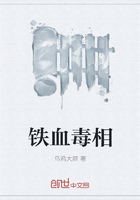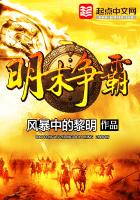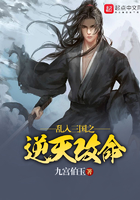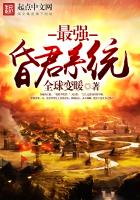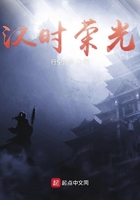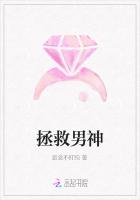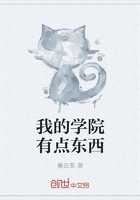司马光这时早已忘记先前的言论,转而指责免役法:现在我听说要将州县的各种服差役之人遣散,让他们出免役钱,转而雇人来干活。甚至连单丁、女户、出家之人都有份,如果真的施行起来,比起青苗法,为害犹胜。为什么呢?上等户向来是轮换着来服役,既然是轮换,肯定有休息的时候,现在让他们每年都要出免役钱,对比起来,就是剥夺他们休息的权利。下等户及单丁、女户,从来都是不需要服役的,现在却也要他们出钱,真是连孤贫鳏寡之人都不放过。如果收上来的钱少了,就不足以雇人;如果钱收得多,则是“重敛于民”。雇人不足的话,就会耽误公事;重敛于民,则众心怨恨。宁波的王安石纪念馆自古以来,都是由人民来承担徭役,现在进行了改革,并没有看到什么好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司马光所指责的后一种情况,在免役法实行之初,是存在的,后来根据实际情况,下等户、单丁户等都不需要缴纳助役钱了。
司马光接着说:力气,是人与生俱来的;谷帛,可以靠耕种、植桑而得;至于钱,是由政府来铸造的,民间不得私铸。现在国家立法,却只认钱了。遇上丰年,人们就要贱卖谷物来凑钱。灾荒之年,就需要砍树杀牛,甚至卖田来凑钱,“民何以为生乎”?此法若行,则富民还稍微能周转过来,贫民则会越来越穷困。
对照之前他所说的“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真不知道司马光听没听过“自相矛盾”这个词。
苏轼也不甘落后,说道:自古就用乡民来服差役,就像吃饭必食五谷,穿衣必使桑麻,渡河必用船桨,行走必驱牛马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虽然其间有时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却非常理。如今听说江浙一带的郡县雇人来做事,而且想把这办法推行于天下,是万万行不通的……士大夫们为了国家的需要,舍弃亲朋、不顾祖坟,而四处飘荡来做官,在为国效力之余自然也想要取乐,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把这些人逼苦了,“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天下之盛观”。
看来司马光和苏轼并不傻,他们不是没有看到免役法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好处,不是没有看到免役法“行于诸路,人皆便之”,“百姓皆以免役为喜”,只是他们更为关心的是自身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也就是前面说到的抑兼并作用。
当然,免役法所起到的抑制兼并的作用是有限的,但仅就保守派们的猛烈攻击来看,还是收到一定成效的。
10.沿用了八百多年的保甲法
1070年12月,保甲法出台。王临川全集那时的京城开封,不知为啥,治安不是很好,老百姓经常一大早起来,发现家里已被盗贼翻了个遍,值钱点的东西基本上都被搜刮走了。天子脚下的开封如此,就更别提其他地方了。
王安石认为,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是民众太散了,没有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大家不能互相照应。如果能够把大家按距离远近,结为大小诸保,加以约束管理。那么,富裕的人晚上可以放心睡觉不怕被盗,没钱的人也不用担心被打。社会治安将明显好转。
结合赵子几的想法,王安石又跟另外几个人商量研讨了一下,得到神宗首肯后,1070年12月,《畿县保甲条例》问世,先看看条例是怎么说的。
“十家为一保”,民主推选一名“有材干心力”的“主户”(土著的原有住户,与“客户”相对)为保长。
五保为一大保,民主推选一位大保长,大保长就是保长的直接上级。
十大保为一都保,领导人有两位,称为都副保正。北宋开封城平面示意图哪些人应该入保呢?别急,有详细说明,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话,要选一个人为保丁;如果家里人丁不旺,只有一个成年男子,或者是五保户什么的,可以就近附保;如果家里有武艺超群的,比如能像李寻欢一样使得一手飞刀的人,也要入保,并且担起责任。
保丁们除了大炮火枪不能置备外,其余像弓箭之类的,都可以置备,农闲时可以习学武艺。
保成立之后,主要负责的事情是治安方面的。“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在本保内往来巡逻。一旦遇到盗贼,大家就使劲敲锣打鼓,并立即报告大保长,当然,那时没有电话,就只能撒开脚丫子跑了。保内的人都起来捉贼,能操家伙的操家伙,没法操家伙的就敲碗敲饭盆都行,总之大家齐心合力把贼给抓住就OK。万一那个贼会点轻功什么的,跑出了本保的地界,同志们也应一边击鼓一边追,直到将那天杀的贼子抓住。
抓住盗贼不是白抓,官府会赏钱3000,若是比较轻微的,就赏1000,这个赏钱呢,就由罪犯家里来承担。如果罪犯家里委实穷得厉害,那就饶他一回,可以取保释放。
同保内如有杀人放火、偷盗抢劫、传习妖教的人,你知道却不报官的话,是要受几天牢狱之苦的。如果保内有盗贼停留了3天以上,你却没发觉,是要追究失察之罪的。
保内如果有户逃移死绝,或者外来人户入保,都需要及时上报。元祐通宝,苏轼手书平时眼睛要擦亮点,看到形迹可疑的外来人,可以报送官府。
为了方便管理,需要做户口本,把每户的详细信息都登记好。
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保甲最初的目的是稳定社会治安。同时,还起到了人口普查的作用,使得国家能比较准确地掌握居民的信息。
当然,王安石还有更为长远的考虑,那就是用征兵制代替募兵制。
自宋太祖赵匡胤以来,北宋实行的是募兵制,当兵是一种职业。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有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他觉得那些整天在社会上吊儿郎当、游手好闲的人,如果都招到军队里面,社会治安自然就会好了,所以,北宋的军队里就大量地充斥着这样的人。
就这样,北宋军队的规模跟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王安石变法之前,军队人数已经达到了140万。没有对比,自然就对这140万没有什么概念。北宋时期的人口,据考证约为1亿。现在中国的人口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军队规模约为230万。如此的对比,就应该明白这140万对于当时的北宋意味着什么了。
而且,如此招募而来的兵,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应该说除了打仗,其他的都挺在行。因是募兵制,所以,国家财政还需要为了宋太祖这一与众不同的想法而买单,自然是有些吃紧。刚开始是吃紧,到后来,就有些玩不转了。王安石《半山春晚即事》王安石就是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减轻财政负担,想要实行征兵制。王安石对此是有着长远的计划的,他认为,减少兵员是当务之急,却又不能操之过急,因为若把现在混迹于军中的那些地痞流氓一下子遣散回家,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是不可能在家里老老实实耕田的,那对于社会的稳定,无疑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所以,兵是要裁的,但要一步一步来。为了全面实行征兵制,先应该对保丁加以训练,让他们能够与正规军一起作战。先前雇佣的兵,若因死伤逃亡等原因而出现缺额,一律不再招募填补空缺,而是改由保丁来代替。这样平缓的过渡,只要坚持下去,假以时日,那些个雇佣来的兵就会慢慢消亡了,而且是用兵不血刃的方式。
按照王安石的这一思路,有计划地开始训练保丁,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只是这样的做法,违反了北宋建立以来所奉行的“养兵”政策,也违背了北宋政权严禁民间传习武技的传统政策。注定要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即使是神宗,对此也出现了怀疑和摇摆的态度。
自然,这反对声中,是少不了司马光的。他在《乞罢保甲状》中说:现在将一般乡民,用弓弩武装起来,教习武艺,农民也成为了半个兵了。他们本来都是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种者,忽然让他们穿上戎装,手持兵器,奔走于乡野之间,见到的人岂不要无比惊骇?老者们都在摇头叹息,以为是大大的不吉祥。
如果让他们去戌守边境,征讨戎狄,然而戎狄之民,向来都是以骑射为业,攻战对其而言是家常便饭,从儿童到老人,都没有丝毫陌生;中国的民众,生长于太平盛世之间,世代以务农为生,虽然现在给了他们兵器,教他们刺杀,在训练场上,貌似还算严整,可一旦跟戎狄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不用多想,也毋须怀疑,肯定是弃甲而逃,一溃千里。
要说司马光这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是一点也不差的了。他自己败了一次,就以为大家都跟他一样,当然,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一朝被蛇咬,终身怕井绳嘛。只是不知司马光大人是否在日理万机之余听过王韶的丁点事迹?
在司马光之流的反对声中,在神宗的犹疑中,王安石实行保甲法所要达到的改变募兵制的目的,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成功。司马光尽废新法后,农民兄弟们是不用每晚轮流着值班了,可以搂着老婆一觉睡到天亮了,只是,一觉醒来,突然发觉,自己的大boss换了。
只是,自宋以后,无论蒙汉满,从元至清,数百年间,皆无一例外,均推行保甲法,也主要是起到维持地方治安的目的,直到民国,仍然在沿用。
王安石的老乡,明朝人陈汝锜感叹道:如果保甲不废,按计划加以训练,假以时日,人们皆同仇敌忾,纵然是胡马南嘶,梁启超著《王安石传》也不至于让金人如入无人之境,纵横数千里,却没有一城能挫其锋芒!
康熙也曾说:“弭盗良法,无如保甲。”
梁启超看到此,也不免有些痛心,当然,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自身的因素,他说,保甲之法被废除之后,宋朝若不想南迁,又能奈何?然后梁启超不禁仰天长叹:“然则祸宋者,果荆公乎哉?抑温公乎哉”?
这一节,就以王安石的《省兵》来结尾:
有客语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
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
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
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
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
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
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11.市易法——那只看得见的手
北宋时期,城镇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自然就会有那么一批人,利用特殊的地位,加上非常的手段,慢慢形成了强势的垄断地位。垄断一旦形成,王安石《详定幕次呈圣从乐道》:扬雄识字无人敌,何逊能诗有世家。旧德醉心如美酒,新篇清目胜真茶。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是大大的不利。外地商贩贩运来的货物,寡头们一合计,就以很低的价格强行收购,然后囤积起来,等市场供应不足之时,再提价销售。这一买一卖之间,有人哭有人笑,当然,哭的肯定是普通老百姓和居于弱势的商人,而偷笑的就是那些个垄断者。
资本形成了积累,自然是要寻找消费的端口,古代的故有观念,土地是不变的财富,于是,大量的资金流入农村,兼并之风日盛。如此恶性循环之下,下头苦了百姓,上头亏了国家,这势必是不行的。
熙宁五年年初,一个自称草泽的魏继宗给北宋政府上书,这样说道:京城是百货云集之地,市场却不稳定,价格经常波动,贱买贵卖之间,有人往往获利数倍。富人大贾因为财力雄厚,有些还有权有势,所以往往能够轻易操控市场。外地商旅因为受其倾轧,无所获利,不愿长途劳顿;而普通的消费者,却要承受日益上涨的价格,民不聊生。这样,既抑制了商品的自由流通,普通百姓也无法达到小康,国家也没有获得什么利益,于国于民,都是百害而无一利呀。王安石《元日》管子曾说:“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那么,在如今的形势下,国家怎能袖手旁观、不整顿市场呢?
不如成立常平市易司,挑选精通理财之人掌管负责,寻求良贾来辅佐,让他们摸清市场行情,价格下跌之时,就提价收购,不至于让普通商人血本无归;价格上涨之时,就降价出售,不至于让平民百姓受苦。这样,一方面可以稳定物价,还能保护商品自由流通,国家也能将开阖敛散之权从富民手中收回,还可以获取一些利益,可谓一举多得。
要说这个市易法,并不是凭空出世的,王韶在秦凤路设置过市易务,可以说有实际经验可考,现在又有了魏继宗的建议,市易务便在开封风风火火地搞了起来。
那市易务具体都干些什么事情呢?
凡是可以买卖的货物,小商小贩们觉得不好卖出去,可以议定价格,由市易务购买;若是看上市易务里面另外的货物,也可以进行货物交换。
想要做点小生意,又缺乏本钱的同志,可以用房产什么的作为抵押,向市易务贷款,至于借了钱干什么,就随你自己的便了,只要到时还钱即可,当然,钱不是白借的,要付给市易务一点利息,年息20%,这样的利息水平,现在看来是有点高,但在当时对比高利贷,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除了借钱,也可以借货物,你看好哪种货物的行情,只要市易务中有,就可以借,也是一样得付点利息。如果点背,一时看走了眼,货物没卖出去,要是没过期变质的话,也可以由市易务作价收买,不再另取利息。
这样看来,市易务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现代商业银行的作用。
以前各地商贩,每个行业,都是有行会的,想要做哪行的生意,就得入哪个行会,当然,入行会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交“行例”钱。各地的行会,基本上是将本地的商品流通把持着的,长途贩运的商人反而得不到多大的利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朝廷的用度,是要摊派给各行的,对各行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成立市易务后,制定了“免行条贯”,各个商户依照盈利的多少,按月缴纳一定的免行钱,政府的采购不再进行摊派,而是在市场上进行正常的购买。
如此看来,市易务又有些像今天的工商局了,那个免行钱就类似于现在的税收。这对于活跃商品经济,应该说是一个进步的举措。
在市易务开展工作的同时,反对派们也没有闲着,忙着对市易法进行攻击,文彦博就写奏章说:我前几天去相国寺上香,看到市易务在街上居然连瓜果也卖,如此小利,所得无几,却失却了大国之体,增加了小民之怨气。而且那个地方,有很多外邦的行馆,让他们看见了,岂不笑话?
堂堂一个大国,竟然锱铢必较,古人说的理财难道也包括这种琐屑之利吗?但凡士大夫,若在市场上买卖货物而盈利,都会为做官之人所不齿。更不用说泱泱大国,却还在皇皇求利了。这样的垄断之事,孟子深以为耻,我也以此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