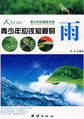我曾经有个偎被窝、睡懒觉的坏习惯。那迷迷糊糊的滋味比喝甜牛奶迷人一百倍!不过,上学迟到、挨批评的滋味可不好受。怎样戒掉这杯“迷魂汤”呢?东东出了个主意,让我临睡时喝三杯开水,让尿憋着我早起。一试,不灵,我还是忍不住钻回被窝去。再说,这太危险,一不小心会“画地图”。
嗐,要改掉一个坏习惯真难啊!
可是,阿芒说:“不难,一点也不难,只要你写个字据。”他递给我一张纸,纸上写着:
保证书
本人保证六点半以前起床,超过时间,阿芒有权用钉子刺本人的屁股。
保证人楠楠
阿芒眯缝了眼,盯着我的眼睛:“敢不敢?”
我咬了咬嘴唇:“敢。”
当时东东正在旁边画水彩画,阿芒捉住我一个手指蘸了点红颜料,说:“自己按!”
我在“保证人”后头按了一下,忽然想起《白毛女》里的杨白劳,憋不住“咯咯咯”笑起来。
阿芒不笑,一脸严肃,从书包里掏出来一根三寸长的钉子,亮闪闪一晃:“看,就是这真家伙!”
东东夺过钉子,装作日本军官的样子,说:“还是乖乖大大的,不然,死啦死啦的!”
这下子阿芒也乐了。
第二天清早,在似醒非醒的状态中,我忽然听到一阵呱嗒呱嗒的声音,自远而近。
啊,是阿芒来了!这是他穿着木屐走在围墙外石板巷子里的声音。那时候,在我们小镇上还见不到海绵拖鞋什么的,天热了,好多人就穿木屐。可四月里穿木屐的人是极少的,好像只有阿芒和他的爸爸。阿芒没有妈妈,他爸爸只会做木匠活,不会做鞋子。
果然是他。听,他在唱山歌哩!
黄箬壳,青竹篾,
一黄昏编只小斗笠。
蒙蒙雨,雨蒙蒙,
雨打斗笠淅沥沥……
我蓦地想起了那根亮闪闪的钉子,觉得屁股上一阵麻,便一掀被子下了床。
外边在下雨,蒙蒙的雨。
围墙的花格子那边晃动着一只淡黄色的斗笠。
我打开窗子喊:“阿芒,进来!院子门没闩。”
花格子里伸进一只手来,打了个“注意这里”的手势就缩回去了,斗笠也不见了。小巷里又响起呱嗒呱嗒的木屐声。
花格子里放着一只烘山芋,用张新鲜的桑叶包着。桑叶上刺着一个“奖”字,对了,必定是用那根钉子刺的。
烘山芋的皮是黑的、硬的,掰开来里头却是黄的、软的,立即窜出一股白气,香得叫人流口水。我把烘山芋拿进屋,放在桌子上,赶紧到院子里漱口。正漱着,听到妈妈在屋里大惊小怪地咕哝:“呀,这是啥?哎哟!”
我满嘴牙膏沫,说不上话。等我回到屋里,那烘山芋已躺在畚箕里了。我把漱口杯碰得山响:“这是阿芒特地送我的!这是对我第一次早起的奖励。”
“那不卫生,吃了肚子痛,你看,妈妈给你买馒头来了。快趁热……”
我背起书包朝外走。妈妈追上来给我馒头,我死活也不要。
到了学校,阿芒问我:“楠楠,烘山芋夹生不夹生?”我支吾了一下,说:“有,有一点。”阿芒用空心拳敲了下额角,“都怪我太性急,夹生了,不好吃。”
我心里很难过,总觉得阿芒受了委屈。
坏习惯要用好习惯来替代。每天早晨,我不再睡回笼觉,一醒来,就期待着阿芒的木屐声。小巷,窄窄的,铺着青石板、黄石板,石板下边是空的,是阴沟。穿木屐在小巷里走,有几种回声,形成一种特别的韵味。阿芒脚下的木屐是柏树做的,声音比一般杨树木屐的钝一点。呱嗒,呱嗒,呱嗒……似乎包含着一种不容违拗的意思,使人想起阿芒倔强的嘴角。
如果是雨天,木屐声还伴着一首水淋淋的山歌:“黄箬壳,青竹篾,一黄昏编只小斗笠……”歌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
如果不是雨天,嘎一声,阿芒就推门进院子来了。他不进屋,把书包放在合欢树下的石条上,自顾自看书,削铅笔。他就是这样的脾气,不爱说话,尤其不高兴主动招呼人。
当阳光照到树冠上,院子里就飘荡起一种橘黄色粉末般的东西。或许这就是书上写的晨曦?合欢树要开好几次花,花是粉红的。小鸟们吵吵着,在花枝间跳来蹿去;有的像在思考什么,头侧来侧去。
阿芒在石条上或站或跑,尖起嘴唇用啾啾的口哨和小鸟们对答。我喜欢看他这时候的侧影——眼睛亮晶晶的,仿佛融进了阳光;脸蛋轮廓线上的汗毛,茸茸的,被阳光染成金黄色……
想不到,清晨竟是如此美好!
从此,我再也没有迟到过。每当木屐声响起,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从被窝里跳出来。
有一天,我没有等到木屐声。
我吃过早饭直奔阿芒家里。
阿芒正在试穿新布鞋。我想起来了,因为天气渐热,穿木屐的人多起来,昨天学校出了个不准穿木屐上学的布告。阿芒穿了布鞋,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像麻雀一样跳跳蹦蹦,一会儿用这只脚跳,一会儿用那只脚跳。
阿芒的爸爸是个和木屐一样爽直快乐的大块头,看着儿子的高兴劲儿,把含在嘴里的米糕一会儿挤到左腮,一会儿挤到右腮,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等到我们要走了,他才说:“且慢!阿芒,还有楠楠,我这当儿正在想,你们也来想想看:天下最补人的补药是啥?”
这问题提得挺突然,我说:“是人参!”阿芒说:“是蜂王浆!”阿芒爸爸直摇头。我又说:“是白木耳!”阿芒说:“是鳗鱼!”阿芒爸爸还是摇头,险些把夹在耳朵上的一小截扁铅笔摇下来。
听我们越猜越荒唐了,他得意地笑起来:“不对!都不对!我说最好的补药是交情、是情分!不相信?昨天放学回来阿芒愁眉苦脸的,今天呢?乐得像跳蚤,因为有鞋了,能上学了。这鞋要是买来的,阿芒哪会这么高兴,我哪会这么心暖?这鞋是隔壁刘二婶大半夜没睡赶出来的。”
我和阿芒不大懂。他又说了:“真难为人家了,阿芒,记着,这鞋要珍惜着穿。听到没有?去吧,去吧!”
补药?这比喻真新鲜,不过,好像不那么贴切。
阿芒果然很爱惜这双鞋。走到校门口,他才脱下木屐换上布鞋;放学走出校门,他又换上木屐。
这样,每天一早,我照旧能等到动听的木屐声。
穿木屐凉快,走在麻石街上,呱嗒呱嗒,没有拖鞋疲沓的调门,听着叫人精神抖擞。
没劲的是我妈不许我穿木屐,她怕我滑跤,怕我脚底嫩,会生什么“鸡眼”。她就是这样,老是唠叨怕什么,怕什么。游泳,她怕我红眼睛,烂耳朵,更怕淹死;骑自行车,她怕我跌了、撞了,和汽车香鼻了……唉,烦死了。其实,她管不了我那么多。东东说:“男子汉不会骑车多失台型!”阿芒说:“不会游泳,要吃亏的。”真对!避着妈妈眼睛,我什么都干。我当然也有一双木屐,那是阿芒亲手给我做的。我怎么能没有木屐呢?妈妈怎么不想一想,在一大群穿木屐的男孩子里,夹着一个穿皮拖鞋的人那是多么丧气,多么“现世”。
有一天,我正走上高高的石拱桥,发现妈妈从对面上桥来。我在慌乱中踩到了一块西瓜皮,跌倒了,滚到桥堍。妈妈奔过来,惊叫起来:“血!血!”
我扭伤了脚踝,头上破了点皮,没啥大不了的,可我妈妈心疼得要命,挂了急诊,嚷着叫医生给我输血。
从医院出来,妈妈要背我走,我不要,还是趿着木屐走。这下子给她抓住了“罪魁祸首”,一迭声问我:“谁让你穿木屐的?是谁?谁?你怎么不回答?”
我死咬着嘴唇,只顾走路,木屐敲打着石子路,呱嗒呱嗒,像在示威。
一到家,妈妈要劈掉木屐,我来了倔劲,说没有木屐就赤脚。她妥协了,反复唠叨一句话:“嗐,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她才四十岁,能算老人吗?
第二天星期天,妈妈不许我起床,要我躺着养伤;一早熬了赤豆糖粥,说那是补血的。粥太甜,不如烘山芋那隐隐的甜来得自然。
阿芒不会来,星期天,他忙着哩,有时还跟他爸爸做木匠活儿。他食指和大拇指的内侧有一条V字形的老茧,就是在推刨时磨出来的。
妈妈上班去了,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闷得慌,只好折纸乌龟,一只、两只……
“呱嗒呱,呱嗒嗒呱嗒……”咦,这不是木屐声吗?但那不是阿芒,阿芒的节奏和声调不是这样的……噢,我听出来了,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阿芒。
果然是这样,嘎一声门响,院子门框里出现了阿芒和他的爸爸。阿芒爸爸拎着一只有盖子的饭篮,阿芒托着一只小竹笼子,里边有活跳跳的绿色的东西——一定是纺织娘。
我高兴了,从席子底下抽出木屐,趿着,一拐一瘸迎出去。隔了一夜,脚踝反而肿得厉害。
阿芒爸爸放了篮子,两只大手捉住了我的肩膀,仔细看我的头,说:“满头缠纱布,伤在哪里啊?”
阿芒不说话,蹲下去看我的脚踝。
阿芒爸爸说:“出了不少血吧?纱布上还有渗出来的,哦?”
我拍拍头:“哪是血?是红药水。”
阿芒爸爸笑了:“不要紧,不要紧,大伯给你送补血药来了。看,鸡蛋!吃一个鸡蛋长一砻糠爿爿血。你不信?你不信就试试看!哈哈哈……”他的嗓门真响,他的手劲真大,轻轻一下子,我不知怎么就坐到床上了。他取下我脚上的木屐,翻过底来,呱呱拍打着,朝阿芒说:“看!看!底里的防滑槽这么浅,这么浅,躲不下一只蚂蚁……”
阿芒连忙把木屐抢过去,说:“别说了,我晓得。”把汗背心往上一捋,露出了别在裤腰上的一根钢锯条。他把小竹笼子放在床上,跑出门去,在院子的石凳上,咕啦咕啦地锯着木屐。他在加深木屐底里的防滑槽。他怎么老喜欢那张石条凳呢?
阿芒爸爸扯了扯我,说:“啊呀纸乌龟活啦!看,在爬呢!”
我回过头,果然看见一只纸乌龟在爬。
他眯起眼看我,一本正经地说:“那乌龟一定沾上你的血了,沾了活血……”
“不对!下边有只纺织娘!”
“你差点又上我的当了,哈哈哈……”他开心地大笑,震得地板和天花板一齐哐哐响。
我说:“你骗不了我。”
他说:“别吹!别吹!没忘记去年蛇咬那一次吗?啊!哈哈……”他笑得更得意了,一边朝外走去,他要上工去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整天哈哈哈,说俏皮话,从不见他愁眉苦脸,发火骂人。我真羡慕阿芒有这样的爸爸。当然,我爸爸也是个风趣的人,可他常年不在家。他是县委副书记,忙得很,一年中难得回家住几天。
阿芒爸爸走后不多久,我妈妈买菜回来了。我隔着窗子看见她在和阿芒说话。
一会儿妈妈进房来了,买来了甜橄榄什么的。我赶紧跑到窗口去喊阿芒。可是,阿芒不在了,石条凳上只有一摊木屑。
妈妈冷冷地说:“木屐原来是他给你的。真是讨厌。跟好道学好样,跟坏道学坏样……”
想不到妈妈还记恨着给木屐的人,真没道理。妈妈一定对阿芒说了不讲道理的话了,所以他走了,带走了木屐。我赤了脚一拐一瘸跑出大门去,想追上阿芒。
小巷里静静的,只有几只大白鹅在摇摇摆摆地踱步。
妈妈追出来,要我穿上皮拖鞋,我不穿,赤着脚往回走。回头看见拿着拖鞋跟在后头的妈妈,我心里又不忍起来。
妈妈,你可知道阿芒,还有他爸爸,对我是多么好!
有一次——对了,是刚才阿芒爸爸提起过的,我、阿芒还有东东,去年去田埂上捉蚱蜢的那一次。我被一条小水蛇咬了一口,在脚背上。这是不要紧的,水蛇没有毒,痛一痛肿一块就没事了。东东和我靠得近,他最会出洋相,故意大喊:“阿芒,不得了!楠楠叫毒蛇咬了!”也真巧,阿芒跑过来时,棉田边真的游着一条赤链蛇,阿芒双眼放光,鼻翼翕动,拾起一块土疙瘩猛地向赤链蛇打去……我和东东反而吓呆了,我们知道阿芒要捉毒蛇了。因为阿芒爸爸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被毒蛇咬了,只要马上吃到那蛇的热胆就不要紧。
打过去的泥块分散了蛇的注意力,阿芒乘机敏捷地捉住了蛇尾,迅即把蛇倒提起来。这是极大的冒险,稍一迟缓,蛇就会回头咬人。我和东东急得说不清话,只是喊:“不要!”“别!”……阿芒打死了蛇,用一片碎碗爿划开蛇腹,拉出内脏,在太阳光里照照,一捏捏出了青黑的蛇胆:“楠楠,快吃!”我不吃,多恶心。阿芒不相信东东和我的解释,只是逼着我吃,最后阿芒一边哭一边揪着我喊:“吃啊!吃啊!蛇胆要冷啦!”
事后,阿芒爸爸晓得了,先说他讲的故事是个传说罢了,而后大大感叹了一番,拍着我们三个孩子的肩一遍一遍地说:“好啊!好啊!朋友就得这么交,这情分是金银财宝也买不到的哩!”
晚上,我把蛇的故事告诉了妈妈。我不能只是朝妈妈发火、顶牛,我要让她知道阿芒是怎样一个人,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情谊。
我想错了。妈妈听了这个故事,像被刺毛虫蜇了一样,坐立不安,唠叨没完:“你被蛇咬过!你怎么不告诉我?哎呀,这怎么办?多危险!多野蛮!多……”
我掩住耳朵,不听她唠叨。
一会儿,妈妈忽然不说话了。我偷偷一看,见她怔怔地坐在凳子上,一会儿用右手捏左手,一会儿用左手捏右手。过一会儿,她轻轻地说:“楠楠,你怎么老瞒着妈妈,这么下去,多叫人担心啊……我只有你一个孩子,你爸爸又不在家,他工作忙,没时间管你……”她说着说着,带了哭腔,咳嗽起来,咳得眼圈儿发红。我忽然发现妈妈本来光滑的脸上有了不少皱纹,本来饱满的嘴唇向两边耷拉下去。她刚四十岁,怎么就老了呢?东东的妈妈,阿芒的爸爸都是四十岁,比她年轻多了。自从爸爸提升为县委副书记,妈妈老跟爸爸吵着调工作。她嫌她现在的服务行业不体面,想乘调到县城的机会调一个工种。爸爸不同意,说按规定调县城是可以的,但工种不能调。妈妈近年来好像变了一个人,和单位里的叔叔阿姨们关系都不好,极少有人到我家来玩。东东的妈妈在小菜场工作,本来常来我家玩,有一次为了妈妈托她买排骨的事,妈妈不再理她,她从此也不再来玩了……
妈妈蹙着眉坐着,不时咳嗽。我忽然觉得她很孤独,很可怜。如果我没有阿芒、东东,还有阿芒爸爸这许多朋友,我也会很孤独、很可怜的。
我走过去,抚摩着妈妈的肩,说:“妈妈,你吃点药吧,爸爸不是给你买了补药吗?”
妈妈回身拉住我的手,眼睛亮亮地说:“楠楠,你是********的儿子,不能和阿芒他们一样要求的。以后,只要你听我的话,对妈妈来说就比吃最好的补药还补。”
我忽然想起了阿芒爸爸说的关于补药的话。我忽然懂了那话的意思。我说:“妈妈,以后你和东东妈妈,还有好多叔叔阿姨和好吧,阿芒爸爸说的,情意是最好的补药。”
妈妈的眼睛又暗了,一撒手往外走,走到屋门口,回头说:“你懂什么!”
砰一声,房门关上了。
脚脖子没退肿,妈妈不许我上学。
躺在床上,我等待那熟悉的木屐声在小巷里再次响起。可是,我没有等到。
这一天真长啊。我第一次发现一分钟竟也那么漫长。秒针嚓嚓嚓走上老半天才能走一圈。
第二天早晨,东东来了。他等我妈妈上班了才来。东东告诉了我阿芒不来的原因:星期天傍晚,我妈妈到阿芒家去了。阿芒爸爸不在,我妈妈对阿芒说以后不要来叫我玩了,怕影响功课。我妈妈带去了那只盖篮,里头有一沓钱——蛋钱。事后阿芒爸爸哈哈大笑,说:“笑话!笑死人!这种蛋是用钱能买得到的吗?”
我能想象得出阿芒爸爸大笑的模样,那不是表示高兴的笑。
东东临走时拿起我床头桌上的小篾笼子,说:“阿芒让我把笼子收回去。”我扑过去抢住笼子,说:“东东,留下它吧,留下它吧……”我觉得很委屈,喉咙里哽哽的。
东东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松了手,说:“好吧,我跟阿芒说。”
几天以后,我上学去,阿芒还像从前一样和我好。像约好似的,我们谁也没有提起不愉快的事,就像从来也没发生过。
以后,每天早晨,我还能听到熟悉的木屐声在小巷里响起。但,阿芒再也不进院子来了,清脆的木屐声渐渐近来,又渐渐远去,总是那样从容而自信。这小巷并不是阿芒上学的必经之路,我知道阿芒这样做的用心。
不久,学期结束了,分数单还没发,我家就要搬到县城去了。去城里,妈妈还当服务员,促使她下决心搬家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许,木屐也是原因之一。
搬家那天,爸爸突然被通知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没能来,只来了两辆卡车。小巷窄,车子开不进,只能停在巷子口,搬运家具很麻烦。
阿芒爸爸刚巧路过这里,把木匠家什一放,站在巷子口喊:“大家来帮个忙吧!来帮个忙吧!”
不少邻居都来帮忙了,连东东和他妈妈也来了。窄窄的小巷一片忙碌。
一会儿,东西搬完了,房子里空荡荡的,我心里也空荡荡的。我从卡车上拿回一只小凳放到院子的石条凳上,爬上去摘挂在合欢树上的小笼子。
汽车要开了,妈妈跑回来喊:“楠楠,小笼子不带了,走吧。”
我没回头,咬着牙说:“不!我要带着的!”
妈妈被我的坚决劲儿吓了一跳,讪讪地说:“随你,随你。”
粉红的合欢花没有谢,使人想起那些美好的早晨。
临上车时,东东对我说:“楠楠,以后你还来这里吗?”我点点头。他说:“你来了就住在我家里,好吗?”我又点点头。他像大人似的,伸过一只右手来,我也伸出右手去,握住了。他又用左手捂住了我的手背,我也用左手捂住了他的手背。四只手握在一起,摇啊,摇啊。我们都别过脸去,男子汉流泪是难为情的。这是阿芒爸爸常说的。
阿芒爸爸挤上来,说:“楠楠,搬家也算是喜事的,别气鼓鼓的,嗯。”他拧拧我的脸腮,忽然收了笑,轻轻地说,“阿芒他没来帮忙,因为……不说了,原谅他吧,他就这么个脾气。你以后回镇上来,一定住到我家来,我和阿芒都欢迎你。上车吧,汽车要开了。”他两手一托,我上了车。
这时东东指着说:“看,阿芒在那儿呢!”
阿芒站在斜对面不远的一条巷子口,见我们注意他,一闪身就消失在巷子里了。
汽车开过那条巷子,我也没有看见阿芒。
别了,我的小镇;别了,我的朋友们。
后来,爸爸问我:“他们都叫你以后去玩,你怎么就不说请他们来我们家玩呢?”
我哭了,我感到内疚,感到委屈,感到说不出的难过。
爸爸听了我的叙述,久久地沉默着。
过了一些日子,爸爸有事到小镇去,回来时给我带来了一件用旧报纸包着的东西。拆开一看,原来就是那双木屐。
我高兴了:“是阿芒叫你带给我的?”
爸爸摇摇头,说:“不,是我向他讨的。”
对的,应该是这样的。我真感激爸爸。
木屐底面的每一条防滑槽都加深过,阿芒怕我再摔跤。
如今,我的脚已经穿不进这双木屐了,可我还是把它保存着。一看见它,我的耳边就会响起小巷里那清脆悦耳、从容不迫的木屐声:呱嗒、呱嗒、呱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