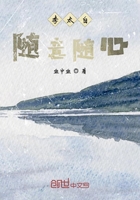季怀槿的生日在春天,柳条抽新芽的季节,风都是暖的。一大早就有几个半大小子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打闹。
季怀槿租住在一间上了楼龄的居民房里,只有一个卧室,客厅小得可怜,勉强放得下一张餐桌。她套上薄外套准备出门的时候,电视里正在播放悼念讲话,季怀槿连遥控器都不想拿,直接用脚踹着关掉电源。
唐叙老早就等在她家门口。平时他也是一个挺显眼的人,因为个儿高,长得也好看,可是今天跟他身后的大家伙比起来,实在逊色了太多。
唐叙周围是几个季怀槿根本就不认识的街坊,假装站在树底下闲聊,其实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这边儿。
季怀槿走上去照着唐叙胸前给了一拳,客套都懒得客套一下,“这也忒土了吧?怎么看都像一流动公厕似的,一会儿就让我坐这个?”
唐叙反应很快,一把打掉季怀槿的手,笑的时候牙齿在太阳底下白得泛光,“懂什么你,这颜色还限量呢,费了我好大劲才弄来的。”
一般人过生日都开心,可是季怀槿不一样,每到生日的时候,老是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唐叙当然知道为什么,所以今年他才特地租来一辆加长的粉色悍马,说是要带着季怀槿公路旅行,从北京开到天津,途中在车里杀人放火,干什么都行。
季怀槿倒还不想杀人,今天只要不在这里待着,她觉得随便干点儿什么都好。
唐叙装得特别绅士地给她打开车门,手护着车顶让她坐进去,然后自己小跑两步,坐进驾驶席。轿车内部驾驶座和车厢是隔开的,唐叙得打开后面的喇叭,才能和季怀槿说上话。
季怀槿上了车以后半天没动静,唐叙“喂”了好一会儿,她才懒洋洋地说:“就冲这内饰,粉色我也忍了。”
这辆车专门做派对用的,一排是座椅,一排是酒柜。已经有好几支洋酒插在冰柜里,冷气和灯光散发出幽幽的蓝色,轻飘飘地向外溢出来。
唐叙清了清嗓子,声音通过扬声器传进季怀槿耳朵里:“走,我先带你吃碗长寿面去。”
在季怀槿生日前两天,唐叙就租下了这辆车,夜里趁着路上车不多的时候,开出去练了好久。他没有开大车的车本儿,虽然办了个假的,但开车技术做不了假,唐叙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儿紧张。
一辆和公共汽车差不多长的悍马跑在路上,简直要引起交通瘫痪。季怀槿窝在座位上,透过黑色车膜看着窗外的车挤成一片,心里却邪恶地轻松起来。
唐叙将车开到一条巷子口,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车停好,光这一辆车就占了三个车位。然后他领着季怀槿走到巷口一家面馆。
面馆临街,大开着门,正对着那辆悍马。
唐叙轻车熟路地带着季怀槿进去,拣了最靠外的一张桌子。他抽了两张桌上的餐巾纸,擦了擦凳子,让季怀槿坐下,自己却大大咧咧地坐到对面去,喊老板娘点菜。
他给自己和季怀槿各点了一碗面,自己是牛肉面,外加一碟牛肉,一盘卤蛋,给季怀槿的就是一碗阳春面。
季怀槿口淡,他还记得。唐叙喜欢吃酱成赭色、切得薄薄的牛肉,她也记得。
点好了面,唐叙和季怀槿一时无话,两人彼此对看着。
季怀槿觉得和唐叙这几年不见,他变化挺大的。在印象当中唐叙总是穿着熨帖的棉衬衫或白色T恤,校服也和别人的不一样,看上去总是很合身,不像季怀槿的校服,永远比自己的身材大两号,仿佛在身上罩了一个面口袋,邋遢得要命。
他俩是最近这两个月才又重新联系上的,因为一次巧合。从前的朋友再见,不热络也不生疏,季怀槿觉得刚刚好。
比如现在两人都不说话,却不显得尴尬。
唐叙从餐盒里拿出两双筷子,在桌沿儿上比齐了,倒过筷子尖儿来摆到季怀槿面前,自己则拿着另一对,说:“这家儿的阳春面,是我吃过的最像老梁做的,一会儿你尝尝。”
老梁是以前他们院儿里食堂的厨子,是个女的,四十多岁了,一直未婚。她说话瓮声瓮气的,好像喉咙连着后脑勺,一发声就有嗡嗡的共鸣。最开始院儿里的孩子分不清她是男是女,而大人们也不教着叫“梁阿姨”。
老梁喜欢孩子们跟着大人们叫,从来不跟他们生气,总是在孩子们饿的时候,用长着厚茧的食指从竹编的点心盒里拈一块绿豆糕递给他们。
季怀槿现在想想,老梁可能不喜欢男人。不过这也不代表她就一定喜欢女人,或许她更喜欢的是那一根根在她手里被越抻越长的生面,和打开锅盖儿后翻滚着冒出来的水蒸气。
拉面上桌,季怀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抬头的时候发现唐叙正一脸期待地看着她,问:“怎么样,是不是和老梁的手艺特像?”
季怀槿点点头,但面子上有些讪讪的,因为她其实不记得老梁下的面到底是个什么味儿,虽然有段时间她吃老梁做的面,能从早饭一直吃到晚饭。
可是这几年当中,季怀槿觉得自己的记忆像是被人颠倒了个个儿,有些事儿无关紧要,她却能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可是有的事情明明离她很近,她反倒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她知道这是人的自我保护机制,在替她过滤一些有可能对她产生伤害的回忆。可是相比而言,她觉得缺失那些回忆才更痛苦一些。
幸亏唐叙没有注意到她表情的变化,而是拿出手机分别打了两个电话。
没过多久米乐和常小柳就来了。
米乐和唐叙一样,算是季怀槿的发小儿。常小柳是季怀槿实习的报社同事,认识不久,但还算聊得来。
她俩也被邀请上了“悍马派对”,上车之前,唐叙从车里拿出一顶粉红色的机车帽,戴在季怀槿头上,“送你的生日礼物,你看是不是和这车特配?”
季怀槿作势要摘,被唐叙拦住,“先别摘啊,今年的第一份儿礼物,你不拍张照留个纪念?”说完他就拿出自己手机,不由分说地给季怀槿照了张相,拿到她面前给她看。
机车帽上用彩色喷绘写着“Happy Birthday”之类的祝福语,季怀槿觉得幼稚,同时也有点儿好笑。唐叙替她摘帽子的锁扣,鼓捣了好半天,最终皱着脸说:“坏了,叫你刚才乱动,卡住了。”
季怀槿看不见锁扣,有点儿着急,“那怎么办啊?要不找把剪刀铰开吧?”
又折腾了几分钟,帽子还是拿不下来,唐叙干脆放弃,“你戴着得了,其实看着还挺有个性的。”
季怀槿本来不想就这么算了,但是见米乐嘴角带着讳莫如深的笑容看着她和唐叙,想想还是不折腾了,就和两个姑娘一起上了车。
米乐比季怀槿小两岁,属鸡。季怀槿一直觉得她的名字起得特好,属鸡的孩子,有米就能高兴,这应该是父母最简单,也最真诚的愿望。
米乐上学早,又赶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办了个实验班,直接把五年级和六年级的课程一起教了,早一年毕业,相当于跳了一级。实验班就推行了两年,后来因为有家长反映孩子升上初中后会比较吃力,就停办了。
米乐因为上了实验班的关系,在初中和季怀槿成了同班同学。
初见时,米乐又瘦又高,脖子长,腿细,笑的时候颧骨轻微凸起,像只丹顶鹤,季怀槿从来没把她当成妹妹看待。可是她们交往的几年,以及分开的几年当中,米乐没怎么长过个儿,连模样都没怎么变,只是胖了点儿,以至于现在季怀槿和她站在一起,才真正显得像个姐姐。
车子开动,沿着市里有些狭窄的旧路慢慢往前磨蹭,终于驶上畅通的环线。
季怀槿用牙咬开一支红酒的瓶塞,将酒倒进高脚杯里,分别递给米乐和常小柳。
米乐接过酒杯,凑在鼻子底下嗅了嗅。“1996年白马庄的赤霞珠,唐叙真够舍得花钱的,”她笑的时候右边的虎牙跑出来,“不过天还没黑呢,现在就开喝?”
“谁规定天黑才能喝酒了?”季怀槿仰头把酒灌进肚子里,倾空酒杯给米乐和常小柳看,一滴没剩。
米乐垂着的睫毛动了动,然后伸手攥住季怀槿的指尖,用力握了握,“行!我陪你喝。”她体会不到季怀槿的痛苦和恐惧,但完全能够理解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