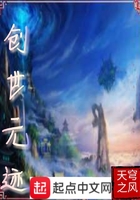离开杨明义老师家时,天色已向晚。回到家里的时候,靖南看到潘淑禾正伏在猪圈墙上喂猪,那背影像一位勤劳的母亲。靖南的心颤了一下,他再度陷入彷徨之中。难啊,难,难于蜀道上青天。他忽然想,应试着与潘淑禾沟通一下,谈谈话,寻找深入话题的机会,对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万一她能够通情达理就好了。看上去,她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当仁不让的女主人,像是天生就与这个家融为一体,这个家已经成了她的。
“喂猪啊?”靖南问。
潘淑禾直起身,道:“是哩。”
“怎么全是地瓜,没有掺糠?”
“人过年,也给猪过个年吧。”潘淑禾说。
靖南想:潘淑禾你也会幽默啊。
靖南问:“娘呢?”
“到大哥家去了。”
潘淑禾将筲里的猪食统统倒入猪槽里,然后又对靖南说道:“靖南,”
“唔,”
“明天,咱一块到五里沟咱二哥那里看看,算是给他拜个年。其实是给我娘家拜个年。你从大学回来得晚,年前没能去五里沟。咱去那里,也不用带什么东西。再拖着不去,外面的人会笑话咱的,说咱不懂事。行吗,靖南?”
靖南没有马上作答。他不想踏她二哥家的门槛。可他与潘淑禾的关系没有了断,五里沟的人、槐树庄的人就都把他们看成当然的夫妻当然的两口子,把潘淑禾的娘家二哥看作他靖南的大舅子。潘淑禾提出去五里沟她二哥家走一走,似乎合情合理,他若是拒绝,倒显得情理难容,甚或有人说他大逆不道。既然他还没有与潘淑禾分道扬镳,从乡下人的情理上的眼光看,他现在就没有理由回绝潘淑禾的提议。
靖南想,也好,到时候在去或回的路上,只有他和潘淑禾两个人,将计就计,也许能做好潘淑禾的思想工作。
“嗯……我想,好吧。”靖南吞吞吐吐地说道。
“去了五里沟咱二哥那里,你要高高兴兴的,不要像现在这个样子。”
“我没有不高兴呀?”靖南听潘淑禾说的话,心里有些不舒服,她嘴里竟然说成是“咱二哥”,谁跟你“咱”?
“傻子才会看不出来呢。”
靖南没再辩驳,朝屋里走去。
潘淑禾放下猪食筲,也进了屋。
“你对我不好。”潘淑禾忽然说道。
“你……”靖南吃了一惊。
“可我对你好。我就是把心给你吃了,也换不来你一个笑脸。”
靖南不作答。
“你好冷,真冷,”
“潘淑禾,你别说了,好吗?”
潘淑禾闭了嘴,却满含怨气地看了靖南几眼。
这一夜,靖南实在困乏极了,精神萎顿,无以自制地阖上了双眼,沉沉地睡了一夜。他不知道,潘淑禾曾几次在灯下迷醉而遗憾却又幽怨地打量他,欣赏他安甜的睡态。他的睡相真是好看,嘴角弯弯的,抿成一条线,一条美妙的曲线,他的脸上泛着柔和的光。
这是她近四年来第一次如此贴近如此陶醉地看他。他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却像远在天边,只能这么地看着,她怕弄醒了他,怕他醒来后会给她冷脸白眼,她不羞死才怪……女人的羞涩仍在她身上发挥着作用,啊,在她眼里,他像是一朵瑰丽的易碎的花,只可欣赏,不可触摸。
更何况,她不也越雷池半步,那道灵符在那里,她的手只要稍一越轨,就会受到重击。她怅怅的,简直想痛哭一场。她觉得自己过的是一种可怜的守活寡的日月,觉得她与靖南的关系其实不伦不类,妻不妻,夫不夫,形同虚设,名不副实,有的人以为他们结婚了,有的人以为他们没有结婚,她怎么真心人换得个空心人呢?不行,不行,一定要敲锣打鼓,一定要放鞭放炮,要让人们知道,要让人们都承认,她是他的妻子,他是她的男人……还要,还要和他一起到乡里搞个结婚登记,白纸黑字红手印,你想跑想赖都休想,你不理我,你不喜欢我,我也是你的妻子,你也是我的男人,这是命中注定,你心强,也能强得过命吗?
第二天上午,靖南和潘淑禾一起来到了五里沟潘淑禾的二哥家里。潘淑禾对靖南的表现还算满意,给了她面子,也给她脸上增了光。靖南没有闷闷不乐,始终微笑着,教养良好的样子。她却不知靖南的心里是多么屈辱,那笑容假装得多么累,又是多么机械,靖南觉得自己简直是在作贱自己。
潘淑禾发现,靖南也称她二哥为“二哥”。只是,靖南话语不多,特别是在酒桌上,更是不言不语,也不大喝酒,好像只喝了一杯,就推说酒量不行再也不喝了,自然也未敬她二哥她二嫂……但是,她已经比较满意了,她在她二嫂面前好好风光了半天呢,她用实际行动向她二嫂证明,她找了一个帅气精干的有出息的男人,她的男人是个大学生呢。
可是,离开了五里沟,两人单独在一起时,靖南的话反倒是更少了。他的心里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再过些日子,大学就要开学了,而现在,他们是在山野的道路上单独相处,周围没有任何人,此时不把话挑明更待何时?
可是,如果潘淑禾还是不答应怎么办?如果事情仍然陷入僵局怎么办?如果自己捅破了马蜂窝怎么办?……为什么老是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呢?不再拖了,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不说出心里的肺腑之言,才是真正对不起她。我决不会像一些男人那样,结了婚,却把妻子扔在家里,在外面吃“野食”,找情妇,****,搞婚外恋……如果我那么做,才是真正的不道德,才是真正愧对于她这个卦姑。
靖南下了自行车,用手推着朝前行进。潘淑禾见靖南下了自行车,不明白是为什么,就也下来,走在靖南的身旁。
这个倔强的不善变通的乖孩子,他鼓励着自己,却仍在踌躇着,嘴唇几度张开,又几度合拢。他将过去准备好的一些理由一些话语重在脑中回忆了一遍,并开始酝酿情绪。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些失态,他紧张得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竟像是要去赴一场国际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