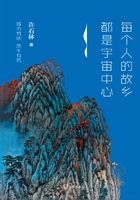那天下午,和往常一样,我围上围巾,下楼,左转,前行三十米,到了街口。
地是湿的,天色阴晦,冷风刮着。冷。冷。冷。脸冷,脚冷,手揣在衣兜里,还是冷。
街口处,有辆三轮垃圾车。从车边走过,转身时,却看见一个人躺在拐角处的墙边。
他身上裹着件肥大的青黑的棉大衣,满是污渍,脏兮兮的,泛着油光,戴顶褐色的线纺帽,穿一双大头皮鞋。他仰面躺在两大包蓬松的麻布口袋上,双手插在袖间,眼闭着,一动不动。
路人从他跟前匆匆而过。
妻子有些害怕地拉着我,示意快走。
流浪汉?乞讨者?精神病人?突发病患者?是死人还是活人?我边走边回头。
第二天,路过时,又看见了他。他正蹲在墙角,手里捧着盒饭,埋头吃着。他的脚边,仍然是那两只麻布口袋,还有根竹筒扁担。我略放了心。
再次见到他时,他正伏在垃圾车旁,双手戴着手套,在垃圾里刨着、翻捡着,我把垃圾口袋扔进去,他就像拾到一袋的珍宝,迫不及待地扒开。这次,看清了他的样子:身材高大,有五十来岁的样子;酱紫色的脸,许是多日没洗过,像抹了层厚厚的油彩;浓眉,大眼,满脸胡子巴渣,鼻子红肿得像根胡萝卜。
我确定了他的身份,而且,前两次夜里路过街口拐角的遮风处,和衣蜷缩着睡在檐下的那个人就是他!
但我觉得愧疚。扔的垃圾袋里除了沤烂的菜叶,变臭的蛋壳,干瘪的果皮,没有他想要寻找的东西。
在街上,隔三岔五,就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乞讨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衣衫褴褛、断手残脚、惨不忍睹的伤残者,向每一个过往的人伸出脏兮兮的手;有背着书包、戴副眼镜,像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小姑娘跪在地上,他们的脚边多半有张学生证或获奖证书,有一封感人肺腑的求助信;有穿戴整齐,拧一个旅行包,再抱一个小孩,申明只要三、二十元路费的求助者……对此,早习以为常、见惯不惊、熟视无睹甚而无动于衷。我总疑心:在不远处,或许正躲藏着一双狡猾的眼光,盯着乞讨的孩子。集散人尽之后,那些无手断脚的伤残者,终会被一双或几双好手好脚抬上车,继续他们的乞讨之旅……
但不知怎的,我却觉得该为这个人做点什么。
回到家,开始找废弃物。早上上班,当我提着装了一个空酱油瓶,两个空纯净水瓶的垃圾口袋到垃圾车旁时,却看到捡垃圾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女清洁工,一个是住在不远处的老人。这正是倒垃圾的高峰期。六只手,在垃圾里忙碌着。显然,在那两人面前,他是异己,是别人领地的闯入者,必然受到排斥。我刚把垃圾扔进车里,一下就被那两人瓜分了。他站在旁边,动作迟疑,只能翻捡那两人先翻捡过一遍的。
我又找到几个纸盒子,折叠好。下午,垃圾车旁空无一人,他正坐在拐角的檐坎上,我走过去,径直递给他。他毫无准备,有些惊惶地站起来,嘴蠕动着,双手接过。我看了看地上的麻布口袋。我希望是满的。
曾看到个故事:某富翁与漂亮女友回别墅,下车,遇一乞丐。那天富翁的心情很好,走过去,说:你要什么?我会满足你小小的愿望。乞丐说:我想讨一本书!先生,你看,天气多好,在这样的阳光里,晒着太阳,看着书,是多么美好的享受!那富翁很尴尬,没想到乞丐想讨的是一本书,而他家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一本像样的书!这是个太过于美好和富于想象的故事,但我看到的那些乞讨者,向同情者露出支离破碎的尊严和灵魂,无一例外的只要一样赤裸裸的东西——钱!可他不是乞讨者,而是一个拾荒者。在这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他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每天不停地在这些抛弃的物品中寻找到能换成钱的东西,然后再用钱来获取可怜的面包与些许的温暖!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姓什么叫什么。他竟牢牢地占据了我心里重要的一角,我又翻箱倒柜。我找出了件旧毛衣,旧毛裤,一床用过的被子,包扎好。我只希望:在这个冬天,他不觉得特别寒冷。至少,内心温暖。
显然,这段时间,他把这个拐角作为了固定的居所。只要路过就会看到他。但凡提垃圾,总要努力找点东西给他:玻璃瓶,塑料瓶,废报纸,包装袋,纸盒,甚至藏了好些年的杂志。我还在单位的收发处顺手牵羊地拿过几叠报纸,回来后给他。下午,他多半坐在拐角的檐坎上,周围寂寞而冷清,风肆意蛮横,雨冰冷无声。看到我,他就像看到老朋友似的对着我憨憨地笑。他沟壑纵横的脸上,留下太多的苦难、艰辛的痕迹,但他的眼睛明亮,平静如水,清澈干净,没有欲望、恐惧、不安、乞求、自卑,看不到一丝丝的悲伤与愁苦。有一天,少见地出了太阳,显得有些病恹恹的阳光从街背后的高楼间投射过来,我看到他坐在那团有限的明亮的阳光里,像坐在一团有限的温暖的幸福中,手里拿着一副扑克牌,一个人饶有兴致地玩着,眉眼间充溢着满足的笑意……
一转眼,春节快到了,天气还是那样冷,但到处洋溢着节的气氛。街边挂起了红灯笼,行道树上挂满了彩灯。街上的城管和环卫工异常忙碌起来,住的楼下的那段烂泥路也铺了层灰沙。习惯性的,提着垃圾到拐角处,却没看到他。旁边的清洁工撇撇嘴,有些得意地说:被撵走了!县里在“创国卫”,过几天省上要来人检查,街上的那些疯子流浪汉都撵走了!
我有些失落。他靠过的那面被烟熏火燎过的墙上,留下一些杂乱不堪的字迹:广东男性丝虫电迷药本地办证你死定了你为什么要样对我。这些字或大或小,重重叠叠,东倒西歪,少一字多一划,吃力费解,一如杂乱的生活,失序的日子。这些盲点,居然没被清除!
一阵冷风吹来,我打了个寒战,几片枯叶无可奈何地飘零在地上,要不了多久,它们就会被清理干净,化为尘与土。
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