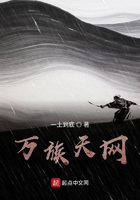真的,我也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家了。你说。
一声喟叹,轻烟似的飘散。在婆娑的光影里,看不清你镜片后那双黯然的眼睛。明明灭灭的霓虹灯闪烁着,跃入清澈的小河;河堤边的垂柳那纤纤的柔枝,快要垂到了河面上、地上。它是在寻找自己的根呢,你想。它的根就在咫尺的地之下。
眼前的一切,熟悉而又陌生,亲切而又伤感。河水,幽幽的淌着;风,带着点点冬天的寒意。风还是这风,河也还是这道河,一如十八年前。可这还是十八年前的风,还是十八年前的河么。你摇摇头。走在这曾经熟悉的大街上,儿童相见不相识,谁知道你是这里的故人呢!
你撩了下额间的发,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已是腊月了呢,可已透出早春的气息了,路边的法国梧桐虽然挂着枯叶,但枝上已有无数的苞了。而此时的高原,依然是北风卷地,大雪纷飞,冰天雪地,银装素裹,一派严寒。和那里相比,这里简直是春天了。
根儿在这里出生,拉萨长大,成都读书。你说。
身边的孩子,站着像棵树,早成了大男孩。
根儿是孩子的乳名。他是第一次回老家,看爷爷奶奶、看外婆。
你双手抱在胸前,似乎有些冷的样子。左手的腕上戴着串藏式风格的手镯。十八年前,离开脚下的这块土地的时候,你心里长满无助与无奈的荒草。什么是故乡,那是最初创造你生命的地方啊。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弱女子,如果不是故乡给你太多伤心的记忆与现实的痛苦,怎么会选择背离,怎么会选择漂泊,这是养育了你一二十年的土地啊!是的,从此,你成了朵漂泊的云,而且是朵漂泊得最高的云。你抱着还不满一岁的孩子,与丈夫一道,毅然踏进雪域高原,来到了离天最近的地方。
我理解你为何选择了西藏。深情的弦子。热情的锅庄。皑皑的白雪。飘动的经幡。洁白的哈达。如茵的草原。琅琅的梵音。成群的牛羊……那里远离世俗的藩篱,远离尘嚣的烦恼。那是一个可以让你的灵魂诗意地栖息的地方,你的思想可以像苍鹰一样在那高远的天空自由飞翔。
可是,那不是我的家。你说。你喝了口杯中的茶,然后又冲了开水。茶叶舒展着绿色的纤细的叶,在杯中翻卷着。细密的心思,像这茶叶一样,在水里悄然打开。
生活不就像你杯中的茶吗?苦涩与清香,只有自己去品尝。一个弱女子,在异域他乡生活,要经受多少常人想不到的种种艰难啊。身体的不适,语言的不通,习俗的不同,生活的压力,创业的艰辛。这些,你是怎样过来的,你没说。岁月是最好的疗伤药。那块陌生的土地接纳了你,包容了你。在那块朴实的土地上,你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得到了人们对你的敬重,实现了你的价值。可你的根呢,你的根在哪里?
人间天堂,那是对旅游者和观光者说的。你去生活几年看看。人不是生活在天堂里,而是生活在尘世中。你说。
当初,你仅仅是为了逃离那个叫故乡的伤心之地。岁月,还是岁月,它可以慢慢抚平你的怨恨与忧伤,也会渐渐销蚀你的容颜,使你曾经青春的额上长出衰老的枯藤,但它永远不会风化你不变的乡音。虽然你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但酽酽的酥油茶,怎能取替故乡余味悠远的春绿,甜甜的青稞酒,怎比得上故乡那千年的五粮醇酿。虽然高原上的人热情、淳朴、开朗、乐观,同事对你敬重、友好,但你很清楚,你永远是一个异乡人,那里注定不是你最后的家。随着时光的悄然流逝,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感在你心中像藤蔓般潜滋暗长,缠来绕去。那种情感啊,就像无孔不入的水,或是空气一样,在你的心神稍一松弛的刹那,渗入你的思想,潜入你的梦里。你常常站在那个叫思念的巷口,越过茫茫的雪域高原,眺望着故乡的屋檐。故乡的风景在你视野里模糊、消瘦,故乡的风物在你的梦里却越来越明晰,越来越丰满。起伏绵延的翠竹。崎岖蜿蜒的山路。简陋的教室。高大的黄桷树。如豆的煤油灯。暮色满头的母亲……当草原上的格桑花开的时候,故乡早已是草长莺飞,柳絮轻扬。那满山的梨花,正挥洒着肆意的白。那遍野的油菜花,正喷薄出熏人的黄。当高原上大雪纷飞的时候,故乡依然翠竹葱绿,流水潺潺。故乡永远是温暖的,故乡的冬天是很少下雪的,最多也只是下点雪米子,盈盈地沾在衣上,像撒下的白糖。故乡是你永远的伤与痛。
你欲归去,但不能归去。一个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去了的,怎还走得回来呢!
那么,哪里是你的家呢,家在何处。
和大多数进藏的内地人一样,你在成都买下了住房,把孩子送到了成都读书。每年的假期,你飞到成都度假。成都就是我的家吗?你说。
你不过是那个都市里的一个新客。没有亲人,亲人在故乡;没有朋友,朋友在高原。在那个陌生的都市里,住在对面的是陌生的面孔,走在街上的是匆忙的脚步。你是谁,从何处来,没人知道,人们也不愿知道;他们是谁,往何处去,你不清楚。人生太繁太累太沉重,短暂的假期,你只是躲进成都那个叫家的屋子里稍憩片刻,一家人熙熙然地享受天伦之乐。然后,又独自去高原,抵御那繁华的寂寞。
杯里的茶凉了,茶叶静静地躺在杯底。
我们站了起来,然后握手,告别。
你是一朵流云,一朵雨做的云,在十八年后的一个暖暖的冬天,你飘回这个叫做故乡的地方,撒下一场淋漓的雨。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