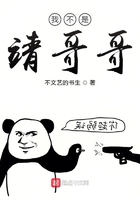鱼涣之卧床一月有余,鱼小少爷收拾着燕京市场的烂摊子抽不开身,大燕皇室公开向鱼家借下巨笔军费,燕军方才备齐了粮草出师西渝。
不足一月,楚元修率领的燕军便让西渝退兵三十余里,捷报频传,大燕举国欢庆,仿佛九年前的老定王爷又回来了一般。然而,事情终于演变成了燕皇最不想看到的局面,楚元修获胜之后,借口西渝尚未下降书求和,并未打算马上启程班师回朝,只是久久驻兵大燕西境蒲阳地区。
楚元偖派去传旨的人一波一波地从不见回来,就连磬阳长公主写给平侯南宫懿的家书也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眼见就快到十月,楚元修依旧没有班师回朝的意思,楚元偖夜不能寐,急火攻心之下生了一场大病,起初咳血不断,后来渐渐卧床不起,一连好几天都没来上朝。
储君未立,燕京恶钱刚止,夺嫡风波又起,朝堂乱作一团,大燕岌岌可危。
楚元偖躺在龙床上,气息微弱,目光滞缓,一袭凤袍的连湘云立在床头,目光冷冷,面无表情。
许是今年的秋天比往年来得更浓,冷冷清清的寝殿里灯火通明,明黄色的稠帐映着摇曳的烛火,忽明忽暗。
“云儿……云儿……”楚元偖断断续续道,一声一声地,口齿含糊。
连湘云并不动容,转身端起桌上的一碗汤药,淡淡道:“皇上该喝药了。”
“不要,朕不喝!”楚元偖厉声道,混浊的眼睛里满是恐惧。
“皇上要听话。”连湘云停下脚步,眼里晕起一层薄雾,冷笑道:“以前臣妾多听皇上的话,皇上说什么便是什么,臣妾什么都依,当初连家满门忠烈,不就是因为太听皇上的话了,才落得这样的下场?”
“你都知道了?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楚元偖瞪着眼睛,言语措辞显得艰难又混浊,“所以……所以你就亲手杀了朕……朕和你的孩子?”
“是!”连湘云眼泪再也止不住,凄凉地狂笑,“我就是要杀了你们楚家的孩子!九年了,臣妾没有一日睡得安稳,一闭眼,哥哥就会浑身是血地站在臣妾面前,质问臣妾为什么不救他,为什么不救他的孩子,为什么还要这么屈辱地苟活于世?臣妾怎么配做连家的人?皇上当初就应该连臣妾一起杀了!”
“不,不,”楚元偖眼角淌下一滴泪,道:“朕不会杀云儿的,云儿是朕一辈子的皇后,是朕的发妻,朕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云儿,朕怎么会杀她?不会,不会……”
犹记得少年时期,楚元偖的母妃是最得宠的妃子,却不是皇后,母妃一贯低调,从不惹是生非,也从不允许他卷入皇权斗争之中,饶是如此,当时的皇后依旧视她为眼中钉肉中刺,几欲除之而后快,母妃日防夜防,终是被皇后陷害,母妃百口莫辩,帝王无情,一条白绫赐死,母妃死得那一日正值隆冬,漫天的大雪纷纷扬扬,他在殿门外跪着,冻得瑟瑟发抖,父皇和皇后出来时眼睛都没朝他这边看就扬长而去,后来母妃再出来时,只一条破席裹着,一只惨白的手从缝里耷拉下来,摇摇晃晃,毫无生气。
那一年,楚元偖十五岁,忽地对这世界充满了绝望。
他拖着冰冷僵硬的身体在大雪中盲目地行走着,冷风像刀子一样戳着他的脸,把他的心都冻结了,就在这时,面前突然跳出一个穿着大红袄裙的小姑娘,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问他:“小哥哥,你冷不冷啊?”
他当然冷,目光都是冷的,整个世界也是冷得银装素裹,这抹红色却在他的眼里心里都亮了起来,像一团跳动的火焰,条件反射一般,他将眼前的小火球紧紧抱在怀里,眼泪噗噗噗下落,小姑娘起初一惊,正要反抗,那滚烫的泪就顺着她的脖颈处往里边滚,一颗一颗地,把她的心都烫化了,到底是怎样一种难过才能把一个人变得这样软弱啊?
小姑娘伸出小手一下一下地拍着他的背脊,口里喃喃道:“不哭不哭,谁欺负小哥哥了,湘云给哥哥报仇,湘云好厉害的……”
楚元偖再看眼前的已为妇人的连湘云,目光清冽绝望,再不似当年那个目光灼灼的小姑娘,他仇恨过世间万物,唯独在她面前,他心里才是饱满炽热的,无论他曾经为皇位怎样的十恶不赦,在她面前,他都是那个抱着她闷声落泪的少年,双手沾满的血腥一扫而空,所有的野心和仇恨也都变得淡了,守住她,便是守住他冰冷的人生中最后一丝温存,然而就连这最后一丝温暖,也终究被他一手毁了。
他和湘云的孩子,他是喜欢极了的。可连家能靠军功封王,又和定王府走得这样近。他们若反,他根本招架不住,所以,他费尽周折的铲除了定王府和沐王府,就是为了他和湘云的孩子能够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成长为大燕最优秀的继承人。
只不过这些连湘云不知道罢了,像是感慨,又像是无奈,他叹息一声,在空旷的大殿里连回声都不曾有。
然而,有些事他也不知道,连湘云自登基之初便嫁给她,先后流产三次,前两次是遭人毒害,最后一次是九年前,楚元偖早有了防备之心,衣食都是自己亲自差人照料,旁人没有可趁之机,所以他才推测是连湘云亲手杀了他们之间的孩子。
可有时候,宫里的人杀人根本不需要动手,他们只需要张一张嘴,把远在北境之外的连家人的死讯蜿蜒曲折地告诉她就行了,尽管楚元偖瞒得密不透风,但一个人若有心告诉你,自会有千方百计。
只是起初她觉得那是一场意外,她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的哥哥一家的不幸而难过,这种难过足以让她在临盆的时候因为剧烈的痛苦而难产。
楚元偖那么喜欢她,在问保大还是保小的时候,自然而然的选择了保小。
连湘云不是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她在皇后的位置上坐了那么多年,又亲身经历了楚元偖的夺嫡之路,自然清楚沐王府和定王府的垮掉意味着什么。
等连湘云把一切都想明白的时候,不觉得那是一场意外的时候,她突然觉得,也许那个孩子根本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个孩子,兴许连城和连奚就不会死。
所以她对向她泄密的淑妃只字不提,流产也成了一个意外。
“为了臣妾?皇上是为了自己!你怕臣妾生下孩儿之后会被连家逼宫,你怕你沦为和你父皇一样的下场!”连湘云泪流满面,她端着药碗一步一步地上前:“皇上记住,云儿早就死了,九年前就死了,臣妾是连家的长女,将门之后,连家的仇,由臣妾来报!”
哐啷一声,寝殿的门突然被打开,一身紫衣的楚君琟走进来,连湘云身子一颤,心里突然松了口气。
那是他,她爱了那么多年的偖哥哥,他做了那么多罄竹难书的恶事,她依旧于心不忍,真是可笑。
“皇后娘娘您忙您的,君琟就是进来看个热闹。”楚君琟云淡风轻地笑道。
他看也不看躺在龙床上的老皇帝,斜斜地坐在一把椅子上。
淑妃心思深沉,所以她生下的孩子也深藏不露,明明是楚君瑞发动的宫变,为什么会半路被楚君琟截了胡?这一点连湘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
“你交于本宫的事本宫都做了,现下是否可以放了瑞儿了?”她说道。
“这也算做了?”楚君琟一怔,有些吃惊道:“父皇死了?”
“混账!”楚元偖有气无力地骂道。
“这不是还没死嘛!”楚君琟呼了一口气,做出原来如此的表情来,然后起身走过去。
龙床上的楚元偖气息奄奄,眼睛死死盯着他,像是要盯出血来。
“逆子!”楚元偖又骂道。
“诶,父皇,您怎么还活着?”楚君琟探着脑袋好奇道,他俊美的脸上满是邪气,突然扑哧一声笑出来,轻声道:“父皇可别忘了,逆子,混账都不是人生的,父皇是混账,才能生出儿臣这样的逆子来。”
“你……”
楚元偖气得浑身发抖,现在的他既老又衰,苍老惨白的脸上发起狠来半点没有骇人之色,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身体会死,会腐烂,会一点痕迹不留就消失在这个世上,但他仍然有着作为一个帝王不容侵犯的尊严,一双嶙峋的手死死抓住盖在身上的锦被。
“啧啧啧……”楚君琟叹口气,道:“皇后娘娘,您快动手吧,瞧把父皇给急的,做皇上做到了这个份上,真是可怜……”
连湘云僵持着犹豫在原地,她还是下不了手。
“给我!”楚君琟见此,颇不耐烦地抢过她手里的药碗,正准备亲自动手又停下来,啪地一声摔在地上,道:“都凉了,父皇怎么能喝这么凉的,端碗烫的来!”
“你这个疯子!他是你父皇啊!”连湘云怒斥道。
“疯子?”楚君琟邪魅的脸上皮笑肉不笑,道:“皇后娘娘,天下人都知我楚君琟是个疯子,我可不能空担了这样的骂名!”
楚君琟恶狠狠的,一字一顿道,“本皇子说要烫的,皇后娘娘听不懂人话啊?!”
“不,不用了,我来!”
连湘云说罢,扑到老皇帝身边,掀起锦被死死捂住楚元偖的脸,楚元偖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蹬了几下腿,便再也没有动静了。
连湘云紧咬着牙,眼泪簌簌地落着,巨大的痛苦将她拖进深渊,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吧,偖哥哥,下辈子我们再不要牵扯进这么多的是非恩怨中了,再也不要这么痛苦地活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