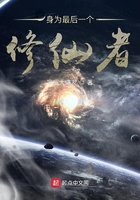三天后,柳杨来到了咨询室。
明白我的意图后,她把自己所知道童海明的情况及其家庭成员的情况告诉了我。
童海明生在西安,长在现在的城市。父亲是一个当地有些名望的学者,母亲是市政府的一名中层干部。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比他大七八岁,先是在国外留学,后就在当地结婚定居。童海明出生后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他,都是姐姐带他玩,姐弟俩感情非常好。在童海明十二三岁那年,姐姐到国外留学去了,这对童海明来说是个挺大的刺激,好长时间打不起精神。平时父母上班,家里由爷爷照看着。童海明从小任性、淘气,除了姐姐外谁也管不了他。想干什么如果做不到就撒泼打滚、摔东砸西,弄得大家谁都没有办法,结果是为所欲为。稍微大些,淘气就更没边儿了。姐姐走时他刚上中学,家里没人管他了,简直无法无天,甚至为了与同学玩都不回家睡觉。为此父亲打他多次也没用,以至父母看着实在没办法也就放弃不管了。参加工作后有时十几天不回家,家里也不找他。这次离家出走四个多月没有消息,父母也没有很着急。
童海明本人身体很好,在体校踢足球,没有听说得过大病;但家族中却不太理想。据说姥爷、爷爷和父亲都有较重的嗜酒癖好,本人也非常能喝酒。据他自己对柳杨说,姥爷和母亲都有精神病史。在“****”期间,在市政府工作的母亲受冲击得了精神病,后经住院治疗没有严重的影响,至今身体还好。另外,其姨家有一个女孩听说精神也不正常。姐姐身体也很好,家族成员中没有其他重大疾病史。
在交谈中,我发现柳杨虽然性格内敛,说话语速不快,但行事却比较急躁,办事认真,有一定的操控欲。可以看得出她对丈夫是很爱的,为了丈夫可以做一切事。
在谈到童海明自杀行为时,她说自从丈夫回来后一直没有涉及这件事,她也不敢提,惟恐刺激了他。但是柳杨却提供了另一件与自杀有关的事情。
一年多以前,那时童海明的情绪已经很糟糕了,夫妻俩人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正赶上柳杨身体不好,童海明也没有时间照顾妻子,于是建议妻子到西安姐姐家休养一段时间,那时柳杨的母亲也在西安。柳杨理解他的感受,前去姐姐家治疗养病。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柳杨的身体好转,也惦记着丈夫,几次电话商量回来,但都被他拒绝了。情急之下童海明甚至告诉柳杨,如果不经他的同意回来,他就从十五层楼上跳下去。就这样,柳杨在娘家一住就是十二个月。终于有一天,柳杨在没有与他打招呼的情况下回到了自己的家。也是机缘巧合,当时他并不在家。进门来,柳杨看到家里一片狼藉,到处是灰尘,脏衣服堆在地下,桌子上、墙角里扔着方便面的包装,床上的被子黑黑地团在那里,这哪还像个家呀!
很晚童海明回来了,惊诧地看着妻子,然后就暴跳如雷,叫喊着“你是不是真的希望我从十五楼上跳下去啊”,柳杨莫名地看着他。因为她早已忘记丈夫曾经说的这些话,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要冲出家门,被柳杨死死抱住。渐渐地他平静了一些,开始打量已经被妻子收拾整洁的房子,一股悲哀涌上心头,紧紧抱住妻子放声大哭,为自己的无能、无奈大哭。
从柳杨这里所了解的情况看,虽然童海明自杀经过尚不明了,但其家族中多位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例,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我把担心告诉了柳杨,并建议她陪同童海明到医院精神专科作检查。柳杨说,在童海明离家出走前半年,她曾陪丈夫到西安某大医院的心理科做过咨询,但他坚决不同意去精神科检查。在医院他与心理医生发生对峙,感觉医生是在压服自己,进行辩驳,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医生借故离开,童海明仍等在那里期待继续辩论,直到其他医生询问“你还有事情吗”,这才离开医院。
我问柳杨那次医生是否给他开药了。柳杨回答医生开了许多药,可他吃了没几天就嫌麻烦不吃了。
我问是否还记得是什么药。她回答说只记得有“碳酸锂”和“奋乃静”,其他的不记得了。
听柳杨说了这些后,我心里更加感到沉重。在精神科用药中,这两种药都是给精神兴奋或有躁狂性质的病人使用的。从医生用药的品种来看,我也怀疑童海明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抑郁症了,恐怕已经不属于心理治疗的范畴了。
这么多年来,在咨询中只要是来访者表现出较多的精神病性的特征,我必感到内心沉重。客观说,我也知道自己的这种感觉来自何处。
记得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家隔壁的院子里住着一男一女两个“疯子”,年龄相仿,估计在40岁左右。可巧的是他们有着某种亲戚关系,至于是什么样的关系我那时搞不清楚,现在就更搞不清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那两个“疯子”许多年无论冬夏,总是穿着一身露出棉絮的破棉袄。夏天我穿着裤衩、背心在街上玩,满身大汗,热得不得了;那两个“疯子”穿着那身破棉袄,把扣子解开,依稀可以看到破棉袄上被汗水湿得一片一片的汗碱圈。每次我都想:他(她)多热啊!那时北京的冬天寒冷无比,可以看到被冻裂的土地,我穿着棉衣、棉裤和“棉猴”(一种戴帽子的棉大衣)上学都冻得哆嗦;有时在路上可以看到他或她,依然是那身破棉袄,在风雪中缩成一团,躲在哪家大门的门洞里。那时我的心就似乎变得很重很重,赶紧用劲儿裹紧大衣跑开。这种情景我好像见了五六年,直到我都快小学毕业了,有时还能见到他(她),后来不知道何时就再也看不见了。但当我每每在咨询中遇到怀疑这类疾病的个案时,我的心就不免变得格外沉重。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与童海明再做一次交流。之所以这样做的内在动力我清楚:要么是想弥补上次自己的过失,要么是想核实真实的情况,要么二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