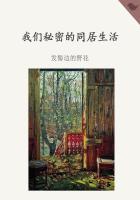三岁那一年,我被查出患有先天性的重度色盲症,从此只能分辨黑白两种类别的色系,我的世界开始变得像家里那台黑白电视机一样,暗沉的没有一丝生机。
六岁之前,我并不觉得这样的色盲症对我有多大的影响,那会儿我只知道爸爸妈妈和邻居的叔叔阿姨们说“狼来了”,我会害怕,除此之外,我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怕的。
六岁开始,我上了学前班,对一切新鲜事物都觉得很好奇,我没有像那些孩子们一样,对于第一次上学而感到恐慌,我显得非常兴奋。那一天早上,我起得格外的早,妈妈领着我去上的学,我几乎一路上都是蹦蹦跳跳的,妈妈提醒我不要摔倒,可我显然没有顾忌到这些,然后摔了一个马失前蹄,手上被磨了一点皮,出一点血,黑色的。
可我没哭,笑着告诉妈妈:不疼不疼。
十多分钟的路程,我总算到了学校。妈妈看我进了班级,老老实实的坐好之后,才放心走开。
学前班的学习生活很好玩,我的成绩一直都挺好,除了美术这门课我从来没有及格过,其他的我都是第一名。
那一天,美术老师叫我们画自己想象中美丽的世界。我周围的小朋友们都带了很多彩色的蜡笔,他们画的天空是蓝色的,河水是绿色的,花儿是红红的,太阳公公露出微黄色的笑脸,而我画的世界,天空是灰暗的,树木是黑色的,河水泛着煞白的光泽,我觉得美丽极了,老师一定会给我高分,第一个上交了我的作品,然后得意洋洋的坐回了座位,显得很神气。
第二天,老师公布昨天美术课的成绩,我的画纸上刺眼的印着鹅蛋般的黑色零分。课间休息的时候,同桌嘲笑我,同学们都跑来看我笑话,大声的喊着:快来看啊,快来看啊,今天有人回家可以吃鹅蛋了。
我捧着自己得意的作品孤零零的回家,一种不被理解的嘲笑让我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居然还有比“狼来了”更可怕的东西。
我小心翼翼的拿着作品回家给妈妈看,问妈妈:为什么我画的画总是零分,为什么我觉得同学们画的作品根本没有我的好,可是分数永远会比我高。
我清楚的记得,妈妈那会儿的眼睛闪烁着一种晃动的光芒,她告诉我:老师们不懂,妈妈给你一百分,然后在我的背包里找出了黑色的圆珠笔,在画纸前面添加了一个1和0。
妈妈为了不让我伤心,以后没有再让我去学习画画,可我因为那张画纸被改动过的100分,却开始偷偷喜欢上了用画笔涂抹世界的感觉。每一个晚上,我总在妈妈和我说完晚安之后,偷偷爬起来,坐在小桌子上,画着一些奇形怪状,天马行空的图案。
我一直相信造物主是公平的,因为上帝再给我关了一扇门的同时,又给我开了一扇窗。虽说我看到的世界总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忍受着太多的嘲笑,可我的文化课成绩一直都在学校名列前茅。
高中以前,我最怕的就是学校每年安排的体检活动,身边的每一个同学都是健健康康的,唯独我在他们之中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每一次测色盲的时候,身边总会围着一群看热闹的同学,他们总戴着有色的镜片看我怎么出丑,看我认不出圆圈里印着的数字,看我像个哑巴一样在哪儿傻傻的站着。
这样的一切都没有击败我,每天晚上在做完功课之后,我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偷偷的把今天发生的一切都画在白纸上,黑白的基调,不规则的图形组合呈现出一个扭曲的世界,一个非比寻常的社会。
高考结束的时候要填志愿,我因为严重色盲的缘故,很多自己喜欢的专业被限制,最后选择了中文系的专业。
上了大学,周边的朋友们总是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出门走山玩水,而我除了看书和画画之外,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以至于,我显得很不合群,变得越来越沉默。
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图书馆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我喜欢那种读书时候世界静止的感觉,白纸黑字也是我看到的最真实的世界,我知道在这里没有人会嘲笑我。
晚上,室友们都在上网玩着游戏,游戏的声响几乎每天都要持续到凌晨一两点之后才会结束,第二天有课的情况,也都一个个无所谓,逃课对于一帮大学生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的事情。可我似乎对游戏和上网从来不感冒,尽管他们的吵闹声很大,可我还是会独自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把白天看过的书,转换为一个个别人看不懂的图画,然后给它起名字。
三年如一日,我的大学基本上就这么度过了,室友们的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而我却依旧守着那张小时候妈妈给我改的100分画纸和当时用的铅笔。
岁月没有让画纸变得枯黄,或者说在我的眼里枯黄也是灰白色的吧。我看不到岁月留下的任何改变,妈妈的头发永远是乌黑的,爸爸的胡渣也是,听妈妈说家里最近又换了大彩电,可对于我来说,黑白电视机和智能彩电根本没两样。
大学上到了第四年,平常游手好闲惯了的同学们开始渐渐收了心,似乎一瞬间就业的压力就摆到了他们的面前,焦躁感开始在他们的眼里泛滥,每天清晨都要整装出门去各种人才市场应聘,直到晚上十点多才能回来,这段时期,他们基本上早上朝气勃勃,晚上回来就是死气沉沉,摊到在床上。
没了游戏里的厮杀声,宿舍安静的可怕,我有点不太习惯。
看着所有的人都在为了未来努力奔波,我不知道哪里来的沉着冷静,还是像大学的前三年一样,读书写字和画画,一如既往。
毕业前的三个月,也就是那一年的二月底,春天刚刚来,他们说世界五颜六色好看极了,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关于超现实主义的艺术类读本。我看了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然后花了好几个夜晚画了一副极为抽象的画作,一不小心把画纸夹在了那本借的书里面,一并还给了图书馆。
很不凑巧,刚还给图书馆没多久,这本书就被一个艺术系的女生给借走了,很显然我的那副极其扭曲的图纸勾起了她的兴趣,于是,她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到处打听,上期的借主是谁。由于当时借书都必须是用自己的学生证借的书,查到我的班级和姓名并不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
可我并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的联系方式。那年三月七号的早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一个细声细语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同学,你是不是上次借了一本关于超现实主义的美术类书,里面你不小心夹了一张图画。有时间出来吗,我把它还给你,顺便想请教你几个关于这幅画的问题,可以吗?
我当时脑子没有想太多,就一股脑的奥了一声。
约在了学校的陶然亭,旁边就是湖光山色。
平常与我接触最多的除了方块字和黑白线条之外,就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了。与一个陌生女生见面,我显得极度不自在,听她后来和我说,我的脸红的很厉害,当时还以为我脸上抹了油彩。
我告诉她我的经历,告诉她我根本不知道红色是什么样子的,我只能看到黑白两种色系。我告诉她我的整个童年都是灰白色的,告诉她我的身边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们总是戴着有色的眼睛观望着自己,就像是在看一只猴子。
她眼睛里突然开始泛着闪烁的光芒,就像六岁那一年妈妈给我改掉零分时候的场景一样。我不确定那是同情的眼泪,还是眼睛被风吹的缘故。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每天都会把这个世界里五颜六色的故事说给我听,告诉我红色用什么音阶代替,黄色又用什么音阶代替,而我总是把前一晚画的画带给她看,告诉她另外一个角度里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我清楚的记得,那段时间陶然亭旁边的小山头上,雨过天晴之后,总会浮现出一种七色的彩虹桥,她用好听的声音读给我听,就像一首动人的歌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头。
突然想起来,这位姑娘的名字还没有告诉你们,她叫贾若梦。
这样美好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毕业离开学校,中间断断续续我也找过一些工作,可是都做的不太长久。后来,我把自己十几年积攒下来的作品同时投到很多家美术类的杂志社,原以为都会石沉大海,没有想到我收到了其中一家画社的电话,对我的作品大为赞赏。对方是一个女生,声音就像贾若梦一样好听,某一刹那,我真恍惚以为这是她来的电话。
可惜,不是。
贾若梦走了,毕业之后就去了远方,她说她的心不在这里,我问她会去哪里,可以在哪里找到她,或者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她说,只想一个人多走几年,积攒一下素材,有缘我会来找你,就像当年那封无意之间在图书里面发现的画纸一样。
我没再多问,然后我们各自上路了。
画社联系到我,给我办了画展,给我重新包装,给我的画作赋予很多种高深莫测的定义,把我美化成身残志坚的艺术大师,称我为当代的毕加索,将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和扭曲的世界观表现的淋漓尽致。
所有人都投来了鲜花和掌声,把我捧到了天上,可我只不过在画我眼中真实的世界罢了,我想的也远没有那么复杂,这一切,只有贾若梦能够读懂。
如今好几年过去了,我都没有找到她的踪迹。后来,在每一个雨过天晴的午后,我都会下意识的抬头看一看天空,黑白色的世界里,我总能看到天空中的那扇彩虹开的好看极了,五颜六色的就像一首歌传进了我的心底。
遇到她,就像遇到她的名字一样,假的就像做了一场好长好长的梦,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愿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