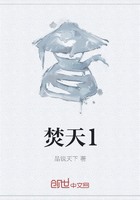次日,山中的鸟儿将司空豹吵醒过来,那时日也高升,年青镖师慌忙从床上爬起,推醒睡在旁边的司空虎,原来他兄弟两个被安排同住一间房,云中林却睡在另外的房间里。
司空豹揭去司空虎的被子,喊道:“快起了,大哥,怎地睡得如此沉,咱们去看看四爷起床了没有,原说好清早就要上路的。”司空虎睡眼惺忪问道:“天亮了吗?”
司空豹道:“早大亮了,看样子也是日上三竿,不知怎地竟睡到这个时辰。”
司空虎爬起来,一边穿衣一边说道:“昨晚睡得可真香,想是一路太累了,几日不曾睡过这等好觉,还得感激人家江少爷。”司空豹道:“别哆嗦了,先去看看四爷再说。”
当他两兄弟敲响云中林那间房门时,里面没有回声,司空豹急得大喊:“四爷,你醒了么,该上路了。”不见有人答应,司空豹抬脚踢门,又喊了几声。还是没有回音。
却见那身着白衣书生装扮的太子走了过来,司空豹忙问道:“江少爷,我家四爷睡的可是这间房?”太子道:“是呀,怎么?难道四哥还没起床。”司空虎道:“是啊!是啊!我们得叫四爷上路了。”太子拍门道:“四哥,天大亮了。”同样没有人应。
太子奇怪道:“这么久不见动静,莫不是夜来出了什么事?”
司空豹闻言大急,早飞起一脚,那扇房门被踢得歪在一边,开了。
看到房门破损,太子心里有些不悦,却又不便多说什么。
三人鱼窜进门,见云中林衣衫未解,仰面躺在床上,怀中抱着利剑,双眼紧闭,面皮鲜红,头发根部冒着热气,浑身大汗淋漓,犹在沉睡。司空豹见状大惊,飞身扑了过去,拼命地摇晃云中林身子,云中林仍然睡意浓浓,不见醒转,司空豹急得哭出声来。
司空虎同样十分焦急,急走到床边,伸手探了探云中林鼻息,说道:“不哭了,豹子,我看没事的,四爷他可能是路上感染了风寒,估计病了,正在发烧呢!问题不大。”
司空豹收了泪,盯着太子,怪声说道:“我家四爷体壮如牛,他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生起病来,我看这其中必有缘由。”太子生气道:“豹兄这话什么意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吃五谷生百病,这是平常道理。你不会告诉我,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这能有什么缘由,既然四哥病了,找名医诊治就是了。两位其实也用不着如此慌急。”
司空豹哼了一声,跑出门去,很快弄来了一盆冷水,劈头盖脸地给云中林泼了下去。
司空虎喊道:“豹子,你疯了么,怎能如此粗鲁!”
经这一下刺激,云中林终于睁开了眼睛。
司空豹喜道:“四爷醒了。”云中林双眼瞪着太子,直瞪得太子有些不自在起来,讪讪问道:“四哥,你怎么啦!”云中林有气无力地道:“我想我是生病了。”
太子好言相慰:“不碍事,小弟庄上有最好的大夫,他们会让四哥尽快康复。”
云中林动了一下,想翻身爬起,一时却使不出力,骇得脸色都变了。司空豹忙来扶他,云中林摇摇头,虚弱地说道:“小豹子,快、赶快和你哥去接应三爷,我现在头昏得紧、全身乏力,这病来得不轻,怕一两日是起不来了。”司空豹哭道:“不行,我们不能丢下四爷不管,你就算杀了我们,我哥俩个也不会走。”司空虎跟着嚷道:“不走,我俩兄弟得留下来照顾四爷。”云中林急道:“这是命令。”他一心急,一口气转不过来,竟又晕了。
在东进的路上,在那一座接一座的群山之间,有那么一片长达百余里的野草地。
草地像蛇一样,匍伏于高低起落的崇山峻岭中,蜿蜓地伸展开去。这片草地一年四季流淌着发臭的污水,就算是烈日当空,火红的娇阳也晒不干那草根底下的污泥。
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片草地才叫做烂泥湾。
不过这一带倒是沃野千顷,良田万亩。远处山坡上的梯田里,稻子成熟了,在晴空下放射着一道道金灿灿的光芒。阳光下,成群的农夫忙着在田野里收获一年辛劳的果实。
烂泥湾这片野草地,同时也是一条西东走向的大道,可惜由于常年聚水泥污,平时行走在这条道上的人并不是太多,因为这条道并不合适车马通行。
除非是那些真有急事的人,才甘愿选择走这里,因为由此处去山东,倒是一条近路。
可是并不是天天都有人有急事,人们出行总习惯于走那舒服的大马路。
于是这条道通常都是冷冷清清的,无论天晴天雨,每天都差不多是一个样。
牧羊人担心他们的羊群会陷进泥潭里,也不愿意到烂泥湾来放牧。
在烂泥湾出入得最多的,恐怕要数飞鸟和山禽。
这是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草地上到处隐藏着看不见的危机。
在草地即将尽头的地方,一道夕坡不得不使它绕了一个急弯,那是一道不算太高的夕坡,不过夕坡的另一端,却是绵延千里的群山。夕坡上除了错杂盘生的大批岩石之外,尚有数株参天古松,古松那粗糙的枝干,足矣见证百年风雨,因此变得更加挺拔坚强。
夕坡上,离野草地稍近一些的一株古松上,斜倚着一个身着白衣的年轻人。
只见他脚踩着这株古松的一枝旁逸斜出的枯萎枝干,背靠树身,环抱双手,双目似睁如闭,那瘦长的身躯与这株古松的枝干实在是有好些相似之处。
这人并不陌生,他就是燕雪飞。那个享誉武林的快刀手。
此时的燕雪飞,背上正背着他那柄要命的鬼头大刀,刀柄上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条红飘带。虽然他看上去悠然自在,其实精神高度紧张,他那双鹫鹰般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透过密密匝匝的针状松叶,悄没声息地关注着从西而来的那条危机四伏的道路。
在他的目光下,野草地上就算是飞起一只麻雀,也绝无可能逃脱他的视线。
燕雪飞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手,在耐心地等待猎物出现。
其实天底下最优秀的猎手也不过如此,或许还不具备他那种专注的职业修为。
同一株古松底下,有一块长满青苔的岩石。
岩石上面铺了一团苦蒿,一个妙年少女坐在苦蒿之上,她是毒观音。
天仙一般的毒观音目视天边流走的白云,正用短萧吹奏一段哀伤的曲子,娇艳如花的她仍然穿着她喜爱的红衫,她看上去忧郁而憔悴,即是如此也毫不影响她那绝世的容颜。
她的红衫边角处沾染了不少泥星,在这种鬼地方,衣衫着泥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虽然这或多或少有点让人感到美中不足,但毒观音并不在意,也许是她未曾觉察到。
这些日子里,她一直跟燕雪飞在一起,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非要跟着他。这次任务尊主点名是要燕雪飞去执行,她完全可以选择离开他的,但她没有。
她也问过自己为什么?同样没有答案,有些事本来就不需要答案。
她不否认,在她那孤寂的心中是有些喜欢这个冷漠的人。
他们是同一路人;流落天涯无依无靠的人,同样也没有家。
也许算是同病相怜吧!也许是因为同情;他的身世,他的遭遇,博得了她的同情。
不对,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她比谁都要清楚,燕雪飞从来不奢求得到别人的同情,也没这需要。如果有谁胆敢对他有那种想法,相信他知道后一定会很不开心。
她和燕雪飞相处已有一段时间了,又或许是日久生情的原因。
总之,她不想、也不愿离开他,她心甘情愿地跟随他流浪江湖。
自从万凤楼燕雪飞在狄为刀下救下她之后,她睡里梦里都是这个冷漠而无情的人,可他常常对她视而不见,不快的时候甚至粗鲁地轰她走,从没有一句好听的言语,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如果她对燕雪飞动了感情,那可真是该死,她宁愿自己爱上的是别人。
在燕雪飞的眼中,似乎从未对她产生过一丝情意,从没有过。不过她也知道,燕雪飞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家伙,或者他脸上流露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他心中最真实的想法。
也许完全有可能就是这样,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燕雪飞不是冰山。
毒观音那哀愁的萧声随风飘远,燕雪飞充耳不闻。
燕雪飞关心的,只是他的猎物,这些天来他一直小心翼翼,害怕惊动什么。
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轻易放脱猎物。
一曲未完,毒观音实在吹不下去了,自娱自乐实在没有意思。她幽伤地轻轻叹息一声,收了短萧,站起身来,抬头偷偷瞟了燕雪飞一眼,眼中又多了一丝惆怅和忧伤。
燕雪飞并不关心她的反应,他关心的只有猎物。她存不存在其实对此时的燕雪飞来讲,那也只是无关痛痒的事情。燕雪飞已经警惕起来了,因为在那野草地上出现了一支镖队。
追踪多日,猎物终于出现,燕雪飞屏住了呼吸,略微有些紧张。毒观音注意到,燕雪飞悄悄将鬼头刀拔出来了,并且紧紧地抱在怀中,她可从来没见过燕雪飞这么不自信。
过来的是一支由八九个人组成的小镖队,只有一辆镖车、走在最前头。
镖车的两旁,紧贴着两条骑马的壮汉,小心谨慎地防备着一切不测,相当专业。
镖车尽管轻便,还套了两匹马,但在这种满是泥泞的路上行走,也未免感到吃力。
当走到那些实在是太稀太烂的地方时,跟车的护卫都充当了推车的角色。
这群人践踏着草地上的泥浆,一步接一步、艰难地向燕雪飞他们藏身之处走来。
燕雪飞一动不动地斜倚在松干上,他除了拔刀之外,其实压根就没动过。
他那瘦长的躯干似乎已变成了这株古松的一个部分。
火辣辣的阳光从高空直泻下来,镖队近了,更近了。
燕雪飞终于看清了镖车顶上那面迎风招展的小白旗,旗上锦绣‘四海’二字,分外的醒目,当这两个字映入他的眼帘时,他的脸上竟然奇怪地露出些笑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