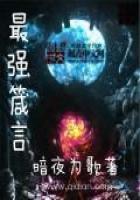然而,任何事都有两面性,有其利必有其弊。
太康帝的确成功地利用南宫宸达到了抑制赵王的目的,另一方面因为他的刻意误导,至绝大部份臣子不能准确地把握皇帝的心思。
误以为,他果然想择优立储,从而给了南宫宸坐大的机会。
最终的结果,虽然如愿立了楚王为储君,却也迫得南宫宸铤踏上拥兵自重,逼宫夺位的不归路。
当然,最后南宫宸是否成功,顺利登上帝位,她已无法得知。
想来以南宫宸的手腕和智谋,又有了杜荭从她手中抢走的金钥匙相助,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然而,今生金钥匙却掌握在她的手里,如果她反过来扶持楚王,借太康帝之手来打压南宫宸,不止复仇将变得事半功倍,事情也会变得有趣得多。
毕竟,她回到了十年前,不止清楚历史的走向,更准确地把握了帝王的心思,这就足够立于不败之地。
而此时南宫宸羽翼未丰,不管是对政事的处理的圆滑度,还是军中的威望都不够,有待他努力摸索,积累经验和加强实力。
在朝里,他虽有一定口碑,但不论是人脉和声望离众望所归四个字,还很遥远――从胭脂马一案,众臣心态可见一斑。
以后,只需比照办理,不论南宫宸如何费尽心力,她都可借力打力,轻松抹杀其功劳,令其功亏一篑!
久而久之,群臣自然不难发现蹊跷,从而准确地把握帝心,找准风向。
任是南宫宸本领通天,亦无法力挽狂澜。
杜蘅忽然有些幸灾乐祸,甚至隐隐开始期待日后的较量。
南宫宸啊南宫宸,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化解重重危机,从各种围追堵截中杀出一条血路,面北称帝,成就一代霸业?
而就在杜蘅踌躇满志,打算给予南宫宸迎头痛击的时刻,南宫宸亦度过了堪称二十一年来最离奇诡异的夜晚。
无言大师接到他的名贴后,欣然赴约。
南宫宸开诚布公,把困扰了他大半年的怪梦毫无隐瞒地叙述给无言,末了问:“以大师之见,此梦究竟该做何解释?”
无言沉吟半晌,问:“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否因殿下太过思念某人,才至怪梦频生?”
“不可能!”南宫宸断然否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女人能吸引到本王的视线,更不要说是日思夜想,思之欲狂了!”
无言想了想,又道:“亦可能是前世因果,万缘未灭,周而复始,天道轮回。”
南宫宸愣了一下,面上表情变得十分诡异,道:“大师此说,未免太过悬乎了。前世之事,如何得入梦中?”
“所谓前世因,今生果。”无言微微一笑,道:“人经生老病死,入六道轮回,转世投胎前时便该饮忘川水,喝孟婆汤,忘却前尘往事重新做人。然而,亦不排除有些意志十分坚定,或是心怀执念者,带着前生的记忆转世。此时,前世所经历的事情,往往会以梦境显示。”
“若真是带着记忆转世投胎,怎会那么巧,于现实中再遇梦境中人?”南宫宸表示怀疑。
无言很是好奇:“殿下遇着梦中人了?”
南宫宸大窘,含糊道:“梦里,我连她的长象都未看清,光凭声音哪有这么容易遇到。”
无言知他未曾吐实,也不戳穿,微笑道:“倘若殿下与她前尘未了,今生再遇,重续前缘亦不是不可能。”
“无羁之谈!”南宫宸默了一默,嘴里虽然驳斥,因一句“前尘未了,重续前缘”心跳却蓦地加快了一倍。
脑海里竟不期然地浮起一双清冷漆黑的眼睛,清澈如水,不沾一丝尘埃,却又犀利得仿佛能看入他的灵魂深处。
杜蘅,这个清冷如冰,才气纵横,却又如谜一般的女子,前生真的与他休憩相关,是以今生才纠葛不断,频频碰撞?
想到金蕊宴,她在宸佑宫外徘徊,莫名引得他心动,做了平素他想都不敢想象的非礼之举。虽然最后未能得逞,然而那一吻却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自此,他的目光开始有意无意地追逐起这个清冷的女子……
他不得不承认,她已一点一滴地渗入他的生活,开始影响他的情绪。
无言在大相国寺,见过的痴男怨女何止千万?瞧了他的神情,已知所猜不差。
遂微微一笑:“是否有缘,贫僧不敢妄下断语。但是,殿下若只是想要看清梦中女子面貌,倒也不难办到。”
南宫宸一怔,涌上狂喜:“大师有办法?”
“殿下请贫僧前来,不就是为此事么?”无言低沉的声音,隐含调侃之意。
南宫宸脸上一热,索性站起来冲他长揖一礼:“此事确实困扰本王多时,若大师能替本王解惑,将不甚感激!”
“是王爷运气好。”无言笑道:“恰逢五月十五,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可乘子时阴气最盛之时做法,助王爷窥梦境全貌。”
于是,南宫宸依无言之意,在燕王府花园里设了法坛,祭了法器,摒除了所有侍卫,沐浴更衣,焚香祷告一翻后,在园中置一软榻,闭目卧于榻上,静等子时降临。
无言则双手合十,盘腿端坐蒲团之上,口中喃喃默念偈语。
子夜,悄然降临。
南宫宸沉入梦境,再次躺到熟悉的简易木板床上,耳边是早已熟悉的女子的嘤嘤低泣。
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今夜终于可以一窥梦中神秘女子的全貌,是以一反往日的焦虑,不再急于睁开眼睛,而是安静地等待着时机。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女子许是哭得累了,起身离开。
他听到吱呀的开门声,听到了鸟儿欢快的鸣叫,和一阵细碎的瓷器碰撞发出的清脆的声音,以及陌生的男子的声音。
这是迄今为止,梦里出现的第三个人!
他一阵狂喜,竖起了耳朵。
那是个极清雅,温和的男音:“阿蘅,药捣好了,该帮他换药了。”
他一愣之后,心脏蓦地狂跳。
阿蘅,她居然也叫阿蘅!如果是偶然,也太巧了些!
许是哭了太久的原因,女子声音很是嘶哑,只模糊飘进来几个字句:“哥……不用……我……”
哥?
他微微一怔,难道外面之人是杜松?
不对,他直觉否认。
杜松他见过,绝没有这样一把好听如天籁之音的嗓子。
随即哂然一笑,这是梦,他竟然把它与现实混为一谈。
正胡思乱想,吱呀一声,门再次打开,耀眼的阳光如水般流泻进来,照得人睁不开眼睛。
女子被一团金光罩着,从外面踏了进来,慢慢走过来。
近了,更近了,先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渐渐有了轮廊,慢慢清晰,原来是个身着蓝白相间,绣满花鸟的苗族衣裙的少女。
然后,他看到的是一只青花大碗,很是粗劣,釉质很差,碗边还有一个缺口。
接着,他闻到了浓郁的药香,看到了碗里绿糊糊的草药。
身边微微一沉,她侧身坐到了床沿,将碗搁到枕边,随即一只微凉却散发着药香的小手伸过来,熟练地解起他的衣服,不经意间,指尖拂过他的下颌……
他浑身一震,这触感,这香味,何其熟悉!
他心急如焚,竭力睁大了眸子。然她的发丝垂下来,遮住了他的视线,由他的角度看过去,只能瞧见一截优美洁白的脖颈!
很快,他的上衣被剥开,露出一大片小麦色的肌肤。
他蹙眉,他的肤色一向偏白,不曾这般黑过――虽然,这种颜色看起来更健康,更有男人味,可看起来还是有点怪怪的。
尤其是,一个陌生女人正如此娴熟而理所当然地替他宽衣解带,场景就更加诡异了!
接下来,他看到了胸前狰狞的伤疤。
与痊愈后那块平滑的紫色疤痕不同,此刻的它不止红肿,还泛着黄水,散发出一股近乎死亡的恶臭之气。
耳边传来水流之声,她弯腰拧了干净的毛巾,轻柔地替他擦拭伤口。
她擦得那么细致,那么小心,仿佛那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瓷器,唯恐令它破碎。
再然后,她开始替他换药。
她拿起了刀子,一点一点剔除着坏死的肌肉,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脓液拭净,直到伤口流出淡粉色的液体才停了手。
因是背对着他,看不到她的表情,却能从她微微颤抖的手和不时滴落到肌肤上的温热的液体,感受到她的谨慎和小心翼翼。
很奇怪,他很笃定她一定是个骨科高手。可是这双手,在面对这小小的创口时却颤抖了。而他居然知道她在害怕什么?
她害怕她的每一个举动,会带给他更多的痛苦。
她,在心疼他。
心,莫名地揪得生疼。
活了二十二年,还是第一次体会到被人捧在掌心地珍爱的感觉。
终于,漫长的换药过程总算结束。
她开始悉悉簌簌地收拾起来,并且起身把空碗搁到桌上。
从头到尾,竟然没有看到她的脸!
他终于焦急起来,害怕她就此一走了之,她却温柔地握住了他的手,终于他看到了那张令他魂牵梦萦的脸!
杜蘅,果然是杜蘅!
心脏再次不受控制地剧烈地跳动起来。
然而,她又不同于他所认识的杜蘅。他说不出来,哪里不一样,明明是一模一样的五官,却绝不是同一个人。
她怯生生地凝视着他,大大的眼里盈满泪珠。
他豁然而醒。
对了,是眼神!
梦里的她眼波很温柔,带着点羞涩和怯意,全不似他熟悉的那个清冷淡漠,时刻含着冰凉警惕,拒人千里的杜蘅。
她说:“你睡了十七天,不觉得腻么?”
“你说过,等战事一了,要带我去看江南烟雨,十里荷花。你,可不能食言……”
“润卿,我好害怕,你快快醒来……”
“阿蘅!”南宫宸惊惧莫名,大叫一声,猛地睁开眼睛。
无言噗地一声,喷出一口血雾,身子一歪倒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