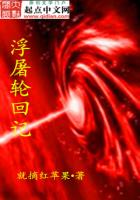古人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之前,我一直认为,摸了女生的胸部,是和******(实际上也就这样)一样的罪行,即便是无意间的碰触,也要赶快给人家道歉,然后自己谴责自己说,自己怎么这样粗心大意。我认为以上的想法,虽然也有一点禁欲主义之嫌,但最起码是符合社会规范的。而如今,自从和什么杨海诚啊,细竹姐啊,这些不知廉耻的人接触之后,我觉得自己的道德水平正在急剧下滑。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正不断地回忆着,紫胸前一团团脂肪是何等的丰满,何等的柔软,如果有机会,我又该怎样好好地爱抚。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处男的性幻想,仅仅在遥不可及的粉红彼岸——因为我还记得,来自美丽那不勒斯情考先生对我的许诺,以及那他那既高傲,但又值得信赖的笑容。尽管我相信,昨天我们说的很多话都是醉话,但最起码,我把钱给他了。妄想,希望,承诺,这些东西都是虚构的,根本就不靠谱。然而,一张张鲜红的金钱确实实实在在的:ATM机在寂静的夜里轰然作响、五张鲜红钞票的余温。记忆隔夜也会变质,只是说变质后的气味更加强烈,因此在头脑里久久不能忘怀。
此时,我竟然有点胆怯了,甚至不敢去正眼看紫。人都有这个毛病,一旦被许诺了什么,便开始朝思暮想,在头脑里设计着各种各样夸张的幻象;而当那个东西就在眼前的时候,自己反而却退缩了,事后才追悔莫及。也许真正吸引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本身,而仅仅是那种被称作“渴望”的感情而已——所谓,“旅途在出发之前最愉快”。如果此刻,我回头,看见紫正拿着快捷酒店(学校周围的圣地之一,以其廉价的小时房而声名狼藉——只要有钱,哪怕是两个初中生,都可以利用午休的功夫做点什么,而且不需要太多。)的贵宾卡,冷漠地对我说,“现在就去吧,我下午还有事儿。”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她,哪怕是让五百块钱打了水漂,我也在所不惜。
人本能抗拒着痛苦,其原因毋庸赘言;而在某种意义上,人也在自觉不自觉地抗拒着快乐——因为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是对人神经上的刺激,按照人类的归宿而言,或许平静安稳的生活更吸引人。而有的人神经很衰弱,衰弱到只能够接受一碗拉面的地步。
所以,当紫不知道为什么朝我这里俯下身子(我能感觉到,因为很明显,紫的胸部已经贴到了我的脖子上,我已经感受到,一团团柔软的脂肪在我的后颈上开始燃烧),而我也愈发地感觉到,我现在的神经有多么的虚弱。我既不惊恐,也不脸红,心脏也没有狂跳——总之,和一般的,毫无经验的纯情宅男是不同的——我此刻是另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更糟,还好紫很快就把身体从我身上移开了,否则,我真的会当场晕倒。
(而实际上,紫只是弯下腰来,拿点儿东西而已。所以关于这种感觉究竟是如何的,我想等到以后再说——我相信,以后我一定会有机会,把这种感觉讲给你们听,只要我那五百块没有打水漂的话。)
紫把小老大从桌子上拿了起来,好奇地转着瓶子,眼神里忽然换发出奇特的光芒——我相信,好奇心是人类最纯洁的情感,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掺杂在其中。所以和好奇心比起来,爱情什么的,简直肮脏得说不出口(当然,所谓“纯洁”,还是“肮脏”,在这里只在一般的用法上来使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明知看一眼也不会得到什么,但人们仍旧因此而前赴后继地遭遇不幸。
虽然小老大没有那种,比如看一眼或者碰一下就会死的设定(也不知道人们都是怎么了,有的时候什么东西一旦有了这样的特征,反而更会折磨人的好奇心),但是一个装在密闭玻璃瓶中的胚胎标本,毕竟也不是什么人见人爱的东西,而且作为一个女生(当然,在我看来,您的心智并不那么健全,少女。所以您对这种东西感兴趣,也并不奇怪)——不过,虽然这不可能,但,如果你真的了解小老大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也许我要另当别论。
“这是什么呀?”
紫双手捧着小老大,把它凑到我的面前,高兴地问我。
这突然间的一问,吓了我一跳——一方面,我神经衰弱,我承认;但是,这变化也太大了吧?
突然之间,紫的整张脸可谓lightened up,她竟然也会露出这么纯真的表情,就好像是她暗恋已久的男神,忽然送了一件可爱的毛绒玩具给她一样……嗯,这是小老大,不过,你最好还是不要把它当成毛绒玩具。搞不好,现在咱们三个的年纪加起来,恐怕都没有人家大,所以,放尊重一点,明白了么?
“它好可爱!”紫惊呼道。
没有你现在的表情可爱,少女,我打赌,就像对待任何毛绒玩具一样,你现在肯定想把小老大搂进怀里,对吧?不过呢,对于现在像小孩子一样的紫,我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紫本身仍旧是一个没长大的小孩子(当然,我也不否认,我们这些人也不比她成熟到哪里去),她仅仅是比我们更热衷于模仿,社会所标榜出的“成熟”罢了。而一个人,越是强迫自己去做出成熟的样子,也就往往越是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幼稚的一面。
而看着现在这个,褪去了一切矫饰,真实的紫,我倒是反而觉得,她没那么讨厌了。而我,也更愿意跟她多说两句话。
“为什么要管它叫小老大呢?”
哦,原因很简单,它的年纪比我们谁都大,所以势必懂的也比我们多,自然就是老大咯。但是,“小”这一点,又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就管它叫“小老大”了。
“你说,它懂的很多?”
嗯,活得久,就越成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模仿成熟的行为就算是成熟么?关键还是取决于时间。就比如说少女你吧,你拙劣地模仿着世人所谓的世故或成熟(既sophisticated),以掩饰内心的幼稚,这是我最看不惯你的一点,而且你现在在我面前已经暴露了——但另一方面,我却没有办法指责你,因为你表现出的sophistication,说到底也只能用外在的行为来界定。所以,再过几年,也许你依旧在不明所以地模仿着,但我只能老老实实地承认说,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人了——而自然,少女,你也有权利来指责我幼稚不堪,我活该这样。)
“那,他都懂些什么呢?”
啊哈,少女,你这么问,可就显得你一点水平都没有了。人究竟能够懂些什么呢?如果我说,我懂这个,也懂那个;那也就意味说,除了这个和那个以外,别的就什么也不懂了。一般,“懂什么”,往往都是“不懂什么”的托词。所以,你不应该问小老大懂什么,因为他什么都懂,所以你就不能这么问!
“那……那我该怎么问呢?”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高傲的女人(我已经强调过了,这仅仅是一种出于对成人世界的模仿而做出的,虚假的高傲,因此也就异常地让人火大,让人想要去侵犯她),恐怕认为这世界上的一切(似乎要除了柚子姐,当然,对柚子姐来说,这个世界上就真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她高兴了),就像柚子姐说的,不过是小便池里的烟头。也许你可以假模假式地尊敬他们,但是实际上,真的不值一提。
因此,少女,当你对小老大表现出如此一种尊敬的态度,我很高兴,很高兴你还会关注一些严肃的事物[69]。在我看来,对于人类所创造出的一切,我们都可以怀着一种,最起码是怀疑的态度,因为人类本身也就是那么回事儿而已。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是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尊敬的,那就是“形而上学”(不是你们那个是么来着?哦,政治经济学里所谓的“形而上学”,即“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看问题”,这里我说的是metaphysics。我一直都不懂,为什么要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立起来,因为辩证法也是某种形而上学)。我坚信,形而上学不是人类的智慧,最起码要超越于形而上学之上。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神的话,那我会说,“上帝创造了形而上学,然后看形而上学是好的,就休息了。”[70]
而小老大,在我看来,就是形而上学的杰出代表。自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一直被密封在这玻璃瓶中,一方面我们可以批评它,说它没有任何现实上的经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讲,从来没有现实上的东西来干扰它。而很难想象,这世界上有某种形而上学不被现实所玷污——是的,玷污!因此我可以保证说,小老大,就代表了这个世界上最纯洁的纯粹理性思辨,是唯一能够跳出现实的,最接近神(如果有的话)的形而上学。这,便是小老大知道的东西。你可以像某些人那样,认为他什么也不知道;而正是因为其无知,方可无所不知。
“那,我究竟该怎么和它……”
用思想!而非语言。你觉得小老大会放弃那如此精妙的形而上学不用,而屈尊用语言来跟你交流么?“当我们用语言来表达形而上学,就如同用手指来修补一张蜘蛛网”[71],我们只能把事情越搞越糟,越弄越糊涂而已——甚至有的时候,你还需要放弃自己的思想。因为,语言又是我们思想的形式,或者说,思想的禁锢。因此和小老大交流的时候,我们需要冲破这种……
“那个,灵哥,我说呀。”
……冲破这种界限,尝试着去达到神的高度。而这,才是和小老大沟通的方法。嗯?怎么了阿卿?你有什么想说的么?
“我认识一个哲学系的女生,长得也很不错,你知道她业余的时候都在干啥么?”
是说的是杨海诚花名册里那个么?有一天晚上我还见过她呢,怎么了?难道说您对她有兴趣?那个,阿卿,咱们等会儿再说这个好么,现在我们在说一些很严肃的问题[72]。
“你这么说的话会让诚哥很苦恼呢,他也管自己的‘副业’叫做‘严肃的事业’。对此,我即不做评价,也不感兴趣……不过,你们两个人还真是投缘呢,这才认识几天,你就知道他业余时间是干这个的咯(其实说实在的,我更觉得他只是在兼职念书而已)?”
(原来不只是杨海诚,阿卿也能够在自己的对话里加上括号——这不禁让我感慨,现在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不破坏句子的完整结构,就不足以表达。)
是这样的,他请我吃了两次拉面,我们就成为了很好的,而且是在真正意义上的,酒肉朋友。
“是么,那我还是恭喜你吧,相信你们以后,肯定会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说到这里,阿卿意味深长的一笑,而我也知道,其背后深长的意味是什么,“比起这个,咱们还是别让杨海诚,以及他那些令人着迷的玩具分散了精力,咱们刚才讲到哪里了?对,形而上学。你把形而上学比作泡在药水里的胚胎标本,而学哲学的女生,则是诚哥橱窗里的漂亮玩偶。你不觉得,这两个东西讲的是一回事儿么?”
阿卿,你好像误解了些什么,因为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么,我所谓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便和“政治经济学”里的形而上学是一回事儿了。我并没有拿小老大打比方,说小老大本人的形象和形而上学有什么关系。
“本人的……形象?”
对呀,小老大的造型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哥特,也许会让人想起康德。[73]但是比喻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因为比喻是随机的——并不是说所有的哲学家一辈子都不准结婚,生活也要机械到人们可以用来校正时间。关键在于他表达了什么,知道么?
我觉得阿卿完全被搞糊涂了,这也难怪,尽管人们常拿诗人和哲学家相提并论,但那也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古时候人才匮乏,一人身兼多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如今,什么事情都讲求“专业”,所以诗人们一般都承担了感性的,直观方面的思考;而哲学家们担任的是理性的,非直观的想法。所以,有的时候哲学家和诗人往往不能互相理解,做出一些鸡同鸭讲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比如说阿卿爱讲的,海德格尔和保罗策兰之间的故事)。
“我觉得我们之间也开始有点‘鸡同鸭讲’了,尽管我算不上是诗人,而你也肯定不是什么哲学家了(你不要对此表示沮丧,这个年头,哲学家都是骂人的话)。你的意思是,那个小老大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就像瓦格纳做出来的人造人一样,把瓶子盖打开了,它便会开口讲话?”
大概是如此,但是,“讲话”这个词用的并不准确……
“那个,我说,你讲完了没有?”
一般来说,三个人在一起是最不好的,因为往往,两个人的话还没说完,第三个人就会插进来,然后把对话带入另一个莫名其妙的方向里去。
紫把小老大夹在腋下(所谓的尊敬,也就是这么回事儿),粗暴地打断了阿卿的发言。我怎么就忘了呢,紫和阿卿是最不对付的两个人了。
“我倒是觉得吧,”紫即恼火,但是又不是讽刺地指着电脑,“我不知道,整天看这些东西的人,是否有资格讨论诗歌,但最起码,没有资格讨论哲学了。这算是什么?自残的非主流么?”
我和阿卿都忘了,现在电脑上,满是沉珂,以及她自残的图片。
而我也怀疑,阿卿是否有耐心,把对杀马特的严格定义,以及自杀对社会的反抗功能,再跟紫解释一遍。
不出我所料,阿卿果然把刚才对我说的话,又对着紫复述了一遍。虽然所谓,“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之类的言论,大意是让我们用不同的内容,去对待不同的人。然而阿卿是个严肃的人,我并不知道,一个人如果性格太严肃的话,是否有利于研究文学。然而在他看来,他所讲的都是真理,而真理,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也许语气态度会有所偏差,但内容不应该有任何变化。
“听我说,我,真理,在说话!”——这种冷冰冰的严肃性格,倒是让我想起了柚子姐呢,我想有机会的话,介绍他们两个人认识一下吧。
然而介绍是后话,他们两个人现在又吵起来了。这的确是很奇怪的现象,而且我认为跟性格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先不论我和阿卿,杨海诚和阿卿这两个人的性格,完全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我真的很难想象,阿卿这样一个严谨的人,怎么能够忍受杨海诚满嘴信口开河地胡说八道呢?但事实仍旧是,阿卿和海诚是最好的朋友,据说杨海诚还讲过:“六爷(即阿卿)和我就是一体的,我活着他就死不了,而他死了,那我也就活不长了。”一类的话(我只是举例子而已罢了,而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不相信,他这种戏剧般的浮夸)。
大概古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发明了一个叫,“八字不对”的概念。
所谓“猫狗不和”,而现代科学对此的解释是,狗做出的表示友好的行为,在猫看来,则是具有攻击性的,and vice versa。就好比说,如果把“****妈”当作“Hello”来用,那走到哪里,都一定会遇到麻烦。在我看来,这大概便是“八字不对”的通俗解释,即,两个人之间关系的恶劣,并非在于性格,价值观,以及别的什么,相对外在的东西;而是说在内在的关键部位,彼此之间有着完美咬合的错位。就比如:
“我真是搞不懂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把女人放在被侮辱和被伤害的地位上呢?而如果一个女人足够幸福,免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不幸,你们便让她自己伤害自己。难道说,只有那些痛苦的,流血的,受伤的,哭泣的女人,才能满足你们病态的欲望么?”
“你曲解了我的意思,这个世界上被侮辱被伤害的不只有女人,而痛苦和我们自己的意志无关。死亡和受伤是我们不可避免的,我只是强调,死亡和受伤的权利被牢牢地掌握在他人的手里,而他人以此来控制我们。而我们所需要的,是从这种桎梏中……”
“不过我倒是觉得,你所说的这种方法,与其是让人从囚笼中解脱,不如说是让人们自觉地给自己带上枷锁。”
“但是这归根到底是某种武器,某种权利。自己有了挥舞利刃的权力,和被严格地保管在别人的手里,不用说也知道该选择哪一个吧?”
“也许吧,只可惜,”说着,紫指着电脑里,沉珂深而入骨,血流成河的那一张,“你们只会怯懦地去伤害自己而已,而从来都不会学着变得坚强。无论是让别人伤害自己,还是自己伤害自己,说到底都只能是怯懦的表现,向那自己不敢去叫嚣的东西低头,反而责备自己的无能,把愤怒发泄在自己的身上。”
而“怯懦”这个词,似乎戳中了阿卿的要害。
“怯懦?如果真的是怯懦的话,她哪来的勇气去……”
“那如果你勇敢的话,你为什么不去自残?不去死?”
这的确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尤其是对于粉丝或崇拜者们而言。也许是被这样问了多次,阿卿显得很淡定,不慌不忙地说,“我要是这么做了,你们便会说,‘这是在逃避’,‘不珍惜生命是无能的行为’,‘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也就不值得别人去尊重’,一类的话来抨击我。而这样,也就只能够暴露出你们的冷酷,你们所标榜的价值的空洞,以及,更重要的是,对我们这种自由的无能……”
在我看来,他们两个人现在讨论的,其实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儿,无非都是在表达,对一个叫做“你们”的怪物的不满之情。而“你”,自然是在“你们”之中的,所以彼此之间便会有这样无休止的争吵。而这也是我为什么很敬佩拉康的一点,拉康发现,把我们之间的关系搞得纷乱复杂,不可开交的那些“你们”,到头来都可以归类为一个,和我们谁都没有关系的“他”。
难道说,这个年头,我们真的从属于某个“我们”么?别开玩笑了。
而以上我的观点,也仅仅是一些外在的东西罢了。而当“她”,穿着漂亮的白连衣裙,轻轻敲了敲门,用银铃般,纯净不沾一丝污垢的声音问,“那~个,我找刘~仲~卿~同学……”,的时候,我便意识到,阿卿和紫之间,有着怎样内在的错位。
“哎~呀~,你是哪位呀~”
“她”看见我,便轻轻地走过来,同时捋着及腰的长发。我看见她染成了黑色的手指甲,意识到,这种错位不仅是严丝合缝的,更是你死我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