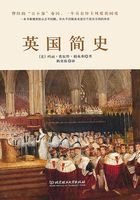伤口再一次开始结痂,瘙痒,如蚁虫爬过一般,恨不得将它挠个舒服。身体已基本恢复了,但一直以未痊愈为借口,避开所有人的探视。
“娘娘已经没有大碍了,等痂壳褪去后,就痊愈了。”秦太医照例早膳过后来请脉,顺道将太医院备下了汤药差人送来。
“秦太医——”我眉色一沉,道:“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你。”
“娘娘有话尽管问,下官知无不言。”他客套地说道。
“那日,秦太医来永福宫,真是为了替杜太医传信的吗?”我旧话重提,辗转再三,若说设计,除了他,不做第二人猜想。
他脸色一僵,“下官,的确是——”
我不待他把话讲完,截问道:“秦太医好像不仅仅替杜太医传信,似乎还替别人多跑了一处地方吧。”
“娘娘——”他一慌,差点舌头打结,哽语着说不出话。
“秦太医别急,”我淡笑,果然与我想的一样,诓道:“大致的事情,皇上已经告诉我了,皇上对我怎样,太医心里也应该清楚。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他稍稍犹豫了一下,心眼一横,说道:“下官——受制于淑妃娘娘,下官只是将王爷病危的事,呈奏了皇上,别无其他。”
他倒是会做人,我就知道事情不会这么凑巧,皇上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在那里。我镇静地说道:“秦太医真是八面玲珑啊,不会将我怀孕的事,都说于淑妃,做人情去了吧。”
“没有,”他忙撇清,“只有这一次,下官不敢多言,娘娘怀孕是皇上的意思,下官再有胆子,也不敢说不去。”
“秦太医不必担心,我只不过说笑,”我澹然地一笑,让他更摸不清我的想法,“过去的事情,我不想重提。但是若以后——”
他舒宽了心,忙接着话头,“下官自当听兰妃娘娘的吩咐。”
他无非是见风使舵,想两下都不得罪,应承的倒是干净利落。这种人,左右逢源,最会顺着竿子爬,一个简单的小人物罢了。
“来人啊,快去请太医——”院中不知何事,喧哗地吵嚷。
暗香急忙地跑进来,慌张地说道:“娘娘,不好了,采女娘娘见红了——”
“怎么会这样?”我边走边问道,进出都是匆忙的人,想来是严重了。
暗香扶着我,疾步向秀馨房里走去,“奴婢也是听侧院的人说,采女娘娘正服药呢,可没多久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具体是个什么情形,也还不知道。”
秦太医跟我一道前去,秀馨害怕得躺在床上哭,床单上殷殷的血迹,触目可见,不免为她担心。
我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桌案上还放着喝了一半的补药。我凑近了辨闻,不对,这个味道跟之前的比多了些什么。
“太医,怎么样了?”我询问道,此事可大可小,绝非一般的疏忽所致。
“有滑胎迹象,不过症状尚轻,服几帖药,可保一时。”秦太医敛眉说道。
“你的意思是——”我猜想着问道。
“怕是会提前生产,若是未满七月产子,恐怕凶险万分。”秦太医黯然地说道。
如今才六个月,腹中胎儿经过这次折腾,还不知道能否安稳一个月。我将药碗交予秦太医,道:“秦太医可知,这里加了些什么?”
他细细辨析,半饷,洞悉地说道:“马齿苋!”
我恍然,宫中的禁药,怎么会出现在永福宫?我狐疑地望着他,“永福宫的所有药物都是经太医的手,怎么会有这虎狼之草?”
秦太医背脊一凉,双膝一颤,惶恐地说道:“太医院决没有这类草药,就连京城也未见得,只有附近县城,地属偏僻,或许还有种植,但要想流入宫中,也是万不可能的。”
“照你这么说,这种草药还是凭空掉下来的不成?”我威严地怒道。
“下官——”他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辩解。
我瞅着无力的秀馨,面容枯槁,神情憔悴,微睁着眼,泛出波光痕痕。此事又是件棘手的麻烦,如此大的事故,却不能伸张,只能哑巴吃黄连,和着眼泪吞下。但若忍下,着实心有不甘,不能便宜了下毒手之人。
我拂手一扬,“你先下去,此事我自会回禀皇上。以后永福宫的药物,务必小心谨慎。”
他见我不追究,松了一口气,躬身告退。
出了秀馨房,暗香掺扶着我,在我耳侧轻声地说道:“娘娘,奴婢觉得,这次是冲娘娘而来,只是阴差阳错,让采女娘娘摊上了。”
“你这话——”我停下了脚步,转眸凝望她。
她眉色一皱,“娘娘忘了吗?不久前,娘娘要奴婢换药的事。”
我这才反应过来,那付药,是给我备下的,秀馨不过上替罪羊而已。我心中慌乱,问道:“你今天也换过药了?”
暗香点头,道:“定是有人想害娘娘,不知道谁这么大胆。”
我暗自伤神,叹息道:“在这后宫,我本就成了众矢之的,这么多人,谁都有可能。”
我不经心的一个好意,险些害到了秀馨,思忖地说道:“以后的药别换了,免得到时又惹出事。”
我冷眸地遥望深宫,重重内院中,谁都不能明哲保身,更何况是我。
与我料想的一样,下毒的事,被掩盖得彻底,宫中平静如常。这个秋却比往年要深,后宫的静寞,朝堂上却是惊心动魄。后宫的静,也不过是前廷震慑下的余波罢了。
数月之前,皇上开始扶持新任宰相,并大力打击排挤右宰相,朝中元老级的人物,或是告老还乡,或是因罪削官。处置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阻碍皇权的老臣。
入秋后,皇上更是雷厉风行,手腕快、准、狠,一扫所有的障碍,兴科举,重贤才,注入了一批活力的年青血液。朝堂之上,顿时焕然一新。我并不关心政治,但或多或少,那些消息就像风一样,自然地飘进我的耳中。
“哈哈——”皇上伴着一声声傲慢的笑声,大步地踏进永福宫,他的得意和骄傲尽显脸上。
见他一身朝服还未换下,如此兴冲冲,定是在朝堂中争了脸面。我迎面问道:“皇上又什么事,这么高兴?”
“朕办了件大事,大快人心,朕忍了他一年,终于让朕等到处置他的这一天,”皇上神情洋溢地说道:“你是没瞧见,朕当众宣读了他十项大罪,欺君,逾制,条条都是死罪。若不是朝中有人求情,朕定会将他凌迟。”
“皇上说了老半天,口中的他,到底是谁?”我见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倒上一杯清茶给他。
“高辅铭。”皇上切齿地说道。
“哦。”我怏然地应道,原来是他,淑妃的父亲,当朝的国丈,权势来得快,去得也快。
“唔?”他小茗一口清茶,见我反应冷淡,眉眼一挑,“朕以为,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是开心不已的。”
“我与高相并无瓜葛,他的得势和失势,又与我何干?”原来他乘兴而来,竟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
他哼笑着说道:“朕是在帮你,你倒是平静的很。”
我淡漠地回道:“高相的今日,只是应证了一句话,‘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富贵荣华,都是皇上给的,雷霆雨露,莫非皇恩,皇上会处置他,也是相权与皇权的矛盾罢了,自古皆是如此。”
“没想到,你也懂政治。”皇上顿惑,好像从未认识过我,扫视着我一脸的从容。
封建历史,教科书上披露得清清楚楚,身临其境,不过是重演了一遍。我莞尔地说道:“谈到政治,我不过是听说一二,但我深知,淑妃失去了最有力的蔽护,不知皇上对她又会怎样?”
“可有可无之人。”他漠视地说道。
好一个评价,可有可无,女人不过是个附庸品,当支持的家族垮台后,她也随波逐流,湮没无闻。
“江山,美人,皇上一定知道这个亘古帝王的抉择,若是皇上,会选哪一样?”我突兀地问道,陡然想到这个千古的难题,很想知道一个真实帝王的选择。
他密而不答,沉默,沉默……
“皇上,朝阳宫走水了——”太监在外高扯一嗓子。
他面不改色,摆驾离去,临别前,对我的问话,他只说了一句:“自古帝王皆无情。”
无情,薄幸。他说的是他自己还是别人?又或者是所有帝王共同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