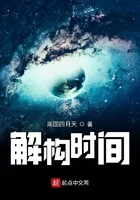这段时间,他们经常在城里的一家小酒店里同宿。露水般的交情向来是晶莹而圆滑的,他们之间有时好像什么都不能相告,有时又什么都可以说说。
他迷恋的是她美艳妖娆的身体,她沉湎于这样混沌、虚空、颓废交织着的不堪,都不能完全拔出来大致因为都还没有完全陷进去。
住在隔壁的宾客,半夜总会听到他们的呻唤,掺着月色和风声,好像旷野中的两个人在悲泣着一起背井离乡。
其实这些时候,他们都已经安安静静地并靠于床头的软垫,各自手中正握着一杯凉去多时的白开水。
不知什么时候睡去,不知什么时候醒来。这天早上,和往常不一样的是,醒来后的他们躺在床头,相继说起了昨晚的梦。
他说,我做的那个梦真是太烦了!
“烦”是他口头上常用到而指意比较宽泛的一个字。看他此刻的表情,听他此刻的语气,她知道他这句话里的“烦”该是恶心、邋遢的意思。
有多烦?
他说,我梦见我是原来的会计师,在公司的老区上班,他们要给我换一间新办公室,是三楼端头的一个很大的房间。
我打开门,发现这个办公室确实很大,足足有八九十平方米。办公室是按欧式风格装修的,有壁橱、壁炉、壁画……只是太乱了,到处都是灰尘到处都是废纸和垃圾。我想再乱也要把它打扫整理出来,正要动手,忽然发现门口站着一个人。
这人是以前的老总,他拿着一个收荒的编织袋问,你这儿有很多废纸吧?我收去卖几个钱。
我说,你不要慌,这儿的东西只有我知道哪些要、哪些不要,我已经想到了,不要的东西和废纸会专门放一边,你一会儿只管来装袋就行了。
他好像不放心,靠在门边还不肯走。我又说,等一会儿再来吧,你在这儿守着,把人引多了,到时我想给你都不好给。他这才掩上门走了。
我又专心清理起来。
我踩在大办公桌上,想把旁边文件柜顶上的那一大包废东西取下来。柜顶和这个大纸包都堆满了厚厚的灰尘,我只好屏住呼吸去取这包废东西,但是没拿好,东西散开了,突然露出一大摊白生生的蛆,蠕来涌去地,一股脑儿全滑下柜子顶。
我惊得叫出了声,这时一只弹起的蛆恰好射进我张开的嘴巴,又正正射进我的咽喉,我立刻要把它咯出来,没想到这一咯,那只蛆反倒滑进了食管,我恶心得要命,吐又吐不出来了,只觉得那只蛆还在我的食道里蠕动。
我烦死了,但是没有办法,只好忍受着继续清理。
我拉开一个大抽屉,猛地又窜出一只大老鼠,这只老鼠根本不怕人,踮着两只脚直立起身子,领着它身后的几只小老鼠像狗一样对我凶巴巴地叫,恶掀掀地还要蹦起来咬人,我赶紧把抽屉砰地关了回去。
说到这儿,他满头满脸似乎还扑着那间办公室的灰尘,那只蛆似乎也还在他的体内蠕动,他干咳着,还想把它咯出来。
是够烦的,你这个梦。她说,别说你做着烦,我听着都烦。不是烦,简直是太烦。不过我那个梦,很怪,简直也可以说是太怪了。
在他的咳嗽声中,她开始讲她的梦。
我梦见中世纪的一个武士方队,正在我童年玩耍的场坝里排列成阵,他们穿戴着漆黑的甲胄,手持利剑,现代机械人一样体格完美,神情空无。
我想避开他们,躲到远处去观望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就在我猫着身子逃遁的时候,两个持剑的黑影向我追来,他们很快追上了我,我跌倒在地,心想完了,这下是真的完了。
果不其然,两柄利剑都同时指向了我的脑门。我闭着眼等待受死,其中一个武士说话了:把头抬起来,不然你会骨折的。
我没有死,我抬起头,坐起并站了起来。我把玩他们的剑,凭触觉,我知道这种剑是一类奇异的金属铸成的,但是剑尖竟然光滑圆钝,就像……
就像什么?他已经从他的梦境进入她的梦境了。像什么?他似乎猜到了,仍待她亲口说出来。她勉为其难地说,就像,就像你们男人的那个东西。
后来呢?
后来他们还示范给我看,如何持剑致礼。
什么?
持剑致礼。
他花了好一阵工夫才弄明白她所说的这四个字。持——剑——致——礼,他念叨着。你这是个什么名堂的梦,更烦!
窗外,太阳已经升起。肠胃里还哽着那只白生生的蛆、眼前还忽闪着一柄明晃晃的剑的他不得不下床去洗漱了。卫生间里的哗哗水流把这一夜上演的两个又烦又怪的梦冲得七零八碎,躺在床上的她也完全醒了。
她猛地想起了什么,一下拖过他搁在床头柜上的长裤,迅速往裤包捏了一捏,长裤前后的四个兜里都塞着厚厚的一叠钱。他说昨天打牌又赢了七八千,临睡前她让他给她母亲买个新的手提包,他说她母亲还不是他的老丈娘。
就在这时,她不禁又动了偷他钱的念头。但是,这一次,她非常地不坚决,动作也迟缓得可怕,以至于他洗漱完毕走过来穿衣服时,她还没有把那个已经打开的裤兜重新扣上。
她只有在他的眼皮下做补救工作。幸好长裤就在床头柜上,她把头凑得很近地扣那裤兜,无奈扣眼特别小,加上她的手在发抖,一时根本不能扣上。他一定会怀疑她的神色,她知道。别无办法,她只能继续扣,他穿好衣服就要穿裤子,这个时候,她只能把他当睁眼瞎了。
刚才,她本来想拿掉他裤兜里所有的钱,她想让他彻底发现她对他的偷窃,她想让他揭穿她,她想在他揭穿她的时候把他的吝啬骂个狗血淋头。但是神使鬼差地,她只取了这些钱中的一小叠。现在,这一小叠钱就在她脑袋下面的枕头下面,她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仓皇和不安了。
他坐在床边穿袜子,完了,伸过手来摸她的脑袋、拍她的脸蛋,他的动作比平常多出一分温存来。他已经穿戴齐整,就要出门了。她才想起今天他又要出差。
今天是到哪儿?她捂在被窝里问他,其实她可以不把什么都问这么清楚的。
澎岭。他说,对了,我突然记起澎岭有一个小杨镇,那里有一个开砂锅店的老板,姓岳,会解梦。有时间,我去会会他。
要把两个梦都讲给他吗?
当然,那间积满灰尘和垃圾的大房间、弹进我嘴巴的蛆、像狗一样凶巴巴叫的老鼠、提着收荒袋的老总、还有你那群中世纪的武士,还有他们所谓的剑,还有,还有那门子“持剑致礼”……
梦,谁能说得清?
别说这个岳老板,他还真的给我解过一回梦。十年前吧,我碰巧也到了小杨镇,就给他说起头晚上做的梦。我那次梦见在一个湖中划船,湖水是蓝黑色的,跟墨水一模一样。他说梦见墨水,近期会收到书信。果不其然,没几天,我就收到了多年没联系的老朋友的一封来信。
现在全都是E-mail了,和墨水又有什么关联?他的解梦之道,肯定早不合时宜了。
问着玩嘛,又不当真。
他起身整顿了一下衣服,又对着镜子抹了抹头发,拎起包,准备开门了。就在他即将拉开门的一刻间,她忽地掀开被子,赤脚踩了地,一下扑在他怀里,戚戚地像一个将被遗弃在家的孩子,她的嗓音甚至在这一刻也泛起了童声,你能早一天回来就早一天回来吧,你能不去的地方就不去嘛,小杨镇离澎岭还有一程的,何必再跑那么远……
当她骤然对他涌起依恋时,他确实感到她比他的孩子还像一个孩子。他又摸着她的头发,亲着她的额头,看嘛,看情况……
他的回答从来就不肯定,似乎永远都面临着选择。他还没说完,她突然又想挣开他的怀抱了。但是,就在她赤裸的肌肤接触到他身上坚硬的纽扣和冰凉的金属配件的一刹那,她想起了去年冬天的一个清晨,那时,他们也住这家酒店,他也要出差,他把厚厚的衣服全部穿好了,她也一下子掀开被子光着脚站在地毯上与他吻别,他抱着她还散发着热气的身体,突然来了灵感似的说:
要是哪个雕塑家能把这个瞬间——一个穿戴齐整的男人与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子拥抱着不舍别离的这样一个瞬间,真真切切地雕刻下来,一定是件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