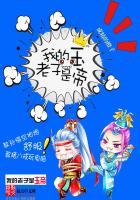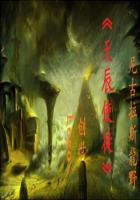凉夏有风,闲敲棋子,夜半灯花落。护国寺中的七天司空仲询显得尤为清闲。朝时他会踏着晨曦出门去找临风一道坐在菩提树下对弈,直到太阳西垂天边启明星亮时,他才会踏着钟声来到禅房中,沐浴更衣后携着梧桐一道往佛堂去。按照祖列他会在佛堂听着经文闻着鼻翼间的檀香跪伏到天亮。然而早在很多年以前,世家贵族的弟子就忍受不了这份孤苦,于是这跪伏到天亮的祖制就名存实亡了,司空仲询身边的人只以为这位天之骄子无法忍受这份孤苦,会早早的与先前的那些贵族子弟一般说是守灵实则睡觉了。然而却没有人料想到这位平时放荡形骸,无拘无束的二殿下竟然生生的忍受了这七日的困苦下来。顿时,无论从内监到护卫无一不对这位二殿下心悦臣服。
七日灵期之后,司空仲询由一众僧人拥簇着往山门外走去。护国寺外车马喧嚣,旌旗滚滚,士兵列阵成行。山门外司空仲询回身双目元远眺,只见护国寺佛塔高雄,塔尖笔直向天。山门外,住持手捏佛珠,双手合十,眉眼低垂,宛若莲花台上供着的菩萨。司空仲询只微微笑道:“住持,请留步,无需远送。”
“施主一路顺风。”住持呐呐道。
司空仲询低头微微颔首。转而翻身上马,墨黑色的云袍倾泻而下。他手拽缰绳牵引马头,只见四蹄之下烟尘滚起,白马离寺。身后是雄雄铁甲士兵,旌旗蔽天之间。小沙弥来到住持身旁道:“师傅,您该回去歇息了。”
“对啊,该歇息了。”说着便由着小沙弥一手搀扶着往寺中走去。古旧的石板路上,还带着淡淡的白檀香。小沙弥仰头问道:“师傅,临风施主是不是也走了?徒儿昨日送斋饭到他房中去的时候并不见屋内有人,一开始徒儿只以为他是出去游走游走一趟,熟料今日清晨,他房中也依旧没人,不知是不是真的走了?”
“缘来由风,该走的会走,要回来的早晚都需回来,又何必问他几时走,几时回?”住持淡淡说道。小沙弥只摸了摸光秃秃的脑门,那什么是该走的?什么又是该回来的呢?护国寺这么清寒孤独,走了的人还会回来吗?小沙弥想问,正在犹豫之间住持已经走远了。他赶忙撒着脚丫子往住持那冲过去,一旁的监寺看见了,虎着双目大骂道:“你这疯疯癫癫的模样成何体统!”小沙弥当即安静下来,却是不敢再去追着问住持了。
寒山门外,十里坡前绿柳轻拂山路。临风正端端站在那棵绿柳树下。正是正午时分,太阳到了一天中最毒辣的时候。临风身旁的夏侯缙云冷冷道:“你们是何交情,他走需你来送他?”
临风笑道:“交情吗?下了七天的棋,这可不就是交情吗?”
夏侯缙云闻言继续虎着一张脸不说话。他身子魁梧高壮,临风与之相较显得身子单薄了些。他背上背着一把巨剑,墨黑色剑夹套着背在身上,剑柄处襄着一块墨蓝色宝石,耀眼的太阳下正散发着幽幽冥光。这把剑还未出鞘,当中的冷煞气之气却通过那墨蓝色宝石幽幽的散发出来,给原本已经高大壮实的夏侯缙云又添多了一份冷气。
司空仲询骑着高头大马正领着身后一众铠甲士兵往这走来。远远的凭目远眺过去,只见十里坡前那棵杨柳树下,临风正白衣飘飘的站着。他低声斥马往前跑去。杨柳树稍拂过他干净的脸颊,马蹄停驻。司空仲询笑道:“我还以为你不会来送我了。”
“怎么可能?”临风道:“你我也算是棋友,今日分离怎有不送的道理?”
司空仲询翻身下马,朝着临风走过来。一路伸手佛开从柳树上垂下来枝蔓道:“你不与我一道回去拜见父王吗?”
“昔日离开时已经向大王辞行了,想来今日卫国正是多事之秋鄙人也不便叨扰,想了我这也不算不辞而别吧。”临风解释道。
“不算。”司空仲询说,而后伸手折下一枝柳枝递到临风跟前道:“古人折柳送别,取得是珍惜挽留之意,今日我折柳相赠,取得却是依依惜别之意,但愿他日再聚我们还可以再下一局。”
临风伸手接过,低眸沉默半响后道:“那是自然。”
说实只见司空仲询已翻身上马。高头大马上司空仲询只与临风说道。珍重。而后一拽缰绳,马儿调了个头,往先前的队伍方向而去。临风遥遥远望着那一头兵甲列队的阵势。低头看见自己手中一根杨柳时,这才想起,他好像忘记折一枝杨柳回赠给他了。远处车夫远远的走来,躬身请命道:“大人,车马已备好,敢问大人何时启程?”
“现在就走。”说完,转身往那车夫来时的方向走去。夏侯缙云远远跟在他身后,这三人与司空仲询那一列的军甲正好是一个背道而驰的方向。
楚丘城中早已不见昔日的哀伤空洞气派,浮欢楼又张灯结彩喜气盈盈起来,门前又是一阵车水马龙。街边小贩们依旧与主顾们热闹的讨价还价,榕树下的说书老头重新拍向了醒木,哒一声,新的故事正在开讲。卖胭脂的店铺里正是绿云绕绕的时候,城门两边的客栈店家又有人在外头招揽着生意。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司空仲询领街打马而过,一众士甲正在前头为他开路。一路上他奋马奔驰而过,从城门到皇城的那条驰道上,满满的都是他一个人的身影。
发丝轻扬,薄唇紧抿。路旁女儿翘首以望过去看见的是他若刀工剪裁出来的侧影。一时之间他又成了春闺梦里人。
王宫厚重的城门外,司空仲询停驻下马。身后的侍卫上前接过他手中的缰绳。而后只他一人慢悠悠的往里走去,宫门次第为他开。卫灵公彼时正站在城墙上,他身边跟着一个蔺温。卫灵公道:“你说宫中有两颗帝星……”
蔺温正经危色道:“是的。”
“寡人知道了,退下吧。”
蔺温依言,如获大赦一般退下。钦天监是一个苦差事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为此,他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卫灵公伸手摸索着城墙上的栏杆,枯朽如树皮的手紧紧的握着栏杆,两颗帝星。可是国无二主,他忽然想起,那日姜国派来的使臣似乎说是为两国可以结为同盟,他们需要一个王子到姜国去当质子,那么……便是仲询吧。如果真的需要一个取舍的话。
入夜后,栖霞殿中司空仲询正伸手接过宫中内应递给他的一卷竹卷,那上面清清楚楚记着这几日以来皇城中发生的大事。他伸手拂过竹卷清晰的字迹,指尖微微停驻在上。那上面的字迹说,姜国有使臣过来,欲邀一位王子殿下到姜国来当质子,以谋求两国平和发展的谋约要求。灯花啪的一声燃尽,司空仲询仰靠着椅背,深深叹了口气。他觉得他会是被自己的父王推出去当质子的那一个。为什么呢?可能是一个帝王的平常心吧。
蜡烛滴泪,灯花燃尽。一夜又到了尽头。司空仲询起身由着一旁的宫女为自己换上朝服。而后理了理自己的衣冠就往宣室殿而去。一路上来往的官人很多,有人见到他会笑口颜开的走来打招呼,有的人则是一脸深沉回避。司空仲询笑了笑只当什么都不曾发生,自己也什么都都不知道。
由于新政的推行,朝堂上不再是世家贵族一家独大的身影,这一个朝堂慢慢地开始有了其他人的声音。巍峨朝堂上,卫灵公双目被白纱所覆,他已经看不见朝堂之下的情况,但却依旧巍峨如山,没有人敢在这位经历无数血雨腥风的帝王面前显露出半点不敬来。
早朝上,卫灵公将姜国来使求质子的事情与众人说了说。朝中目光刷一声齐齐的向司空仲询看过来。卫灵公只有两子,没有女儿,大殿下如今还在外头浴血奋战,这时候将质子的事情提出来。难道是想让二殿下过去,朝中一时间噤若寒蝉。
司空仲询暗笑,起身,躬首道:“父王,孩儿愿意前往姜国为质。”
百官当时倒吸一口凉气。司空仲询话音刚落,当即有人站出来反对。那人说,二殿下乃皇室之尊,怎可为质?如此一来,莫不是丢了江山社稷的尊严。又有人说,二殿下贵为王族之尊,自当承当起一个皇子该担负的责任,臣恳请陛下同意二殿下的请辞。
因为这一个新的变局,朝堂之中又开了一场论战。而当事人竟云淡风轻的站着,不声不响。卫灵公道:“询儿,你可是真心的?”
“真心。”司空仲询道。他身后的大臣听着,眼泪当即储满眼眶,哽咽着小声道:“殿下。”
“好,不愧是寡人的儿子……”卫灵公一句话说在了老臣的前头。就这样一个决定下来,司空仲询只要等到大皇子班师回朝那日就是离开楚丘之时。司空仲询踏出宣室殿那一刻,只觉得琉璃瓦上的阳光扎的人眼晕。一展眼,他又要离开这个皇宫了,第一次他是自愿请辞的,第二次他也是自愿的,是自己顺了他的愿,所以也是自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