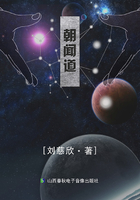事情有了转机,趋向恶性——真的出了些问题。
我们必须去新疆。一个在政治上曾给过人可怕震撼,在景色上使人产生诗意遐想的远方。它的矛盾纠结,正如那些在烈日与妖娆器乐的缠绵下用艳色面纱蒙住极致面孔的西域女子,在神秘与差异中演绎着躁动不安,致命吸引。暧昧些讲,我管那叫西域——一个听起来不错,也很正常的通俗叫法,而你可知,那对于一个饱受噩耗打击的小人儿来说,可相当于从撒哈拉沙漠中鞠一捧清泉的想象能力极限。我苟延残喘中还不忘自娱自乐,甚至……恩,真的起了作用。
妈妈接了一个电话。她的表情由悲转喜。我的心近乎麻木地目睹着。
这一次,上天又要和我们家玩什么暧昧却没有结果的游戏?
我啊,比任何人都想要结果。是死是活,只求横竖一个结果。
“啪”,妈妈合上手机的翻盖,眼神明亮地说:“我们去乌鲁木齐。你不是一直想去那边走走吗?”
我愣了一下。鉴于腹中腹水的压迫,使我思绪的运转都有些短路。
我佩服眼前这个女人,她可以将外出就医看做是一场旅行散心。
她可以将身边这个连食物的营养都吸收困难的患儿视作是生命中最大的希望。
“好啊。”我欢快地笑着回答。
即使可笑,人却可以不那么孤独。
我和妈妈站在外公家楼下的马路旁,黑夜,风很大,即使我那一头浓密却不美观的头发已经因化疗失去了三分之二,却还是可笑的被风吹乱。这世界上有一种悲哀就是东施效颦,还有一种最悲哀的讽刺,就是被迫东施效颦——而我,无疑在路人眼中演绎了那种刺人眼目的画面。面色蜡黄,身体失去正常的比例,腹中还有积水,以至于与我营养不良的干枯四肢形成鲜明的对比。可我是一个黑影,我是说,即使路灯不慎打在我的身上,也不会因给路人呈现了过于逼真的画面而坏了什么的心情。我很善良,善良就在于我有自知之明。而妈妈则比我好一些,除了微胖,她比我健康,身材比例也足够恰当,秀发即使不算多,但绝对没有该死的自来卷儿与因身体原因而无法吸取食物营养的枯黄发丝。那一夜,我的心情在绝望恍惚到近乎痴醉梦幻的搅拌下,望着眼前背光,头发被吹乱的正在打电话妈妈,有一种“她就是我的神”的感觉。
妈妈冰凉的手握住我苍白毫无养分的手。
我以一米三的个头,无比惶恐地仰望着这座陌生的城市。
动也不敢动。
非常巧,旁边有一个卖烤包子的摊位。我们晦涩不安的情绪被那种富有野性与冲击力的奔腾香气击晕,心情的死水中被这异域的食物致辞挑逗出一抹好奇(后来才知道我们真的惊诧早了),只见古老简朴到固执的巨大炉坑——当地人管那叫“馕坑”的布阵,在乌市高温盘踞的城市广场内宣战似地强调存在感,高温扭曲了我们眼前的空气——在我还来不及在化学课上了解到的物体密度的年龄,年轻俊朗的维族小伙(这点还比较安慰人心)用完全可以胜任恐怖片杀人狂道具的铁杆儿插起馕坑内的包子,然后像捏起一串羊肉似的高举这烹饪的战利品。在我和妈妈还未意识到眼前的食物在表达什么意义时,爸爸捂着肚子说他饿了。
我们提着装了五个烤包子的塑料袋,爸爸的口中正撕咬着一个——他是狮子座,食欲也像一只狮子。他不嫌对方烫,在他的眼中,一切只有“能吃”与“不能吃”的区别,就像烤包子与装烤包子的塑料袋的身份差异。他的食欲,吃相,作为他身上最杰出的品质之一,总能有效地点燃任何处境中的篝火。哪怕那个环境中没有可燃物,我们也能从那种“呼噜呼噜”的吞咽中想象出来。然后气氛爆棚,人品窜天,否极泰来,峰回路转,我是说,我们期待。
他吃完了第三个包子,我们没有餐巾纸。爸爸用我们所能想象的方式擦了嘴。短袖不方便,手背会留痕迹,他自下而上撩起衣服,迅速完成了那个动作。我和妈妈在旁一愣,又实在找不出制止的理由。按照我们的理由,这里谁也不认识谁。如果不雅也可以为路人造一个笑点,那么我们初来乍到,也算积了德。
我可以治疗。
我们叫了一辆当地出租,出租车亦是踉跄地行驶在不够光滑的路面上。我抵挡不住内心微妙的嫌恶,可依然勉强自己敬畏此地。
神秘,亦或是我不知道它会带给我的什么。
惊喜亦或是惊吓。
没有什么不敢预料。
而此时,我又何尝不能做到赢。
这一路上我出了很多的汗,毛孔显然比肾脏更争气。汗液的黏腻让我饱受折磨,却也感到酣畅过瘾——真想一直这么淌汗,我就会有救,身体实在有必要被打开数以万计的水闸,活生生流干体液。而流出的汗液兴许可以换一碗冰镇的绿豆汤,加一勺赤砂糖亦或是蜂蜜,然后让我在这个本该属于任何人的夏日中没有顾忌地喝下去,生命才能变得千娇百媚。我实在做梦都想喝一碗不会威胁生命的水。听起来好荒唐,然而闹点就在这荒唐——眼下我的身体因此轻松了不少,方才肿胀的手腕也在此时松了一口气,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以至于使我有一再锯断它的冲动。
“医生长什么样子,多大年龄?”我仰起头问妈妈。
“你要叫爷爷哦。”她简单回答一句,“要记得,他姓李。”
我迅速在脑中勾勒出一个老中医的模样:他需要很瘦,道骨仙风,架一副眼镜。身上有那种犹如职业女性舍身不离的国际一线品牌香水气息的中药缠绵——和我接触过的许多中医有相似之处,却又需要有绝对的不同。而所说的那种不同,在于我看到他后能预料到最终得到的结果。
那是夏天。
“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无趣又无知的我就喜欢问废话。
“很快。”她说。居然总是回答,从未沉默。
我们都想多一些对话。
好像她的智商也低到想要询问与我相同的内容。
可是问谁呢?
爸爸吗?不,他很累,太累了,也很无辜。他不能被抛以任何疑问。他最大的疑问是如何压制烟瘾,却又能麻痹身心,强身健体。
问谁呢?
那么,是第一天的烤包子吗?是街道两旁的树吗?是那个没有空调却依然自信地治病救人容留生命的客栈般的病房吗?是店小二般温柔的新疆护士姐姐吗?是面肺子吗?是大巴扎里载歌载舞的异域蒙面女郎吗?还是这里的形象代言人拉条子拌面呢?
人在逆境时的希望在心中的地位,就像寂寞时想要拉来身边消除孤寂的情人,一旦知己蓝颜,就想要抓紧不放走。内心的踏实,可以让世界都盛满心跳。
而我马上就告诉你答案。
这里没有别人,身边不会有别人。你这个样子,在某种社会现实下连没有亲人都很正常,所以你放心,现实不会微笑着更改,掏出小刀划拉你的眼神与嘴唇,在你流出鲜血的时候捧出一盘粉色棉花糖堵住你的伤口,然后亲手喂你吃下那饱蘸着血腥的柔软糖果。如果厄运扇了你一个在众目睽睽下冤屈的耳光,你也别奢望得到一颗续集般的枣儿。你将看不到乌市的冬天——即使妈妈在来之前对你绘声绘色地讲起他们在这里的小时候,她和她的哥哥也就是你的舅舅在这共同拥有的无比丰盈而纯洁的童年雪仗,以及一个永远不会感到孤独不会融化的雪人。而那不是乌市是库车——远处,有你无法想象的落后经济,可是饱满到华丽。人们的肾脏很少有问题,浮肿也是因为饥饿而非代谢。那时死去不少人,那些人死去的时候也是浑身肿胀的——本质上与你不同。可活着的你,思想分外活跃的你,却难以逃脱那种惨剧的对号入座。远处,有一个你不曾亲身参与的简陋却足够健康快乐的院落,有人看似孤独地玩耍,身边融化了一根劣质也便宜的明目张胆地添加了奶精与甜味剂的冰棒,俗称老冰棒的家伙——它自己死在自己的一汪血泊中,却还幸福地“咯咯”笑出了声。妈妈还小,喜欢那个时代里一切甜味的东西,舅舅欺负她,使尽心计想让她多多洗碗,她什么都不懂,她的脸像个包子,她的世界很轻松,作为看客的我,也愿意抽空自己的身份祝愿这童话一直轻松上演下去——可是后来怎么会有了我?她做错了什么吗?
我得出的结论之后的疑问,就是:“她做错什么了吗?”
究竟做错了什么,才有一个不得已接收的残损生命体。
更可怕的是,她还是一个敏感多疑的怪胎。
“我想喝水。”
在思想内打完了一场人格分裂的仗,我已经近乎虚脱。
需要说点什么了。
我于是哼哼唧唧,近乎呻吟地说。
“快给我水!”
“乖,我们不靠墙。那墙很脏。”妈妈试图将浑身充盈着废水的我从病房里那面绿色油漆依然斑驳脱落的墙面下拉回床位的正规。我别扭地哼唧了一声,那个声音亦换来了我自己的一身颤抖,更别提妈妈的脸色,对于自己亲手逼退到坏局面的事实,我总能邪恶地回避。我决定装睡——她再次努力拽着我的睡裙,最后我一个咕噜,被迫翻回到病床正中。为了表达不满,我挤出了更难听的声音与眼泪,最后居然真的哭到了啜泣的程度,连带我的整个满载了积水的腹部一切颤抖起伏,我像一个因偷吃了蜂蜜而被猎枪射中浑身上下弹孔开花的黑熊,以怪异而丑陋的姿势在森林中制造着更刺眼的画面。我在面积相当有限的病床上来回翻滚,踢腿,双臂在半空中胡乱抓取着不属于我的空气与希望,意识在连自己也辨不清情感程度与方向的泪眼朦胧中越加模糊,直至错乱。我憋成一个实心气球的腹部,阻碍着我的行动,更奇异地淹没着我的理智,却从未因挤满了液体而在人体大幅度晃动的前提下晃荡出迷人的水的“咕咚”——不符合常理的现象,接二连三在我幼小的身躯上上演,而在承受这一切亦推动这一切的同时,我选择回避爸爸妈妈的目光——从那里随便牵出一缕探寻,就足以制止这恼人的小恶魔的劣迹。
可我难受。
我想喝水。我热,我更想知道,他们有没有耐心,是不是真的爱我。
我真的疯了,不是吗?
这是第几次了?耳边传来低沉雄浑的声音,来自天空,他说什么,也无非这一句:“孩子,你真该去治治脑子。别再闯祸,骚扰人间。”
每当被这样教诲时,我就会踢掉鞋子大胆亦无辜地质问对方:“我请您拿掉我的性命,拿掉我那闯祸的肾,拿掉我们迟迟不来的希望——您不这么做,却还嫌我们演技不够好。人间生活如此艰苦,连个演出费都没有,还要我们坦诚地故作坚强——凭什么啦?”
然而世间最多余也最愚蠢的疑问,就是“凭什么”。
当我屡屡从一个相同的噩梦中醒来,眼前都是妈妈红肿黯淡,却为了迎接我睁开的双眼而瞬间披挂笑意的双眼。
爸爸率先在医院楼下一家小规模餐馆吃了咸味奶茶与当地即使在清晨也依然销售火爆的拉条子拌面。他打着嗝儿,眼神空洞内心闷骚却异常深沉地走到我们面前,妈妈同情又关怀地摸了摸他像做了隆胸手术般的胃,用眼神询问:“还好吧?”爸爸以非常男人的姿态推开她的手,说:“李大夫到了吗?”言语间有一种“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只要人”这样的进击人生观。我在一旁,知道他如此自信沉静的原因在于吃了一种前面已经提到过名叫“拉条子拌面”的食物——来到新疆,来到乌市,你会发现它以非常地痞霸道的手段,使每一个步入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将其列为生活的重心。即使胃口已经违逆到想吐,思维却本能拓展开这样的宏图:我吃饱了,青椒与过油肉正在我的嗓子眼打架,并且还没有受过胃液的洗礼,这架势是要我呕吐吗?我连呼吸都是拌面的味道,下一顿打死我也不吃这种东西了——第二天:啊我又饿了,那怎么办附近有什么吃的吗?咦好巧,我看见了卖拉条子拌面的餐馆,粗犷油漆与强势霓虹如此霸气地亮出餐厅主打餐食拉条子拌面的自信与拉客架势,如果不这么进去的话,会不会不给人家面子啦?会不会破坏民族和谐呢?那怎么办?即使再吃一顿也不会尊严扫地伤天害理吧?好吧我要踏入第一只脚了哦——你告诉我是左脚还是右脚呢?这又不是成亲哪来那么多讲究——恩?什么我居然已经坐在了面馆的椅子上并且手指正好翻到全是拉面种类的那一页。什么?不可以过油肉?那今天就青椒土豆吧?啊?你说什么?前天才吃过?那茄子过油肉好了——恩?你说今天没有茄子?那就点一份西红柿土豆片拌面吧。等等,胃好像有话要说,说什么“西红柿土豆没有肉所以不要”这样违背天理却非常有道理的话——要肉吗?那还是过油肉拌面好了。
你带着说不清的满心疑虑,再将盘子里最后一滴汤用舌头吸干后,意识到自己的可鄙。
你终于输了。在现实的生拉硬拽广告宣传强势左右开弓软硬兼施齐齐上阵只为力保这城市代言人形象的活计下,你输得很伟大也很彻底。
“这个管饱很不错。很好吃。”爸爸受到了当地饮食民俗的蛊惑与洗礼。他开始传教。
“你们不饿吗?要成仙吗?”他的神情充满了对我们无视拉条子拌面的罪孽深重的审判。我和妈妈都有些害怕。耳边恰到好处地传来“来来来来,里面坐里面坐,拌面拌面”的叫卖声。我们默默脱掉恐惧,重新换上了一身冷汗。现实那种直接扑上来的架势告诉我们,下任何结论都太早。
那是一个高个子瘦削,戴眼镜的爷爷,长相儒雅,整个人比我想象中还要富有书香气息,只是不知道他是否也是吃了拌面才来。
“除了腹水严重,其余还有什么症状吗?”
妈妈替我交代了全部,最后我点点头表示默认。
“小姑娘,你几岁了?”他抬起头轻声问我。
我说了自己的年龄。
“配合治疗,一切都会好。”
这是我听到的最具力度与善意的保票。
我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