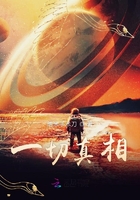皇帝放慢脚步道:“哦,你来说说。”
宗孝廉笑道:“朱逢时也有攀附,他攀的是陛下您,所以他的生意做得最好。”
皇帝哈哈大笑,指着宗孝廉的鼻子道:“你讲话的本事已经超过你的剑术了,朕不知该夸你,还是该罚你。”
宗孝廉知道因为自己的话皇帝刚才在垂光殿里结下的心结已经稍有松弛,心中喜悦,脸上却是微笑不语。
皇帝背着手道:“你整日陪着朕操劳,朕居然忘了赏你点什么。不如让宗无本也给你备一份礼物如何?”
“陛下厚爱,微臣感激不尽”宗孝廉窘笑道:“只是,微臣是凡人,如何能比陛下的真龙之躯,无本大师的礼物微臣恐怕难以消受啊。”
君臣二人一路谈笑风生,走进洪恩殿南阁。
到了阁中,皇帝坐在檀木椅上,命门外候着的小太监给宗孝廉搬来一个矮一些的绣墩,君臣真正坐而论道。
宗孝廉道:“在羽城巡查的校尉今日来报,四年前在赤霄山发现的一颗神族的种子近日有了动静。”
“神族”二字似乎比三胞胎的瑜伽仙子还有魔力,犹如两团火焰,让皇帝的眼睛亮了起来。
一千八百多年前,神族与人族大战,神族屠杀人族以千万计,人族的开国皇帝戚太祖宗正便是死在与神族的战斗中。神族纵然远徙西北,依然被认为是宗氏戚国的最大威胁。宗氏与神族不共戴天,但皇帝听到“神族”二字眼中闪动的分明是压抑不住的欣喜。
宗孝廉自认为伴君多年,皇帝的心思十有八九都能摸透,唯独皇帝对“神族”的心思,百思不得其解。
皇帝道:“说下去。”
宗孝廉:“赵定方,年十六,神光二十一年生于赤霄山下一户樵夫家中。神光二十三年玉州蝗灾,赵定方父母双亡,赵定方被羽城洪恩馆收留。神光二十六年入羽城弘文馆,当年的教习均称其天生怪力,木讷寡言,性情乖僻,一月内打断五个同窗的鼻骨。神光二十八年送入赤霄山习弓马剑术,性情稍缓,依然少言寡语,师长同窗皆以为赵定方是痴人,其好把玩铁器,故有铁痴之名。神光三十三年,赵定方年十二,开霖骑震天弓,五箭连珠,箭箭中靶,被称为弓马天才。玉枢院与当时的羽城道巡检都尉均认为此子有神族禀赋。”
宗孝廉早将巡检都尉们整理的情报熟记于心,将一大串数字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皇帝对这个忠臣的办事能力也十分满意。
宗孝廉继续道:“不过,此子虽弓马双绝,对法术一道却毫无进境,剑术尚可,但从未御使飞剑,亦无召雷之能。近日此子忽然一改木讷寡言之性,言语如常。玉枢院水火二剑已出手试探,查明其毫无御剑召雷天赋,亦无御使水火之能,遂未予清除。陛下,是否让赤霄山上的巡检校尉解除监视?”
皇帝望着地图上赤霄山的方向,摇头道:“若是他已知自己是天神之子,暗藏不露呢?”
宗孝廉沉吟片刻,道:“他不过是十六岁的少年,自知事起便在山中,恐怕难有如此心计。”
皇帝道:“你不要忘了,赤霄山上可有一个离经叛道的宗师,他若是有心帮这个孩子,恐怕以你那些下属之能,根本看不出来。”
提起赤霄山上那个人,宗孝廉的肩膀忍不住抖了一下,人也缩了几分。
宗孝廉道:“这个人虽满口忠君之心,却向来好异端邪说。况且此人对我巡检司了如指掌,微臣以为留他在世上徒增祸患,不如……”
皇帝摆摆手道:“不急。朕手中的剑虽多,敌人却更多。你看今日洪恩殿里的左右丞相和两府将军,哪个如你一样是真心忠于朕?若不是我有先见之明,让桓儿入主左藏寺,领衔文臣,恐怕天下事已经不容置朕喙了。朕必须爱惜自己的剑锋。”
皇帝说到此处似乎陷入回忆,缓缓道:“神光三杰,嘿嘿,朕的手中曾有三柄可与开天三圣争锋的利剑,而他,本是朕手中最利的一柄剑……”
皇帝摆摆手,打断自己的回忆:“罢了。且让这柄剑在青锋酒中生锈销毁吧,将来或许还能再为朕所用。他虽然比以前钝了,却比你们都锋利。他还没被铁锈腐蚀透,此时贸然派人前去,恐怕反而把他磨得更加锋利。你觉得呢?”
宗孝廉见过那个人鼎盛时期的本领,那时宗孝廉还不姓宗,职位也只是个巡检校尉,当他看见烈焰如刀横过长空,自上而下斩入大地,刀锋所过之处,草木成灰顽石化为岩浆,炽热的风如同汹涌的海浪撞过来,他几欲跪倒。
宗孝廉的官越做越高,权力越来越大。被皇帝擢升为巡检司都司之后,他的权力与声望都达到了顶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并不是尚书台的左右丞相,也不是两府将军,而是三品的巡检司都司:着金翅服,配尚方剑,四品及以下官吏均可先斩后奏,拥有这个权力的,在戚国几十万官吏和将校中,只有他宗孝廉。
但是,宗孝廉对那个人的恐惧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发强烈。那个人给他的威压甚至超过皇帝。只要他足够忠心、圆滑,他就可以在皇帝面前安然无恙。那个人却是无懈可击的,他不需要别人的忠心和奉承,像一柄挥出去的刀,不去听也不去看,只为斩断。
宗孝廉很想借皇帝的手折断这柄让他恐惧的刀,抹去心中的阴影。但他不敢让皇帝知道。普天之下,如果只有一个人有权力握住刀柄,那个人一定是皇帝。皇帝永远是捉刀人,不是刀。谁把皇帝当刀利用,谁的前途和性命就会被拦腰斩断。他正是因为深谙这一点,才能安稳地呆在皇帝身边,看着周围的人不断倒下,自己却步步高升。
“陛下圣明!”宗孝廉讲出这个无懈可击的答案。
“微臣探知朱逢时向太子殿下上了一道折子”宗孝廉抬头看了一眼皇帝的表情,放低视线,继续道:“朱家进入南方诸邦的商队在经过晴波山脉时屡遭游侠和流寇的劫掠,恳请请两府一司派人护送商队南下。太子已经把这个折子递给尚书台,还没送到您这。”
皇帝的手指轻轻叩打椅子的扶手道:“嗯。根据左藏寺的折子,朱家所有商铺票号一年向朝廷缴纳的厘税近三百万两。况且,将来借通天道靖北平南还要借助朱家的商队和商号。朱家的生意,也是我戚国的生意。”
宗孝廉:“陛下圣明。”
皇帝面露微笑,声音却没有一丝笑意:“朱家的商队是我戚国的商队,劫掠朱家的商队便是与我戚国为敌。朕自会派精兵良将护送。不过,你也要告诉朱逢时,朕既然给他专折奏事之权便要好生使用,他有事不跟朕讲而是向太子递折子,置朕于何地呀。”
皇帝云淡风轻地说着,宗孝廉的头越垂越低,脊背上早有冷汗汩汩流下。
皇帝早立太子,并让太子执掌天下财帛货殖只是想在强臣林立的朝堂上给自己多一个助手,并不是想让朝廷里多出一个山头。
朱逢时希望得到皇帝的帮助,又不想越过主管内外商贾的左藏寺而得罪太子,故而想出双管齐下的法子:递折子给左藏寺,同时托宗孝廉在面圣时向皇帝提及此事。
朱逢时做生意很精明,却在这件事上犯了糊涂。储君不是君,只是皇帝的一个指头,皇帝废旧立新不过手掌翻覆之间。在皇帝看来,朱逢时先递折子给太子便是在拉拢储君,与储君结党。储君与人结党一向为皇帝所不容,如果天威震怒,后果不堪设想。
皇帝的敏感和精明是宗孝廉始料未及的。“陛下圣明”在这件事情上讨不到皇帝的欢心。宗孝廉浑身冷汗搜刮枯肠,一时竟找不到对答之词。
皇帝停止叩打椅子的扶手,微笑道:“朱逢时的心思朕明白,他是个商人,总想多赚一些。他既想让朕帮忙,又不想得罪太子。朕不是不通情理的昏君,叫他下不为例就是了。”
宗孝廉松了一口气,人从绣墩上滑下来,顺势给皇帝叩头:“陛下圣明!”
皇帝看着伏在地上的宗孝廉,仿佛一只被责罚的家犬。
国运昌隆自然离不开名臣良将,但皇帝更需要的是会犯错的家犬。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无欲无求无懈可击的人,那便是皇帝。
皇帝站起来,边踱步边道:“鹰犬鹰犬,犬不及鹰迅捷,鹰却不及犬忠心。朕欲开疆千里,要借助雄鹰之翼;但要保我宗氏江山万世不易,却要依仗忠犬之心。”
皇帝在宗孝廉身前停下道:“朕不希望你作鹰,朕希望你做犬。”
宗孝廉再次叩头,语带哽咽道:“陛下厚爱,微臣欣喜惶恐,必粉身以报。”
皇帝坐回椅子,问跪在地上的宗孝廉:“奉国府白衣堂那个裴如晦品级如何?”
宗孝廉:“五品骑都尉。”
皇帝点点头,道:“你即刻代朕拟手谕给赢纵,裴如晦睿智勇武,南下之行进退有度,深得朕心,特擢为从四品后将军,入巡检司听差。见手谕之日起裴如晦便归你调度,即刻安排他进朱家南下的商队,护卫之责是次要,为朕看看通天道是否畅通无阻。”
皇帝的目光在庞大的地图上来回逡巡,眉宇之间豪气飞扬,仿佛看着戚国的兵马正在那些化成线条的山川河流上行进,像慢慢张开的五指,要把整个天下握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