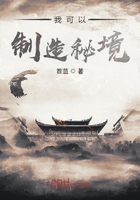武定侯府比原先那套御赐宅邸大了十倍,中有楼阁十数座,以回廊相连,又有假山池水七处,散于楼阁之间。
如此大的宅院,自然不在紫衣巷。
紫衣巷中的大宅皆是王侯世代相传,抑或重臣宠臣受皇帝恩赐宅邸。仁宗迁都御天已有百年之久,城中的王侯国戚数以千计,能住紫衣巷中的寥寥无几。赵定方是异姓侯,资历尚浅,要住大宅,便要从紫衣巷搬出去。
武定侯府在乐游原东北的荣升坊内,此地靠近御天城东门,取朝日初升之意。
赵定方策马来到武定侯府时,门前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站了百余人,衣饰分黑蓝赭绿四色,见赵定方前来,齐刷刷跪地道:“恭迎侯爷!”
赵定方心道:这些定然是武定侯府中的佣人。
清秋原上,赵定方指挥五百骑兵尚能得心应手,此时面对这百余人竟有些无措。
“大伙快起来”赵定方下马道:“见我不必行礼。”
一位黑袍老者起身上前道:“小人钟锦荣,是侯爷的管家。”
赵定方道:“钟老今年春秋几何?”
钟锦荣愣了一下,恭敬答道:“小人今年五十有六。”
赵定方道:“我便叫你钟伯如何?”
“使不得,使不得”钟锦荣连连摇头道:“尊卑有序,小人不敢乱了规矩。”
“侯府之中,我的话便是规矩”赵定方道:“钟伯不要再推辞了。日后大伙在一个院子里相处,便是一家人,各位若是比我年长,我便以兄姐相称,若是比我年少,我便直呼其名。”
百余仆人议论纷纷,钟伯喝道:“噤声!”
侯府之前顿时鸦雀无声。赵定方心道:这老伯果然有些威严,有他操持侯府,我这一府之主便轻松许多。
赵定方在钟伯引领下进入侯府之中,在院内一方水塘之前将府中上上下下的仆人姓名年齿一一讲与赵定方,赵定方与每个人都打了招呼。
府中年过五十的除了钟伯,还有一位花匠、一位大厨和一位太医出身的大夫。赵定方以叔伯称呼这几人,几位老人诚惶诚恐。余下诸人皆在三十以下,赵定方皆以兄姐相称或直呼其名。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被赵定方以兄长相称,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倒是那些年轻的女子泼辣大胆,忍不住掩口娇笑,任钟伯呵斥也难以禁止。
还有一位名为江迎潮的女子,不等赵定方开口便抢先道:“侯爷且慢!奴婢比侯爷年长几个月,恳请侯爷直呼迎潮之名,莫要把我叫老了。”
江迎潮一身翠色衣裙,纤腰如柳,****高耸,月眉星目,青丝如瀑,用一根丝带绑住,说话时下颚微微抬起,如娇似嗔。
江迎潮身后的几个婢女齐齐发笑,钟伯怒斥道:“胡闹!”
“侯爷莫怪”钟伯对赵定方道:“这妮子是小人的同乡,年少无知,不懂规矩。侯爷若是嫌她吵闹,我便把她送回去。”
“二伯”江迎潮正色道:“我是去是留侯爷自有定夺,您老一个下人,怎么能替侯爷拿主意呢?越俎代庖,喧宾夺主,此乃为仆大忌呀。”
钟伯被她噎得老脸一红,脖子上青筋暴起。
赵定方摆手道:“钟伯勿急,我说过,侯府之内,便依照我的规矩,不行跪礼,称呼以年齿长幼为准。出了侯府,便依侯府外的规矩。”
“侯爷,奴婢有一言不吐不快”江迎潮道:“侯爷的规矩好是好,可是钟伯、方伯、王师傅和叶先生改掉几十年的习惯,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何况,我们不叫侯爷做侯爷,别人会以为武定侯府没规矩,侯爷会被人小看的。”
“说得好”赵定方抚掌道:“那我们各退一步。我称呼你们按我的规矩,你们称呼我,按你们的规矩。不过,我不习惯被人叫爷,你们以我的武职称呼我如何?”
江迎潮莞尔一笑,领着十几个婢女齐声道:“多谢将军!”
赵定方命众人各司其职,只将钟伯留在跟前道:“钟伯,我有几件事想向您老请教。”
钟伯四下看了看道:“将军请随我来。”
钟伯带着赵定方穿堂过室,走到一处庭院之中,院子四面门窗紧闭,院中有一株老树,主干五人方能合抱,树冠如一把打开的折扇,半个院子被树叶遮蔽。树下是一个半月形的浅水塘,正好与树冠相对。水塘之中有数尾不足一尺的锦鲤,在圆润的卵石间游动,发出轻微的水声。
“将军”钟伯道:“此地已无六耳,小人知无不言。”
“看这宅子有些年月了”赵定方道:“不知在我之前是何人所住?”
“这府中有七座主楼,各有假山池水”钟伯道:“对应的是双星五虎。”
赵定方心里一寒,道:“戚国有五虎之称的姓氏并不多,不知双星指的是何人?”
“自然是姬兴与姬冲”钟伯道:“二人年少时便以精通兵法成名,都是当时公认的智将。姬兴入了奉国府,多年未受提拔,姬冲这个弟弟后来居上,袭了靖远侯之位,掌管讨逆卫,姬氏小辈出了五个勇将,世人便忘了姬氏双星,只记得姬氏五虎。”
“不过侯爷尽可放心”钟伯道:“这套宅邸自姬冲北上修戎城之后便一直没有人住。姬兴嫌这宅院太空旷,又买了套小些的宅院。”
赵定方点头道:“钟伯,我有一事,请坦诚相告。各地藩王身边都有奉国府派去的龙宿营,虽然节制之能形同虚设,却可以充当皇帝的眼线。我的侯爵之位是以武功获得,府中没有侍卫,仆人中想必有巡检司或是白衣堂的人。您老若是知道,不必瞒我。需要让皇帝和宗孝廉知道的事,我会告诉你,我们互相帮助,如何?”
“师尊没有看错”钟伯笑道:“宗主虽然年少,心思缜密,目光如炬,令人佩服。”
钟伯须发花白,背有些驼,在此之前,看上去只是个脾气有些暴躁的老管家,那一笑却狡黠如狐,似一只千年老怪。
“你不是皇帝的人”赵定方奇道:“你叫我宗主?”
钟伯单膝跪地道:“属下在御仙山学艺时不甚触动明王法阵,几乎被无相、无量、无形三明王法身杀死,多亏不动明王现身相救,自那以后属下与不动明王一直以师徒相称。前些日子属下回御仙山又见道师尊,得师尊之命助宗主成就大事。”
“不动明王是你师父”赵定方道:“那你岂非是我师伯?师伯快快请起。”
“算起来,无相门前任宗主许空炎本是属下的师弟”钟伯起身笑道:“不过后来他成了无相门宗主,我与师尊都成了他的下属。”
赵定方笑道:“我本在师祖面前说过,无相门已经解散。师祖也未给我提过我还有一位师伯。”
“师尊并非人族,行事自然常常出人意表”钟伯道:“师尊说宗主你的天资比空炎宗主还好些,若是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太可惜。若是宗主想成就事业,有无相门相助,事半功倍。”
赵定方道:“那无相门共有多少门众?”
“这……”钟伯道:“属下只知世上的无相门除了属下,便只有师尊与宗主。”
赵定方心中笑道:这无相门果然厉害,若没有通天之眼,连宗主都无法看清本门深浅。
“有师伯在我便安心了”赵定方道:“依照我对无相门门规的体会,本门是最不讲世俗规矩的一派。师父在赤霄山上传剑与我时,有时候会与我以兄弟相称,师伯既是无相门下,何必在意宗主与门众之别呢?”
“天性如此,更改不易”钟伯道:“正因如此,创出无相门的才是空炎宗主,而不是我的这个师兄。”
“日后你我不必以宗主属下相称,师伯叫我将军亦可叫我定方亦可,我还称你为钟伯”赵定方道:“师祖可曾与你说过要助我成就何种事业?”
“师尊只是命我助你”钟伯摇头道:“至于助你成就何事,你是宗主,自然由你做主。”
“那…..”赵定方道:“便请钟伯讲一讲府内这百余人都是何方神圣。”
“是”钟伯道:“第一个便是属下了。属下在御仙山学艺时,入了无间堂…..”
“无间堂?”赵定方道:“我知御仙山中有空性、定身二堂,从未听过无间堂。”
“那是因为在很多眼中,无间堂并不存在”钟伯道:“无间堂创于仁宗朝,是专为宗氏训练杀手的地方。仁宗迁都不到三年,外有鬼兵作乱,内有流民起义,国内群雄并起,各州太守各自为政。沈朝宗在御仙山上创无间堂,于三十三天宫遴选年轻高手,为皇室充当杀手与死士。无间堂中众人互不相识,只从宗主一人之命。巡检司的巡检校尉虽然只受皇帝节制,终究是朝中的官员,行事自有一套规矩。无间堂杀人的规矩,只有宗主一句话。皇帝杀人,巡检司与无间堂一明一暗,无间堂众先领宗主之命杀人,后被巡检校尉击杀的事屡见不鲜。是以仁宗朝屡有名将重臣被刺,却没人怀疑道宗氏身上,反而是宗氏出动巡检校尉击杀凶手,令那些被杀之人的族人感激涕零。”
“无间堂如此凶险,钟伯此时能站在我面前”赵定方道:“一定有过人之处。”
“运气”钟伯道:“天下高手多如牛毛,无间堂众执行三次任务还没有死的,靠的绝非技艺,而是运气。”
赵定方笑道:“除了运气呢?”
“除了运气,属下最善用的,便是毒物”钟伯道:“御仙山化乐天宫除了传授无上瑜伽大法,还传授制毒用毒之法。”
赵定方道:“皇帝派你来,看来是存了除掉我之心。”
“并非如此”赵定方道:“我是上一任无间堂主派到姬府中准备杀姬兴的。不过,前段日子无间堂内有巨变发生,据师尊说无间堂已经易主了。新宗主杀死前任宗主之后,也失去了一批杀手,属下便是其中之一。无间堂易主之后,我曾上御仙山查探,遇到师尊,才知道无相门又有了新宗主。此时除了我自己与宗主你,天下在无人知道我是无间堂杀手。无间堂于属下而言已经不复存在,属下只听无相门宗主一人之命。”
赵定方道:“这么说,武定侯府中除了你,并没有暗桩?”
“有”钟伯道:“这里有至少三个巡检校尉。”
赵定方皱眉道:“谁?”
钟伯道:“第一个便是那个江迎潮,此女算是我的晚辈,曾随化乐天宫主宗无本学习用毒之术,不过她最擅长的应该是暗器。”
赵定方道:“她所用暗器并非金铁。”
“宗主明鉴”钟伯道:“她用的是叶底枯云,此针为木质,坚愈金铁,分量却轻许多。属下曾在止水城中遇到缚魂宗的人将此针装在木傀儡上,用机关发出,二十步之内可以洞穿板甲。”
“缚魂宗?”赵定方道:“我曾与木妖交过手。”
“木妖乃龙族依炎皇之术所造,有昊天神将之能”钟伯惊道:“宗主能在木妖手下逃生,果非常人。”
赵定方摇头道:“我能侥幸逃生是因为有人相助……化乐天宫怎么会有缚魂宗的兵器?江迎潮是什么来头?”
“叶底枯云本是炎皇所造,御仙山本就有,不过这种针以人力使出来到底不如木傀儡中的机括之力,缚魂宗算是青出于蓝”钟伯道:“江迎潮是巡检司的人。”
赵定方道:“你如何知道?”
“无间堂与巡检司一暗一明,巡检校尉是无间堂众的天敌”钟伯道:“算起来属下已经躲过巡检校尉的追杀不下十次,自有一套分辨的办法。”
赵定方道:“除了江迎潮,还有哪两个?”
“马夫孙吉,还有那个叫小山的打杂的”钟伯道:“宗主若是不放心,这三人随时可以一病不起。”
赵定方摇头道:“不要小看巡检司的人。我刚到这府中,若是三个巡检校尉同时生病,宗孝廉便会派更棘手的人来。不如将计就计。”
钟伯道:“遵命。”
赵定方看钟伯一幅毕恭毕敬的样子,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个狡黠如狐的老者会对真心实意自己俯首帖耳惟命是从。
难道是钟伯口中的“本性”使然?那这“本性”究竟是何物?
赵定方正皱眉思索,钟伯道:“有人来了,是那丫头。”
赵定方道:“我们出去看看。”
二人走出院子,正见江迎潮匆匆而来,见赵定方便道:“将军,门外有两个奉国府的人,要将军去府上答话。”